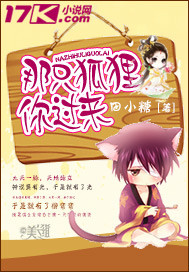A城有许多大街,在其中一条大街那装饰马虎的住宅里,坐着两位绅士。一位三十五岁左右,另一位四十五岁上下。
第一位是林峰,第二位是李文。
林峰的面容生动,表情丰富。乍一看,他比实际年龄年轻:宽阔白皙的前额显得鲜亮饱满,双眸时而闪烁思想、情感和欣喜的光芒,时而陷入沉思,耽于幻想,此刻,他的目光几乎似年轻人那样富有朝气。有时,这双眼睛显得成熟、疲惫、烦闷,将自己主人的年龄暴露无遗。双目间甚至聚起三道淡淡的皱纹,那是时光和阅历无法消泯的标记。乌黑顺溜的头发披落在后脑勺和耳朵上,可鬓角上已有些许银丝显现。脸颊和前额,眼睛和嘴巴旁,依然保持年轻的色泽,可太阳穴和下颏周遭的肤色已呈黄褐色。
总之,根据这副面容,极易将人生阶段猜透,青春与成熟的争斗已然完成,此人已进入其人生的另一半,他所经历的每一个人生体验、情感和病痛,都留下了痕迹。唯独他的那张嘴,在薄薄的双唇难以觉察的变化中和笑容中,还保存着年轻人的、有时几乎是孩童的那份纯真。
林峰身穿家常灰大衣,盘腿坐在沙发上。
李文则相反,他穿件黑色燕尾服。白手套和呢帽放在身旁桌子上。他神色自若,或是说,他对周围可能发生的一切,持漠然等待态度。
目光机灵,双唇透着聪颖,黄褐色的脸庞,一头修剪漂亮的花白头发和一脸斑白的络腮胡子,举止温和,言谈持重,装束得体——这便是他的外表肖像。
从他脸上,可以读到不露声色的自信和对他人察言观色的了然。凡观察过他的人都会说:“此人活得潇洒,懂得生活,了解人。”倘若不把他归于气质不凡、特殊的人群,至少也会将他列入生性质朴的那类人。
他是人才辈出的A城人中的佼佼者,人们称他为上流人士。是的,他属于A城,属于上流社会。很难想象,除了A城,他会待在别的什么城市里;除了上流社会,也即A城居民中闻名遐迩的最高层,他会待在别的阶层里。尽管他工作缠身,私事繁忙,但你常常会在各家的大客厅里遇见他,早晨拜访,中午宴会,夜间家庭晚会,最后便是牌局。他马马虎虎,平平常常,既非性格刚强,亦非意志薄弱;既非学富五车,亦非不学无术;既非信仰坚定,亦非怀疑一切。
不学无术或缺乏信仰,在他身上的表现形式为某种轻率而浅薄的否定一切:他对一切漫不经心,从不真诚地接受任何事物,既不对它深信不疑,亦不特别偏爱入迷。与人交往,他怀着几许嘲笑和怀疑,几许冷淡和平静,既不给谁以始终不渝的深情厚意,亦不与谁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他在A城出生,上学,人到中年,西边没有到过比更远之地,北边没有到过更遥之处。因此犹如水滴中的太阳,在他身上反映出A城的整个世界,显现出A城的全部实际、风气、生活方式、本性和工作——此乃A城的第二特性,别无其他。
关于其他种种生活,除却城内外各种报纸提供给他的以外,他本人没有任何概念和观点。A城的激情,A城的观念,A城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恶习和美德,思想,事业,政治,大概还有诗歌——他的生活便围着这些转,不曾想从这个圈子里挣扎出来,因为他在此,为自己的本性找到了最奢华、最充分的满足。
四十年来,他不断冷漠地观察着,看每年春天一艘艘挤满旅客的游轮,如何启航驶往城外;看四轮公共马车,随后是火车,如何在俄罗斯大地上驶过;看成群结队的人们,如何“怀着天真无邪的心情”出游,去呼吸另一种空气,去凉爽凉爽,去寻找感觉和消遣。
他从未感到有类似需求,也不认为别人有此种需求,只是平静而冷漠地盯着他们,盯着这帮异类,脸上的表情彬彬有礼,目光中却在说:“随他们便,反正我不去。”
他谈吐朴实,随意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世上、上流社会和京城里出现的一切事情,他无所不知;倘若战争爆发,他密切注视战事的各种细节;他熟悉新上演的歌剧,对夜晚有谁被杀一清二楚。他对京城每个名门望族的家谱、事业和庄园状况、家庭丑闻如数家珍;他明察行政机关内每秒钟所发生的事,包括人事变动、人员升擢与奖励;他知悉城里的各种流言蜚语、家长里短。总之,他对自己的世界了如指掌。
上午他满世界转悠,也就是奔波于各家的客厅,多多少少也是为私事和工作;晚上常常先是看戏,最终是在城俱乐部或熟人家里打牌,几乎人人他都熟悉。
他打牌从不出错,有出色赌徒的美誉,因为他对别人出错牌十分宽容,从不发火,而且显得彬彬有礼,好像搭档非但没出错,而且出了张好牌。此外,他既玩大赌注的,也玩小赌注的,既同高手玩,也陪任性的太太们一起玩。
他在建筑部门的工作进行得不错,在办公室里干了十五年苦差使,执行的是别人的设计方案。他机敏地揣度上司的想法,赞同他业务上的观点,灵巧地在纸上体现各种方案。上司换人,观点和方案亦随之改变,李文在新设计理念下与新上司一起共事,依然聪明灵巧;他所服务过的董事长大人们都喜欢他起草的报告和呈文。
眼下,他在一位董事长手下担负一项特殊使命。每天一早,他来到董事长办公室,然后去董事长夫人的客厅,实实在在地完成她委托办理的几件事情,而每到晚上,在约定的日子里,他必定按约去凑牌局。他有相当大的职位、相当高的薪俸,却无所事事,清闲得很。
倘若允许钻进别人的灵魂,那么,在李文的灵魂里,没有任何黑暗,任何秘密,往后也不会有任何难以猜度的东西,即使女巫们亲自以某种更为美好的命运来诱惑他,或是将他如此执着、如此精神抖擞所攫取到的东西夺走,也已无能为力。他步步高升,从五等文官升为四等文官,最后,又因长期而又卓有成效的服务,以及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牌局上的“不倦努力”,他又擢升为三等文官,并保留原薪在某个不朽的常设机构或一个什么委员会里抛锚泊港;在那里,任凭人类的海洋汹涌澎湃吧,世纪风云变幻吧,民族和帝城的命运落入深渊吧,一切均将在他身旁一闪而过,直至中风或其他打击中止他的生命历程。
李文结过婚,丧偶,并有个十二岁的女儿,用公费在贵族女子中学受教育,而他安顿好自己的事务,过起了平静而无忧无虑的老单身汉生活。
唯独一桩事,扰乱了他的安宁,那就是因坐着不动的生活引起的痔疮;对他而言,前景令人担忧,他得暂时中断此种生活,到什么地方的矿泉去待着。医生曾这般威吓过他。
“是否该穿上衣服啦:四点一刻!”李文说。
“是啊,该穿了。”林峰答道,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你在想什么?”李文问。
“是在想谁?”林峰纠正道,“一直在想她……想张荟彩……”
“还在想!嘿!”李文说道。
林峰开始穿衣。
“我把你拽到那儿去,你不心烦吗?”林峰问。
“根本没有:在那里和在周来家,不都是玩吗?说实话,赢老太太的钱,很不好意思:张娜瞎吃自己对手的牌,而张欣要什么牌就大声嚷嚷。”
“请放心,你不必为五元去行骗。两个老太太收入达六万呢。”
“我知道,这一切都将归张荟彩吧?”
“归她,她是亲侄女。可何时才会到手哪!两个吝啬鬼,会活得比她长。”
“她父亲好像也稍许有些……”
“不,全给他花光了。”
“花哪儿啦?他几乎不玩牌的。”
什么花哪儿啦?那么女人呢?这通忙乎,这整个儿的呢?去年冬天,他在晚会上送给一套餐具便价值五千,可她连晚宴都忘了邀请他……”
“对,对,我也听说了。为了什么?他去她那里做什么?……”
两人笑起来。
“张荟彩的丈夫好像也给她留了些钱!”
“没有,七千元进项;这是她的零花钱。其实全靠两个姑妈。哦,该走啦!”林峰说,“午饭前我还想上玫瑰大街走走。”
李文和林峰走在大街上,朝左右两旁点头,行礼,握手。“现在你在张荟彩那里待的时间久吗?”
“和通常一样,暂且还不撵我。怎么,感到寂寞啦?”
“不,我在想上周发来家是否赶趟?我倒并不觉得寂寞……”
“幸福之人!”林峰羡慕道,“倘若世上没有寂寞无聊该多好!也许比抽顿鞭子还难以忍受?”
“劳驾,别作声!”李文充满迷信的恐惧将他制止,“还说些乱七八糟不吉利的话!身上长个痔疮就够我受的了!大夫们就知道把我从这里打发走,说是全是这坐着不动的生活闹的,所有不幸就在于此!其实还有空气:还有什么比这空气更好的吗?”他欣喜地嗅了口空气,“如今我挑了个比医还善良的人:他打算夏天用酸奶替我治病,要知道我长的是内痔……明白吗?那么你是出于无聊才上自己表妹家的?”
“自然啦,这还用问!难道你坐到牌桌旁不是因为无聊?人人都像逃避瘟疫那般在摆脱无聊。”
“你挑了服多么瞥脚的药来摆脱无聊,天天一个样:陪着女人说些无聊的空话!”
“你打牌,难道天天不一个样?你是在牌局上躲避寂寞无聊……”
“哦,不,它可不一个样:有个D城人进行过运算,分出一副同样的牌,千年才可能重复一回……还有手气呢?牌手的性格、牌技、花样呢?打错牌呢?……不可能一个样!可是,瞧,陪着女人斗嘴皮子,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今天,明天……瞧,这一套我可不懂!”
“你不懂得美,这有什么法子?有人不懂音乐,有人不懂绘画:这是自己家族的智力不发达……”
“对,确实是自己家族的原因。瞧我的局里,有个陈晨,当个副手:此人不论对官太太还是女仆全纠缠不休,一个也不放过,当然,全得有几分姿色。对她们说恭维话,献殷勤,送糖果,送鲜花,难道他智力发达?”
“我们不谈这话题,”林峰说,“不然我们俩又将钻牛角尖,差点动起手来。我不懂你的牌艺,你有权称我外行。可是,关于美,你也别硬要大发议论。任何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欣赏绘画、雕塑和女性那鲜活的美;你的那个陈晨这样欣赏,我那样欣赏,而你怎么也不欣赏——那随你便!”
“你同女人们玩牌的,我见过。”李文说。
“是,我玩牌,那有什么?你也玩,并且差不多老赢,可我老输……这有什么不好的?”
“是啊,张荟彩是个美人儿,而且还是个有钱的、打算出嫁的姑娘:娶她吧,万事总该有个结局。”
“是啊,万事总该有个结局,而无聊又该开始!”林峰若有所思地重复道,“可我不要结局!请放心,她们不会将她许配给我的!”
“那么,依我看,就没必要再来往了。你简直就是个唐璜!”
“不错,是唐璜,一个无聊之徒:依您看,是这样吗?”
“可不是:那依你看,他是什么?”
“哦,那么拜伦、歌德,还有一帮画家、雕塑家,全是无聊之徒了……”
“难道你是拜伦或是歌德不成?……”
林峰恼火地扭过脸去不看他。
“唐璜主义在人类中同样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还更深刻些;这种欲望还更有天赋些……”他说。
“既然是种欲望,那就结婚吧……我对你说……”
“嗨!”林峰几乎绝望道,“要知道,结婚可以一次、两次、三次:莫非我就不能像欣赏雕像之美那样,去欣赏美吗?唐璜首先享受到的是美学上的此种欲望,但很粗俗;作为自己时代、教育和风习之子,他沉溺其中,超过了此种崇拜的极限,再没有别的。嗨,我同你有什么可说的!”
“倘若不想结婚,那就没必要再去。”李文淡漠地重复道。
“你听我说,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对的。我首先想说,我的迷恋永远是真诚的,没有预谋,这并非追逐女性,请你永远明白。当我的偶像哪怕有一个细节接近理想,我的想象力立刻会将她塑造为一个理想中的人物,其余部分则由我自然而然地加以补充完善,于是便出现幸福的理想、家庭的理想……”
“瞧你,那就结婚吧……”李文说。
“等等,等等,从未有过一种理想能待到婚礼前的:它失去光泽,消失,而我则离去,变得冷漠无情……想象力创造什么,具体的分析便将其毁坏,犹如纸糊的房子。或者是理想不待我冷静下来,便离我而去……”
“可毕竟你还是每天同女人待在一起,闲聊啊!……”李文摇摇头,固执地强调道,“就譬如今天吧,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她们不让她嫁给你,你还想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
“那我也问问你:你想从她姑妈那里得到些什么?你得了什么牌了?你是赢是输?难道你上那里是想把那份六万元的进项全赢过来?你是去玩牌,还是去赢钱……”
“我没有任何打算:我这么做是因为……因为……为了找乐趣。”
“是因为……因为无聊,你要知道,我才是为了找乐趣,同样也没有什么打算。至于我如何欣赏美,你和你的陈晨无法理解,你和他都别介意——那就齐了。要知道,有一种人对强烈的情欲异常崇拜,而另一些人对此种需要一无所知,并且……”
“强烈的情欲!情欲这玩意儿可是影响生活。需要劳动——只有事业才是摆脱空虚的一剂良药。”李文庄重道。
林峰停住脚步,拦住李文,恶狠狠笑着问:“事业?什么样的事业,请说说,这倒挺有趣!”
“什么什么样的事业?工作啊!”
“难道这也算事业?请告诉我,除少许例外,工作中有哪项事业,离了它是玩不转的?”
李文惊讶得吹了声口哨。
“你瞧!”他说,朝自己四周望了一眼。“就是他!”他指着一个警察局的小官吏,此人正目不转睛地朝一边盯着。
“你去问问他,”林峰说,“他为何站在这里,那么专注地望着是在等谁?等位将军!他都不瞧我们一眼,因此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把我们的手帕从口袋里掏走。难道你以为你的几张公文纸便是事业?关于事业,我们不必再多费口舌,告诉你吧,说实话,当我在我的画上涂鸦时,当我在钢琴上乱弹一通时,甚至当我为美貌所倾倒时,我才干得更欢……”
“除了美貌,你在自己表妹身上还找到什么特殊之处?”
“除了美貌!哦,这就是全部!其实,我对她知之甚少:美貌加知之甚少,便将我吸引过去……”
“天天在一起,怎么还会缺乏了解?……”
“了解不多。我不知道在她娴静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不知道她的过去,也无法猜测她的未来。她是个女人还是个洋娃娃,她在过着这样的生活还是在假装如此生活着?这都折磨着我……你看,”林峰接着说,“看见这个女人了吗?”
“是那个胖胖的、带着包袱爬上出租马车的女人吗?”
“是啊,还看见那个从四轮轿式马车的窗户朝外张望的女人了吗?以及从街角拐出朝我们走来的那个姑娘?”
“嗯,那又怎么啦?”
“你匆匆一瞥便能从她们脸上看出某种或关切,或忧伤,或欢愉,或思索,或无拘无束的迹象:总之,那是运动和生命。不过稍稍需要选配一把钥匙,才能说出这个女人有家庭和孩子,就是说有过昔日的生活;而那边那位看得出充满热情或是显露出活生生相爱的迹象,就是说她拥有今天;而这边这位,年轻的脸上透着希冀,心中的愿望暴露无遗,预示着她那并不安定的未来……”
“是吗?”
“是啊,到处都有着某种生气蓬勃、要求有所作为、创建功绩、期望生活、呼唤生命的迹象……可在张荟彩那里,这一切全没有,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甚至没有冷漠,没有寂寞,想诉诉苦,说一句曾经有过真正的生活但给毁了,也不可能!她容光焕发,容貌出众,但既无所求,也无奉献!因此,我对她一无所知!而你对我去打牌还惊讶不已。”
“你早告诉我这些,我就不会惊讶了嘛,因为我自己也是这种人,”李文说,突然停住脚步,“去我家里,不去她那儿……”
“你家?”
“是啊,我家!”
“怎么,你想显示美貌?……”
“我将显示宁静安逸,并为此感到满足;其实她同样……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与你是毫无关系,可她确实很美,美如天仙!”
“那就结婚算啦,倘若不想或不能结婚,就打住,料理事业……”
“你先着手吧,你可以把藐视死板的活生生的智慧和充满热情的灵魂,投入到事业中,并指出如何把精力用于某种事业上,什么值得奋斗;而让自己的纸牌、拜访、招待晚会和工作全见鬼去!”
“你本性真不安稳,”李文说,“缺乏严格的管教和艰苦的磨练,因此便瞎胡闹……还记得吗,你的唐静在世时,你曾说过……”
“唐静!”他轻声重复道,“这是我心头唯一的一块重石,在这美好的印象和短暂的迷恋中,请别妨碍我对她的怀念……”
他叹了口气,两人默默走到一条胡同,走进一座贵族宅邸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