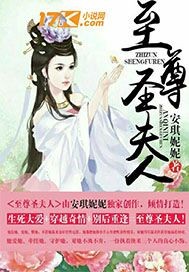“寻常珍珠生于海底,由母蚌以身体孕育,此物生于黄河入海口之处,河水海水轮番冲刷,色泽与众不同些。”灵珠夫人娇笑道:“不过此物真是不值多少银子,我喜爱它是因为它的名字叫灵珠。”
男子看了又看,露出喜欢之意,灵珠夫人摘下灵珠,戴在男子的颈间,正色道:“你我之情可堪日月,必不负灵珠。”
李家小厮仆妇过百人,此刻却鸦雀无声,正房中大夫人居中而坐,身着明黄服饰,遍插珠玉,不怒而威,看的下人们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上前奉茶,或是发出一点声音。
大夫人拍着桌子厉声道:“灵珠不过是萧家的家妓出身,侥幸成了妾侍,正室死了之后才成为夫人,如今却不安于室,四处招摇过市,还想进我李家的门?”
“姐姐稍安勿躁,易辰沉迷至此,可能有什么缘由,阿银,你平日跟着少爷,你来说说是什么缘由。”说话的青衫男子是李家大夫人的亲弟弟王莫言,言语中护着的正是与灵珠夫人交好的李家少爷李易辰,李在牡丹是国姓,李家正是正宗的皇亲国戚。他与李少爷的感情深厚,是以连忙安慰姐姐。
阿银自下人中间走出,但低头而站,却未答一句。
王莫言追问,“阿银,幸得你一直跟着易辰,照料得当,才拖延至今未病发,事已至此,我们并没有怪你未提早禀报,有话直说,不用害怕。”
阿银轻声道:“少爷个性倔强,只怕家里越反对,他便越坚持,以小人之见,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过去,或许有情淡的一天。”
大夫人喝道:“这样的丑事,若是传了出去,就算我们李家能担待着,汴京城中那帮老东西也会嚼舌根的,阿银,你说那女子到底有多美貌?”
“灵珠夫人眉清目秀,优雅脱俗,举止出尘,却是个美人。”阿银道。
“即是如此,我便去会会她。”大夫人道。
莫言上前,“也好,姐姐亲自去一趟,可当探知虚实。”
唐多慈的院子内,她正在喜洋洋的教多多学走路,含烟姑娘饶有兴致的在一旁看着,看着看着也看的腻歪了,于是问道:“你知不知道萧玉郎的爹爹是怎么死的?”
唐多慈白了她一眼,“我连见过都没有见过他,听说早就死了,我如何能见?”
含烟姑娘自知问了废话,却没有引出她想听到的话觉得挺没趣的,不过还是想炫耀一番,“我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你都能知道,看来你听说的也不是真的。”唐多慈毫不留情。
“你别小看人,当年萧江山死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蹊跷,我爹还派人去查来着,只不过查来查去的也没查出来什么。不过有一次我在爹爹的书房看过一个卷宗就是关于萧江山死因的,上面写死于中毒,至于为什么给压下来,我就不知道了。”含烟姑娘道。
“没写中了什么毒吗?”唐多慈问道。
“我也是很好奇,后来还特意问了爹爹,爹爹告诉我说是死于中毒也只是猜测,因为尸体没有任何异样,偏偏是没有任何异样才让人觉得奇怪。”含烟姑娘道。
“或许死于天下第一奇毒呢?”唐多慈微微一笑,带着调侃。
“什么是天下第一奇毒?”含烟姑娘问道。
唐多慈沉吟片刻,“说的太隐晦了你反而听不懂,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含烟姑娘瘪瘪嘴,“讲吧,反正我还挺爱听你讲故事的。”
从前呢,有一个师傅问他的徒弟,“什么是天下第一奇毒?”
七师弟道:“我愿走千山,渡万水,收瘴疠,品花草。菌菇蕊叶,阴阳调和,遍览医典,以求生克。研磨细琢,鼎炉蒸熏,使毒无色无臭,无迹可寻,无药可解。”
师父摇了摇头。
六师弟道:“我愿杀猛兽,捕蛇蝎,采矿石,淬金铁。提配方,做分析。细密纪录,研究结构。集万物之邪诡,合天地之残忍,使人见血封喉、当者立毙。”
师父摇了摇头。
五师妹道:“我愿红妆素裹,描眉画眼。习箜篌,按玉笛,摹工笔,绘写意。四书五经、淫词浪曲,饮食茶酒,德容言工,以至于婉转承应、品箫媚术,无一不精。令天下男子皆为我裙下之臣、入幕之宾。那时节,任凭我端给他们喝孔雀胆、鹤顶红,他们也甘之如饴。”
师父擦了擦鼻血,摇了摇头。
四师弟道:“我愿研究风的吹送,水的流动,人的饮食习性,牛马的走向爱好。我愿参透天地星辰的运行,探寻世间的规律,绘制出一幅图像。我只要一小撮毒药,不必见血封喉,只要能生生不息的繁衍。我将毒药下在一条合适的河中,自会被合适的荇藻吸收,自会被合适的男子吃到,自会传递给另一个女子的嘴唇,自会传递给衣服、器物、牛马与孩子,自会有带毒的蒲公英被风吹送到天涯海角,沾染上花草、楼阁、船舶、笔墨、胭脂、簪钗、甲胄、门扉,自会从手脚、口唇、眼睛、肌肤上入肠胃、进骨髓,日积月累,深不可治。”
师父立刻停下给身上拍爽身粉的动作,摇了摇头。
三师弟道:“我愿苦读孙吴兵法,精通三韬六略,烂熟经史子集,旁涉诗词歌赋。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唇舌鼓摇三百国,胸中甲兵十万人。那时我自荐为相,出谋划策,结党营私,欺上瞒下,取朝纲,揽大权。那时,管你忠臣良将,都敌不过我信口开河。任你尽忠报国,抵不住我十二道金牌。为所欲为,毒施人鬼。”
师父摇了摇头。
二师弟拍案而起,横眉冷对朝诸位师弟和师父环视一圈,一字一句的说:“尔等卑鄙无耻、毒辣残忍的鼠辈!”
然后摔门而出。
后来,他们听说,二师弟走得很远,去投了义军。他娶了义军头目一个嫁不出去的丑女儿,成了义军的名将。他爱兵如子,衣食与士兵待遇相同,肯为士兵吸吮伤口的脓液。他清廉无私,有赏辄分,家无余财。他遇敌则冲锋在前,撤退则单骑断后,知人善任,贤达开明,有过则改,兼听则明。他甚至还是位良医,亲手救过无数将领的性命。他微笑着,“我以前学毒,好歹也有点用处么。”
岳父死后,二师弟成了义军的领袖。他率领大军以少击多,以一场背水大战奠定了中原大局;他命忠诚的部下袭取东南,楼船如林,一鼓而定。他又亲自率军进取西北,拓荒万里,诸小国纷纷请求入朝依附。天下已定,他又和好友兼宰相一起谋划更新的制度,休养生息、以慰百姓。他忙于军政大计,唯独没有考虑自己的地位。他日夜操劳,不近女色,始终只忠于自己那丑陋的原配夫人。
最后,在都城,他拒绝登基为王。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群臣上表,他再次拒绝,并威胁说如果再逼他为王,他就要匹马出行,挂冠归隐。百姓们箪食壶浆,拜倒在宫门前,号哭连天,说若他不允,则天弃吾民矣。他泪流满面的下跪在百姓面前,被迫从命,遂为王。
师父看了看徒弟们,慨叹道:“你们还务于雕虫小技……看看你们师兄的志向!”
后来,王威加海内,于是免去诸将权,把他们圈养在宫中。
王营造了复杂精致的制度,装备了精良的设备,并收天下百姓的兵器,随后用两场干脆利落的戡乱,向天下夸示了御林军和普通百姓之间压倒性的差距。
王设立了精密的信息处理机关,控制了百姓们的每一个信息源头。
师父在老家出门少。但他每次出门,都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他好奇的打听又有哪些邻居过世了,但大家都说不出所以然。师父发现自己头发掉得越来越多,容颜日益枯槁。
后来,深夜,有一乘车来,几个持戈卫士把师父带进了宫廷。
王在百丈高的露台见师父。他拒绝师父行君臣之礼,反而向师父行了师徒之礼。他微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他说,师父当年对徒儿的教诲,徒儿一刻也不敢忘。”
师父问,“怎么个不敢忘呢?”
王拉师父到露台栏杆边,俯瞰河山秀丽。王向师父指了指天边,如紫罗兰一般绽放的云。王向师父指了指滔滔大河,如鲜血一般殷红的流水。王向师父指了指亿兆黎民的脸,那像桑叶一样绿的肤色。王笑了笑。
师父问,“怎么呢?”
王道:“我记得七师弟的创意。他要用植物的阴阳生克调出毒药,无色无味。我记得六师弟的创意,他要从动物、矿物身上提炼元素,来合成见血封喉的毒药。我记得五师妹想用女色,我记得四师弟要研究下毒的路线,我记得三师弟想成为奸臣。我一直记得。”
王道:“我现在,可以随便在稚儿的牛奶里加毒药,让他们提早衰竭。我现在,可以随便在百姓的茶饭里加毒药,让他们短寿。我现在,可以随便在女子的饭食里加毒药,让她们不育。我现在,甚至可以一高兴便坑埋百姓。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别人听见。”
王回过头问师父:“现在,师父,你知道何为天下第一奇毒了吗?”
师父退了两步,看了看他。师父道:“没人阻止得了你了吗?”
王笑笑。
师父道:“你难道什么都不怕了吗?”
王笑笑。
师父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排行第二?”
师父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大师兄?”
王愣了一愣。
师父道:“你就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比如,你的大师兄天赋异禀,击败我之后叛出师门,而我培养你们,就是企图击败他?”
师父道:“你就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比如,你的大师兄一直藏在你附近?他的手段还高你一筹,可以随便毒死你?”
师父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个技艺还在你之上的大师兄,他又怎么甘心被你超越?你有没有想过,他随时都可能用一种更绝妙的手法,来让你败北?”
王想掩盖自己笑不出来的表情,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