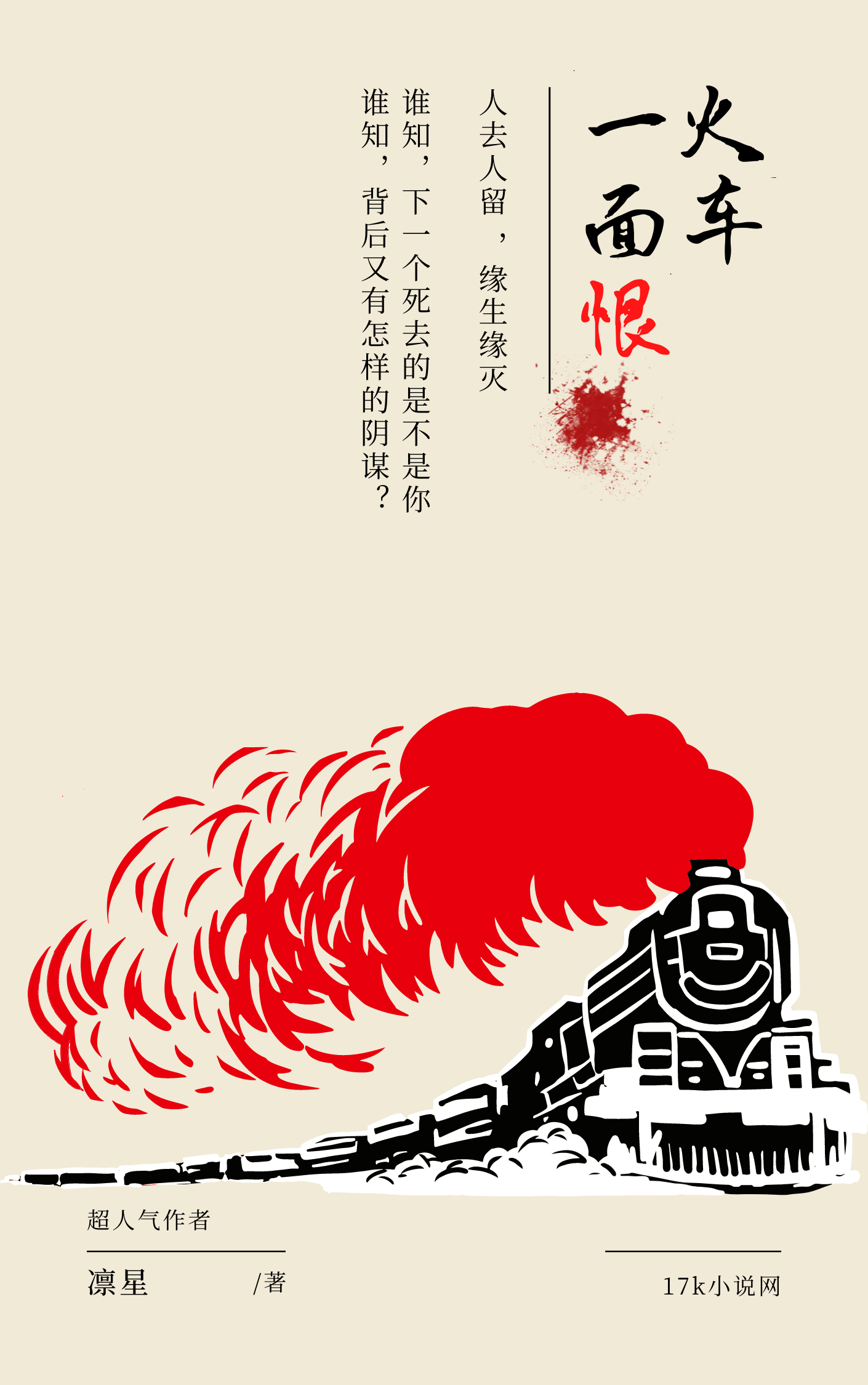等子衿赶到景府时,锦子铭垂头丧气的从另一边回来,子衿赶紧跑着迎了上去,“锦子铭,我告诉你,今天我碰到了一个怪老头,他告诉我你说的那种毒叫做‘青离’,闻了活着喝了对常人无异,但是对怀有身孕的人来说却是致命的。”
“我知道,所以王爷知道后,才让袭若喝了流产的药,怕怀着孩子,袭若的命会不保。”锦子铭仍旧垂头丧气,去了一趟冰儿说的山上,找到了那个姑子,却发现那个姑子固执的什么也不说,整日看着那半支烧坏的梅花簪发呆。
锦子铭继续向前走着,子衿在后面继续说道:“那老头说,中这种毒和雪兰混在一起,便是更甚的药,会让人终身不能有孩子,你还不明白吗?”
锦子铭的脚步骤停,“你说什么?”
子衿的眼眶有些湿润,慢慢的靠着景府院外的墙,慢慢的向下滑去,继而抱着双膝坐在地上,眼眶有些湿润,“怪不得她非要离开景府呢,她承受着那样的痛楚,我还那么落井下石非要嫁给景亦宸,我是个狠毒的人。”
锦子铭也慢慢蹲在子衿面前,手掌抚过她的面容,“你也不知道结果会是这样不是吗?”
子衿能看到锦子铭眼中的痛意,她上前拥住锦子铭的脖子,“我很坏对不对?对不起。”
锦子铭也回抱着她,“傻丫头,你和袭若一样,心底都是善良的,只是袭若,她现在如何呢?”想到这里,锦子铭有些恨自己,他曾经答应过爷爷会用生命护着袭若,现在却连袭若在哪都找不到,他恨自己的无能。
景亦宸已经在锦府的大厅内,跪了整整一天了,期间他滴水未进,白岑静静的伫立在他身后,也是什么也没吃,白岑明白主上是想得到锦老爷的原谅,更想惩罚自己。
当管家又一次端着饭室进来时,仍旧被景亦宸拒绝了,身后响起锦老爷的声音,“起身吧!我想我的外孙女儿也不想让你这么跪着,起来吧!”
景亦宸仍旧没有动静,锦老爷慢慢走过去,拉着景亦宸的手臂,“老夫不为难你,你难道要为难老夫不成?”
景亦宸低下头,“晚辈不敢,只希望您原谅。”
“罢了,老夫知道你并不坏,要不我的袭若又怎么会喜欢你,今日我先原谅你,日后如果你找不回袭若,我不管你是什么王族贵胄,老夫都不会放过你,听好了吗?”锦老爷的声音明显高出几分。
景亦宸看的出一位老者对于外孙女的疼惜,他点点头,“请您信我。”
“那就起来吧!堂堂的王爷不要失了身份,这是袭若昨天寄来的信,你看看吧!”说罢把景亦宸拉起,把一封信塞到他手里便离了大堂。
景亦宸看着锦老爷的背影,总觉得太多落寞,顿时愧疚又增添几分,来不及细想,他打开了那张很奇特的信纸,袭若娟秀的小字呈现在纸上。
外公:当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请原谅若儿的任性,袭若不得不听从心的安排,袭若想好好的去在乎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和他在一起,袭若不想一辈子和娘亲一样去思念着一个人过一生,可是上天总是不给我机会,我们之间总有太多的荆棘,我想努力的靠近他,我不怕刺痛,可是我怕他痛。他已经隐忍着恨意过了十几年的时光,我想让他快乐,真的想。
我有太多的话想说,可是说出来反而言不由衷,袭若明白您一直爱着袭若,对不起,我会好好的想着您,无论我在南止还是峥定,又或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我都会好好想着您,珍重。
看着看着,白岑明显看着主上的手微微颤抖,他赶紧上前,“主上,您还好吗?”
“她是爱我的,她是的。”景亦宸的声音很是低沉,但是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没错,这封信带给景亦宸的是深深的不安。
“夜地,立即召集你门下的使者去查寻这封信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这张信纸,不像我们中原造的纸张,立即着手去办。”景亦宸喝声道。
白岑单膝跪地:“夜地遵命。”
说完便离开了锦府,景亦宸也随后跟锦老爷告了别也离了锦府,景亦宸只身一身在回峥定的路上并没有快马加鞭,他反复的在想着袭若的信,每字每句都刻在了心上,现在的他可以肯定两点,那便是袭若是真正在意自己的,第二便是,她的离开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可是是什么,他猜不到。
已经慢慢的行进了几天了,期间白岑也没有消息,正准备下马继续慢慢寻找时,白岑出现了,景亦宸和白岑找了一个茶馆谈话。
白岑把那封信拿出来,放在桌上,说道:“主上,我门下的人来报,这些纸张并不全是木启国的纸张,而是两国边境上的一些人做出来的,联合两国纸张特性做出来的,做这种纸的地方叫做朝安,也就是……”
“就是峥寒的封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锦子铭一个翻身便从茶馆二楼飞身下来,坐在景亦宸旁边的椅子上。
“你怎会在这?”景亦宸问道。
锦子铭深吸口气,“当然是找你们,我已经快马加鞭了几天了,把那丫头也甩在峥定了,只是你呢,你的收获呢?”白岑的语气很直,直冲景亦宸。
景亦宸没有吱声,眼睛还是看着信纸,锦子铭似乎一下子怒了,他把信揉成一团,厉声道:“不是已经知道袭若在朝安的吗?为何不去?是你不敢,还是你担心去了之后才发现袭若和峥寒在一起。所以你不敢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