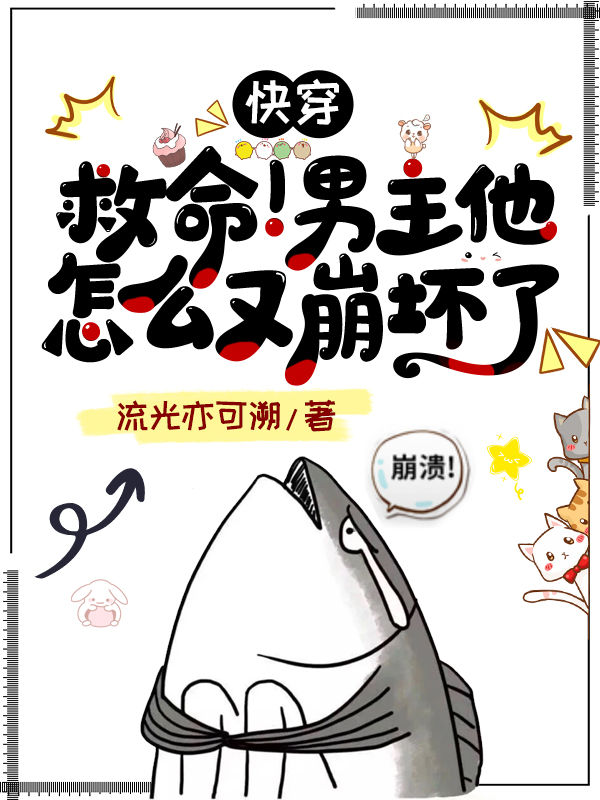顾落月控制自己不要翻白眼,见慕容楠打开点心食盒,冷冷道:“大小姐饿了吧?那我们先吃饭。”
“吃什么饭呀。”慕容楠踮起脚尖往顾落月的嘴里塞了块绿豆糕,她将自己的脑袋埋进顾落月的胸膛里,“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顾落月的脸有点发黑,也不知是糕点过于甜腻,还是挽着自己的少女甜得齁咸。
的确可爱的让人有点心慌。
“吃什么饭?顾大哥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常乐的手搭上两人的肩膀,用力往里一推,发出低低的笑声,“不过是想让你乖乖就范罢了。”
顾落月的下颚擦过慕容楠的发丝时,身体很明显地颤抖几下,他朝常乐和楚无衣露出诡异的微笑。常乐佯装不明所以,楚无衣本能地躲在常乐身后。
几人坐上门派弟子拉来的马车。
慕容楠端坐着,规矩地与常乐和楚无衣保持一段距离,她的嘴角扬起的笑容恰到好处,活泼大方却隐隐有种疏离感:“这位公子该如何称呼?”
“顾升日,我族弟。”顾落月抢先一步回答,眼底竟全是坦荡,仿佛他说的是真话一般,他的手覆上常乐的脑袋,“你可别欺负他。”
听起来的确和“顾落月”很对称。出乎意料的是,慕容楠没有表现出任何怀疑。
果然爱情只会打扰女人思考的速度。
喜欢板着脸的楚无衣最先轻笑出声。这短时间在外漂泊,脸比原先晒黑不少。或许山水使人豁达,使夜间落入他眸子里的星光在白日也能呈现。
“在下名为韦砚,是常姑娘的表兄,常年云游在外。”常乐的眼皮跳了下,她打掉顾落月的手,朝慕容楠行礼,长袖一辉,努力想使自己看起来洒脱一些,但与慕容楠对视的眼睛,看似神采飞扬,却藏着几分冷静,“她自知无力护住这个孩子,家里又有生意操持,就将孩子托付于我。”
常乐的确有个云游的表兄,每年秋季都会停留在连城休整。本来常乐是准备随便借个好编故事的马甲冒充的,结果表兄竟豪迈地摆了摆手,说自己要跟随商队出海寻仙,这几年估计都不回大梁,只求常乐能借着他的身份不要冷落他的父母即可。
所以金钱帮若真要查“韦砚”,应是查不出什么。毕竟表兄行事随性,很少在世间留下痕迹。
慕容楠听到常乐说“云游”,问了不少细节,所幸常乐做了功课,倒是能没有漏洞地答上。
“阿砚和无衣劳累多日,有什么事大小姐以后再问罢。”常乐回首望了顾落月一眼,她以为顾落月是爱笑的那类人,但到了金钱帮后,无论是对死缠烂打的慕容楠还是普通的金钱帮弟子,嘴角就未真诚地翘起半分。就连那对天生多情的狐狸眼,眸光暗淡后,也显现出了常乐少见的清冷。
这副模样常乐倒也不是没见过……只不过是两人初识的时候,顾落月刚刚失了家。
可能是顾落月在金钱帮活得并不畅快。
慕容楠是极其听顾落月话的,没有再问常乐乱七八糟的问题,只不过夜间用饭时灌了她不少酒。
翌日,常乐睁开眼,发现自己正枕着楚无衣的手臂,抬眸正对上一对幽幽的墨色瞳孔。
常乐见楚无衣眼眶下的乌青,知道他昨夜没有睡好,她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难道她睡觉时打鼾了,影响到孩子长个子了?
那这不是破坏了好大儿对她的良好印象。
昨晚常乐喝大了,一听金钱帮有财部,硬是求着顾落月带她去聚财楼转悠。或许是吹了冷风,常乐脑子的确清醒了少许。楚无衣在门口等着,却听见房间里传来珠子“噼里啪啦”的撞击声,他谨慎地推开门,发现常乐正执灯翻阅着账本。
至于顾落月,早被慕容楠拉着去赏月了。
常乐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楚无衣有些手足无措,只敢端起油灯,防止常乐将油灯碰倒。
灯光黯淡不少,常乐看不清账本的字,委屈地拉了拉楚无衣的衣角。她的身体忽东忽西,脑袋更是左右摇晃,脸颊仿若烧开一般,眼神更是异常的迷离。
“工作要做完,不然老板要扣奖金的。”常乐的喉咙深处发出哽咽的声音,眼角开始堆积泪水,她猛然起身,挥臂擦掉眼泪,露出坚定的目光,捏起拳头喊道,“打工人,打工魂,打工才是人上人。”
楚无衣的脸部狠狠抽了一下,他瞧常乐鼓起腮帮子,手不听使唤地捏上对方泛红的脸颊。不碰还好,这么一碰,常乐直接嚎啕大哭。
常乐指着映射在墙上的人影:“老板怎么还不下班啊,他是没有老婆吗?他不下班我也走不了。”
眼泪鼻涕一起糊在楚无衣的袖子上。
这下楚无衣彻底绝望了,只能嫌弃地卷起袖子。
楚无衣端着灯,坐在常乐身旁和她一起看着账本,尽管看得不太懂,但他的眼里始终透露出孩子劲的认真。冷风透过缝隙吹到他身上,他的身体抖了抖,和常乐越靠越近。他咬着牙挺直了腰背,希望能给自己的阿姊将大部分的风挡下。最后实在看不进去了,楚无衣举灯开始观察常乐的眉眼。
少女的眼睛并不是会被所有人认可的美。它没有大梁王朝赞赏的妩媚、乖巧,也不似母亲的温婉、顺从。它有过墨竹的坚毅,冰雪的淡然,浮云的从容,狐狸的狡黠,烈酒的泼辣,亦有过连楚无衣都很少展现的天真烂漫。
不知不觉中,楚无衣离常乐愈来愈近。他努力睁开迷蒙的睡眼,鼻息间是佩兰的幽香。
他的脑袋埋进常乐的胳膊,迷迷糊糊念叨着:“阿姊,我没有母亲了,我也不是我父亲唯一的儿子。除了你,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昏黄的光落在常乐脸上,引得她眯起眼睛,露出几分清明,使楚无衣快速别过头。
他的父亲曾夸赞过自己的母亲是大梁最理想的女子,因为她是母族最体贴的长姐,亦是夫家最贤惠的妻子。她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过错,仿佛她的出生是大多数人的福气,唯独是自己的修行。
但是楚无衣认为,常乐可能不是世上最好的女子,但她却是自己最好的阿姊。
因为她的眼睛拥有母亲没有的光,年少时的他读不懂,长大后他才明白,那叫希望。
远望巍巍塔七层,红光点点倍加增; 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各层几盏灯?
楚无衣恹恹地看着平板里张苍捧起《九章算术》,他只能无趣地咬着毛笔笔头,常乐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重复着他不理解的公式。楚无衣看见那些公式只觉陌生,竟无法动笔,常乐气急,抄起一把戒尺向他的背部袭来。
他蓦然惊醒,结果看见常乐面无表情地拍了拍他的肩,只觉一时恐惧。
真是做题前家庭和睦,做题时鸡飞狗跳。
“醒了?”常乐搂住楚无衣,轻声问道。
楚无衣愣了下,点点头。
常乐瞥了眼墙上的影子:“回家吧,老板太上进了,我实在熬不过他。”
楚无衣顿时感觉语塞。
他陪着常乐看了一个时辰的账本。
清晨,耀眼的阳光刺激着常乐的眼睛,她的四肢依旧是没有力气,而且还泛着冷。她喝断片了,不记得发生了什么。那双总是充斥着情绪的眼睛难得涣散了目光,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楚无衣。
楚无衣由着常乐枕着他的手臂,他似乎是怕把对方吓到,小心翼翼道:“阿砚,翻个身。”
常乐一时没有领会过来,当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开始使用“韦砚”这个姓名时,迷茫地翻过身体。
然后一只大鹅狠狠啄向她的额头,并扑腾着翅膀,极其霸道地把她赶下床榻。
常乐虽习过武,但对于大鹅还是有种来自记忆深处的恐惧。在乡下老家过暑假的时候,她带了家里的大黄,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欲对其进行复仇,结果是常乐带着满身的羽毛与伤痕拖着四脚朝天、头顶鸟屎的狗落荒而逃。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带回一只鹅?而且我怎么带的不是一只烧好的鹅?”常乐被大鹅逼得在房间里到处乱窜。
“阿砚,昨天在你聚财楼看了一个时辰的账本,看完了还想吃宵夜。”楚无衣甩了甩被常乐枕麻的手臂,他看着满地的白色羽毛,长叹道,“但聚财楼公厨里的师傅要歇息了,不肯为你开灶。你不服气,仗着会武功,直接冲进公厨抱走了人家一只鹅。”
那只鹅还在门口下了个蛋。
“阿砚,好些没?我给你端来了醒酒汤,直接进来了哈。”早早等在门外的顾落月听见动静以为常乐清醒了,直接推门而入,踩碎了地上的鹅蛋。
蛋黄从破碎的蛋壳徐徐流出,常乐趁机爬上了屋梁,楚无衣慢慢地退却到屋子的角落,只剩下大鹅与顾落月大眼对小眼。
大鹅VS顾落月,READY,GO!
第一回合,一个大鹏展翅,大鹅直接踩在顾落月脸上。扣除对方五滴精血,增加对方愤怒值。
而顾落月不甘示弱,一记鹰爪捆住对方的翅膀。减缓对方速度值,增加对方愤怒值。
这事上竟有人能制服比恶狗还要凶残的大鹅。常乐看向顾落月的眼神,难得流露出一丝崇拜。
“关键时刻还是要看你顾大哥。”顾落月有些得意忘形,还未向常乐展示自以为极富魅力的微笑,就被大鹅伸长脖子啄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