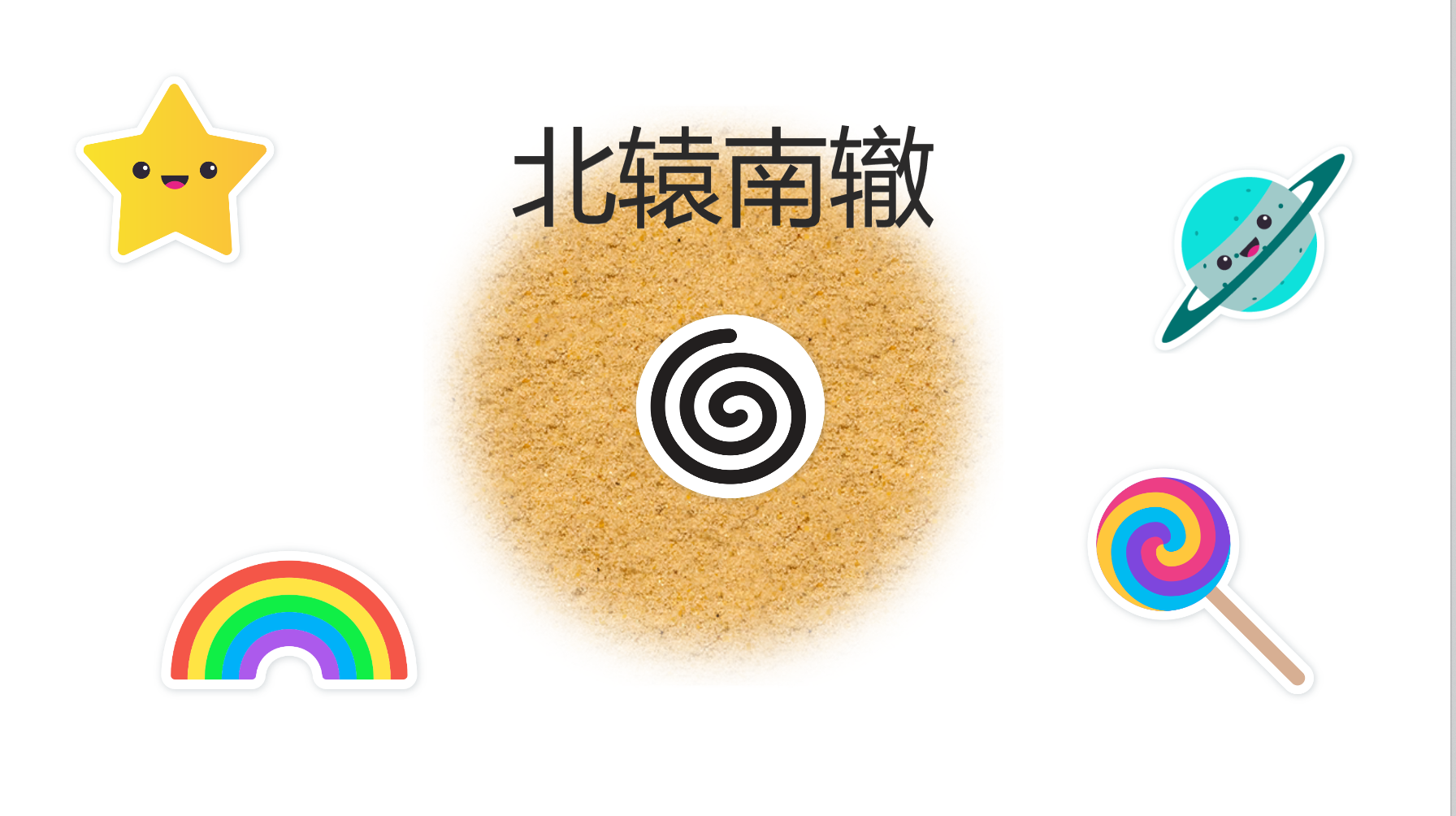“到底什么事,怎么还要拉上我?”乔月站起身来。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那我就是个庸人咯?”乔月走到窗前,从上东银行十四层望出去,可以见到东亚银行和中储行的屋顶,这屋顶之后,就是空空荡荡的税关码头和寂静奔流着的黄浦江。
这间办公室里,一切陈设如旧,属于梁成杰的大办公桌原封未动,一旁梁利群的办公桌上则文件凌乱,椅背上还丢着他的米色风衣。
“这是利群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余笑蜀走到乔月身旁,“我们现在就以他的视角,看看这个无事的天下。”
“他不是去开米统会的咨商会了吗?现在全上海、汪政府、日本人、市民们,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他还能潇洒起来吗?”
余笑蜀看着窗外,又看看乔月,道,“他能,哪怕在当年南京屠城的关头,他也在随波逐流,这个人心里大概从来没有什么家国天下。”
“你确定?那他还跟你借人借枪,他这个米统会副主委,要枪做什么?你也真借给他。”
“就是实在想不出他要做什么,我才借给他。我一个特工总部主任,还不能借出几个特务了?”余笑蜀耸耸肩。
两个人都笑了。
“不管梁利群想要搞什么,高田正夫这次弄出来的动静实在太大了。日本人分明要借着整肃米粮贪污,来重新加强物资统制。东南贸易公司也好,民华公司也罢,统统都要清点盘查,物资线已经断了,交通线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这种时候,我真怕这个心大的人应付不来。”
“是啊,”余笑蜀叹了一口气,“反对清乡委员会的声浪一波接着一波,而且,松泽俊久特别约见了我,跟我大谈时局,现在整个上海滩都人心惶惶,大家都感觉自己被针对了。”
乔月道,“还不是秉南,他就是不认输,除了他谁还能掀起这样大的波澜。”
“除掉了许仕明,日本人算是第一次给了他一个严重的警告,不过秉南又顺利拿到了江苏省**,这令他更不肯回头。”
“你呢?许仕明就这么死了,你不煎熬吗?听说,他还替你挡过子弹。”
余笑蜀摇摇头,没有说话。
“乔月,你上次说,我们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出问题了?”
“是,被特高课监听了,非常时刻,根据地用来和秉南沟通的密码本也作废了,现在我们和根据地的电讯联系完全中断了。”
“换个角度想想,大概根据地很快会派交通员来上海了?”
“大概吧。”乔月的表情有几分惆怅。
“有没有想过,复生也许会重回上海?”
“不会吧,”乔月言又欲止。
“是复生又出了什么情况吗?”余笑蜀察觉到了乔月的不自然。
“嗯,”乔月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复生被甄别审查了。”
“什么?!为什么?凭什么?”一股怒火从心底升起,余笑蜀不可置信地看着乔月。
“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会出现在这样的情绪,身边同甘共苦、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被怀疑,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在敌后,离组织和同志们都太远了,告诉你,怕你动摇了革命的决心和信念。”
“看来组织还不够了解我。”余笑蜀的语气冷了下来,“如果我的信念那么容易动摇,我就不会在四一二之后加入共产党,也不会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为党工作了。”
“你冷静一下。”
“我很冷静!复生在敌后工作这么多年了,上次入狱,是亲自领教过许仕明的手段的,他要是背叛革命,我余笑蜀早就死了一千回了!”
“严先生说得没错,你这个人,遇到复生的问题,一定会怒火万丈。”
余笑蜀深深吐出一口气,缓缓道,“没错,我刚才是有些情绪,我检讨,可复生这样的好同志,究竟有什么问题,需要被甄别审查?我要求组织做一个说明。不然,我没法继续潜伏。”
乔月意外地看看他,道,“你要求组织给你说明?复生亲口对我说过,上次,你也是为了蔡玉珍,和他翻了脸。无论怎样,你也要像我一样,相信党、依靠党,尊重党的决定和方针,相信复生在暂时的休憩后,很快就能真相大白,重新投入到他热爱的工作中。”
乔月这番话,即是“渔夫”说给“矿工”,也是同志说给同志,是同一个人的爱人,说给他的好朋友,乔月的眼圈,红了。
余笑蜀张了张嘴,终于把要说的话都憋回了肚子里。
“笑蜀,我理解你的焦虑,但是,这样的情绪就到此为止吧。这不是专门针对复生的审查,我们在敌后工作的同志们,包括你我,回到组织后,都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这次华中局的整风是延安整风的延续,无论覆盖面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必要及时的。再说,我们的整风审干和国民党那一套不一样,不是排挤苛责自己的同志,而是在诚恳、坦白、正面的态度下,相互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严格检查同志们的思想意识和党性,以便改善党的领导,团结、识别敌特分子。我相信,复生是经得起这样的考验的。”
“好吧,”余笑蜀烦躁地坐回了沙发,道,“你说的对,这一点上,你和复生倒是一模一样,我从来也说不过你们。”
“笑蜀,我才是最担心复生的人,你要相信我。”乔月也坐了过来,道,“这些道理,严先生也做过我的思想工作,但是让我最听得进去的,还是复生。可能因为我也和你一样,不够坚定吧,我的奋斗,大概有相当部分,是寄托在复生身上的。”
余笑蜀有些诧异,乔月,她居然也认为自己的信仰不够坚定吗?
“这会换我不相信了,你怎么会坚持了这么多年,而且,严先生居然放心把银匠小组交给你?”
“大概是我这个人比较浅吧,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不该这样,虽然有很多事情我未必理解得上去,但同志们都相信我,不会背叛革命,不会背叛党。”
“还有老赵。”
“对,还有赵复生。”
余笑蜀觉得心头有些烦闷,打开窗子,摸出烟来。
乔月伸出了手。
“怎么?”
“给我也来一根。”
余笑蜀道,“你也抽烟?”
“是啊,我怎么就不能抽烟?”
“从来没见过你抽烟啊。”
“你没见过的事情多了去了。”
“也从没听你聊过复生。”
余笑蜀给乔月点上烟,她深深吸了一口,道,“那要从秉南说起了。”
“民国二十年前后,那时候秉南和严先生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都活跃在上海文化届,他还没有叛投中统,复生更只是一个文学青年。说来好笑,那时候的秉南很低调,也很有魅力,我对他是很崇拜的,就是他介绍我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入狱,我去求舅舅出面,出过大力。严先生了解我,也是通过他的介绍。对我,我仅有的一些关于党的了解,就是从他们夫妇那里得到的。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是个成熟的革命者了,而我,不过是个热爱文学的报社实习生而已。后来秉南再次被捕,被押解南京,佳兰姐也就此失踪。我在愤怒和失意中,更格外卖力地写起左翼作品,也因之结识了一样带些傻气的复生。”
“这些事情,秉南都没说过。”
“是啊,这和他没什么关系呀,”乔月把一口青烟缓缓吹开,“这是我自己的事。”
余笑蜀看向窗外,点了点头。
“那时候我闷头创作,写了不少东西,复生初来上海,正关心左翼青年的文学动态,看多了我的作品,就慢慢喜欢上了我。”
“那你呢?你不喜欢复生吗?”
“哈哈,开始,还真是没什么感觉,觉得他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幼稚又冲动,看起来也毫不可靠。还好,慢慢发现,他还是挺厉害的。”
“想不到,复生这样谨慎刻板的人,原来也幼稚冲动过。”
“还好吧,他,”乔月似笑非笑,“其实复生的文章写得比我好,不了解的时候看不上他,了解多了之后又开始羡慕他,他总是夸我写的小说好,但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他不搞创作。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候专门搞革命嘛,文学对于他来说是小事,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才是他为之奋斗和付出的一切。我也发现了,讲大道理,我是说不过他的。然后就这么恋爱了,那时候年少不懂事,但是真快乐啊!不过很快,他和秉南一样,渐渐离开了我们的圈子,开始每年多少还能见他几次,直到淞沪战前,他彻底失踪了。”
余笑蜀道,“我知道,他开始潜伏了,那时候和我都在军统。”
“没错,知道他是军统的人,我真是又震惊又痛苦,难以置信。他去了南京,怎么也想不通的我,也追过去了。和秉南不一样,秉南入了中统,依旧郁郁不得志,而复生去了军统,却青云直上。我去了,也生气,也纠结,就拿他过去那套理想追求来反复挤兑他,他被我磨得没法子,终于承认他是奉命潜伏,这一次,最终是我胜利了,我在南京入了党。”
“看不出来,组织性和纪律如老赵,居然会因为你违反了组织纪律。”
“看不出来吧?他是不会承认的,到今天都在说,是因为组织同意吸收我在先,他才对我露了底。”
“我不信。”
“我也不信,”乔月开心地笑了,道,“半年之后,南京陷落,我先走,他后到,都去了武汉,武汉会战,局面越来越危急,我们又辗转去了重庆。当时你已经潜入了七十六号。在银匠意外暴露之后,复生因为和你搭档过,就被派回了上海。那时候我也想要跟回来,但是组织上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棒打鸳鸯?”
“开始我也不理解,觉得是不是因为他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而我不过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我们的差距太大了?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在来到上海之后,终于想通了。组织上这样安排,是因为彼此相爱的同志在同一系统工作,万一出了意外,容易感情用事。何况,那样的痛苦,也太过直接和强烈了。”
乔月的话中带着深深的遗憾。余笑蜀捕捉到了她话中那些微妙的意味,一些早已消失的记忆又重新泛起,他的心忽然就剧烈地疼痛了起来。
“后来呢?”他勉强蹦出了三个字。
“后来,组织上了解到了我和秉南的关系,再后来,我也就来上海了。”
“现在老赵不在上海,这样你也大概可以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了。”余笑蜀不着四六地应了一句,这个话题,他不想再继续了。
“说是这么说,谁又能闲下来呢?省委撤往根据地之后,淮北苏北的反扫荡、苏中、苏南反清乡的斗争都成功,根据地扩大了,也更稳固了。反清乡,我们战果很好,损失不大。这也算你我尽了一点力。可惜,今年和重庆的摩擦、冲突却越来越多了。”
好像心有灵犀一般,乔月也不再谈论感情的话题。
“嗯,德国在苏联受到了重挫,闪电战也闪不动了,英美进入了全面反攻,日本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在中国,我们的胜利大概也为期不远了。”
乔月歪着头看着余笑蜀,“你呢?你的心情好像并没有好起来。”
“我?好心情是什么滋味,我早就不记得了。国府服务十年,在伪府一晃又五六年了,两个政府,如此相似,都是容不下竞争者和制约者的。我总觉得,有朝一日日本战败,内战一定会马上爆发。一想到余笑蜀同志这短暂的一生,都将在战乱中度过,心情怎么会好嘛!”
“怎么会呢?”乔月把余下的半支烟掐掉,道,“笑蜀同志,你太消极了,人的一生这样漫长,还有无数的日子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也有一种感觉,感觉战乱不会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生结局。现在对于胜利后的中国,重庆的态度是模糊的,但是抗战已经死了这么多人,蒋介石真的想再开始一轮内战吗?党的指示,我们和国民党要既联合又斗争,也是为了争取和平建国的局面,迟早,边区武装和新四军一定都会合法化的。到那个时候,成立了联合政府,我们也不用在敌后潜伏了。我还想和复生过几天好日子呢。”
真的有那么容易吗?在千疮百孔、问题重重的庞大官僚机构中,生长出一个全新的中国?
余笑蜀心里有着深深的疑问,但他并没有反驳乔月,只是笑笑,道,“是,你这样一说,我的思想觉悟是该提高了。”
大门打开,上东信托的财务主任王寿春走了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余先生、乔小姐,梁先生请我转告两位,他的事情办得很顺利,现在请二位去聚丰商号一聚,下午两点,他要在那里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
余笑蜀看看表,站了起来,问道,“这个时候,要开什么发布会?他午饭不吃了?”
王寿春道,“少董说,等发布会结束,他再回来请客吃饭。”
余笑蜀转头对乔月道,“利群忙到连午饭都不吃了,这倒少见。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原来梁利群借人借枪,居然直接杀到了周佛海一派的最大采买商家里,这个一贯随心所欲的家伙估计又要捅马蜂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