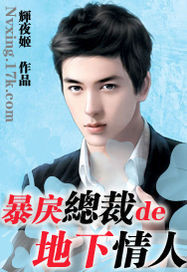自由的意志浸润着光焰与暮霭在空白的地带里来回穿梭延伸了谁的大爱,卑微的大爱守候着虔诚的信仰把救赎与原罪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理性的翅膀承载着乐观与消极在迷蒙的感官里任意翱翔增添了谁的欢乐,简单的欢乐捆绑着悲悯的情怀把安逸与争斗湮灭在了肮脏的污垢中,正义的激情燃烧着亢奋与倦怠在残酷的骗局里上下颤动扩大了谁的良善,孱弱的良善堆积着高尚的道德把真实与荒谬潜藏在了野蛮的游戏中,一切感知到的停靠在遥远的彼岸无法抵达内心的港湾,那些破碎的完整的在泛黄的书页里一次次陷入了昏迷一次次又苏醒了过来。我望着衣衫褴褛的少年终于确定了他具有双重人格,表面上他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实则内心隐藏着一头野兽,我觉得是他内心的野兽杀了那位农夫而不是他,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和众人也认为以前误解了他,我走出村子又返回到田垄的小路上告诉人们那个少年患有精神疾病,真正杀害农夫的不是少年而是那头不受控制的野兽,人们摇了摇头并不相信我的一面之词,他们觉得我肯定收取了那个少年的金币替他逃脱罪责,我辩解说我看到他可怜的模样就觉得应该帮助他免去惩罚,况且他的犯罪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人们望着死去的农夫又望了望黯淡的血红色,一切的原谅似乎都在沉默的回音里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光明……
同情和冷漠交织在一起将虚无的幻梦残留在了现实的荒诞里,虚无的幻梦从黑暗的起点过渡到光明的中心最终滑进了黑暗的终端,勇敢与懦弱掺杂在一起将孤单的魂魄安放在了物质的漩涡里,孤单的魂魄从残缺的血肉延伸到瑰丽的片段最终坠进了残缺的记忆,正义与邪恶碰撞在一起将野蛮的游戏混合在了血腥的争斗里,野蛮的游戏从颓丧的意念游走到理智的边缘最终掉进了颓丧的陷阱,有限的无限的都是自然秩序里的一个部分,感性的理性的都是宇宙精神里的一个原子,那些感觉到的感觉不到的影响着心灵的律动然后间接地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你们要相信我,那个少年是精神病患者,他现在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已经都不记得。”我站在人群的中间,恳切地说。“你这样替他求情只是出于怜悯罢了,我们不会轻易相信你的一面之词,你不要感情用事否则既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别人。”一个渔夫站了出来,沉静地说。“你们怎么为难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病人呢,他杀人的动机是完全不受他控制的,你们如此武断只会让渴望温暖的人们寒心。”我憋红了脸,气愤地说。“你看到他那些异常的表现就确定他患有精神疾病,你除了给他开脱罪责之外并没有拿出什么有效的证据,你的一言一行怎么可能彻底说服我们呢,”一个铁匠伸着懒腰,困倦地说,“我们会联系村子里的医师亲自去检查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到那时所有的谜团都会真相大白。”“我测试了好几次发现他的确具有双重人格,他杀害农夫都是他野兽的一面造成的,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医师坐在少年的床榻边,肯定地说。“我们为曾经的鲁莽行为向他道歉,我们不打扰他了让他好好地休息吧!”人们露出愧疚的神色,支吾着说。“看来我的直觉还是挺准的,总算没有白白冤枉一个好人,农夫的死我们都非常难过。”我擦着眼泪,哀伤地说。
黑夜的忧伤瓦解了幸福的权利在破碎与完满的交错中掩盖了虚假的幻影,虚假的幻影编织着贪婪的欲望任凭暗黑的陷阱埋葬着新生的萌芽,悲观的念想冰冻了自由的意志在高贵与低贱的杂糅中缝合了带血的伤疤,带血的伤疤依附着哭泣的眼泪任凭无声的缄默冲淡着喧闹的印记,混乱的秩序阻遏了前行的道路在坚持与放弃的抉择中封存了阴冷的沟壑,阴冷的沟壑聚集着堕落的迷雾任凭疯狂的感官吞噬着理智的琼浆,一切的努力似乎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然而在另一个维度里却变成了徒劳的结果,所有的真实与梦境让空白中残存着饱满让饱满中残存着空白。人们走进麦田里替死去的农夫挖好了一座坟墓,他们将农夫的尸体从小路上抬到田间进行了入土安葬,坟丘没过多久便像一抹淡淡的愁怨滋生出来掩盖了暖阳的明媚,人们站在麦田里低垂着脑袋仿佛一墩墩雕塑哀悼着悲伤的自己,我为成功解救那个少年兴奋不已,看到人们自责的表情我的虚荣获得了真正的满足,那个少年将我和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一行人邀请进了屋舍,他从厨房里端上来盛好的粗茶淡饭让我们享用,我们吃着简单的饭菜心里却像抹了蜜一样甜,那种难以名状的快乐涤荡在心间将冰冷的气息驱逐到了黑暗的底层……
血红的光焰浸染了漆黑的暗流在希望到达不了的地方制造出了另一种希望,希望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梦魇把正义的旗帜插上了信仰的山巅,悲悯的情怀感化了虚假的面具在真诚到达不了的地方孕育出了另一种真诚,真诚的雨露滋润了枯竭的湖海把和谐的法则引上了道德的范畴,博爱的精神扼制了贪婪的欲念在良善到达不了的地方拼凑出了另一种良善,良善的钥匙打开了仇恨的门扉把宽恕的力量套上了自由的花环,简单的幸福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心,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中早已失去了暖融融的人情味,只留下了赤裸裸的铜臭味。我和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一行人准备离开屋舍继续踏上征程,那个少年也跟随着我们走出来给我们送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要为自己无意杀死农夫而沉浸在悲痛之中,那个少年眨巴着眼睛说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我望着他可怜巴巴的模样问他愿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到达美好的幸福之地,那个少年摇了摇头说自己唯一无法释怀的是人们因为误解我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如果你们在半路上遇见他们一定要开导他们,我对那个少年的话语产生了怀疑,他既然什么都不记得为何还要让我开导那些误解他的人,那个少年知道自己的话语露出了破绽便大笑了起来,他说自己至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人格,野兽的一面才是真正的人格,而温柔的一面都是假装的,那个医师是自己用金币买通的,他明知自己撒了谎却经受不住钱财的诱惑,现在为了掩人耳目自己已经将他杀害,他的尸骨被自己扔进酸液里融化成了血水,我听完那个少年的讲述后感觉自己的身边刮起了一阵冷风,寂寞的影子穿过血红的光色在同情与残忍之间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