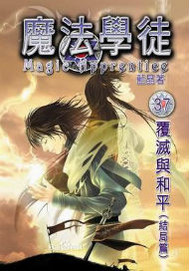黄昏的暗影拂过心灵的码头把黑夜的屏障覆盖在了黎明升起的前端,模糊的记忆挑动着迷幻的感官在意识的波谷里得到了理智的青睐,冰冷的风雪冻住希望的原野把流浪的尘埃堆砌在了幸福凝聚的当口,悲观的情结感染着淌血的疤痕在刀剑的拼杀里得到了积极的态度,贪婪的欲望吞掉星河的柔媚把罪恶的魔爪镌刻在了正义觉醒的背面,荒诞的现实连接着虚构的剧本在平淡的生活里得到了真相的教诲,所有的完美与残缺处在光明与黑暗的两端寻找着平衡的支点,当平衡的支点达到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自我时,所有的快乐与痛苦就是一种随和的幻象。我和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将儿女们从驼峰上抱了下来,两个孩子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早已忘记了困倦和单调,众人迈开双腿好像遇见了久违的甘霖不顾一切地向那边冲去,就在他们以为幸福的花环指日可待时行军蚁从沙堆里钻了出来,一大片一大片乌泱泱的行军蚁爬上众人的脚踝、手臂和脸颊开始了撕咬,前面的众人来不及细想摔倒在沙地上被啃食成了骨架,后面的众人望着可怖的一幕扔掉刀剑纷纷向后撤退,我看着惊恐的众人告诉他们将枯藤做成的拐杖燃起火焰,并吩咐他们将火把对准爬满行军蚁的地面开辟出一条通道,行军蚁望着熊熊燃烧的大火一个紧挨着一个向后逃窜,我和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带领着剩余的众人快速离开了这片蛮荒之地,直到透明的湖水映入眼帘将所有的疼痛化为了心口的朱砂痣……
勇敢的钥匙开启了杀戮的铁锁将慈悲的情怀烙印在了坍圮的废墟上,坍圮的废墟掩埋了光辉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里把星宿变成了泡沫,忠贞的信仰感化了罪孽的欲望将救赎的力量释放在了脆弱的血肉上,脆弱的血肉腐蚀了高尚的魂灵在暗黑的骗局里把至善变成了妒忌,恒久的幸福缩短了孤独的距离将无限的欢乐镶嵌在了冻僵的残雪上,冻僵的残雪冰封了温暖的春天在荒凉的寒冬里把未来变成了回忆,一切无法圆满的片段都在时间与空间的夹缝中拼凑着故事的里里外外,那些凝固的幸福潜藏着冷漠的想象让你倚靠着我让我倚靠着他。我和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一行人将所有的水具装满了月牙湖的水,然后我们跳进湖水里洗去了全身的尘土和酷热,众人拍打着水花让清凉的感觉穿过脉搏渗进了每一块血肉,我抱着儿子站立在水中央望着延伸到地平线上的暮色,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拉着女儿的手一步一步靠近了对面的浅滩,我们将沙漠带来的苦痛全都抛弃在湖水里兴高采烈地上了岸,接着我们望见了不远之处忽明忽暗的叶子和树影,我们睁大眼睛发现了沙漠里生长的沙棘和红枣,众人撑开布袋把丰硕的野果一大捧一大捧装了进去,我们收获了所有的果实在幸福的大道上又唱起了歌谣,美妙的旋律淹没了风暴的怒吼让光明冲破暮霭涤荡到了天边……
远方的幸福还是那么飘渺但我们不怕艰险
凝重的夜幕会撕裂光亮但光亮会积聚本善存活下来
我们虽然孤独但我们充满梦想
在简单的日子里平凡编织着复杂的世界
我们高举着信仰的旗帜一直走到天明
以梦为马的生涯也许是一场逃亡也许是一段美好的旅程
灰暗的阴影侵占了光明的领地后继续掠夺着微弱的希望,希望的田野聚集了简单的幸福在杀戮的残局里等待着光明的降临,流浪的尘埃堵塞了正义的出口后继续瓜分着朦胧的星河,星河的银辉浸染了缤纷的美梦在漆黑的夜色里观望着正义的觉醒,锋利的刀刃斩断了信仰的旗帜后继续摧毁着博爱的力量,力量的天平均衡了单一的重物在混乱的规则里改变着信仰的冷暖,希望不是梦想的开始却成了堕落的终结,星河不是光明的起源却成了黑夜的毒药,力量不是勇敢的斗志却成了退缩的幻影,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朝着真实的镜像和虚假的模具的两端移动,没有短暂的停歇只有永久的循环。我和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带领着众人经过漫长的跋涉终于走出了沙漠,沙漠的边沿隐隐约约坐落着一片静寂的村庄,我们行走在平安村的街市上听到教堂里传来了唱诗班的歌声,稚嫩的童音回荡在村庄的上空仿佛污浊的心灵被雨雪冲洗了一样,我们观望着漫天的柳絮让血红的光焰重新回到了黑色的瞳孔里,那双灵动的眸子掩盖了孤独的气息在喧嚣的激情中会聚了美的一切,我们嗅触着浓郁的香味在花瓣与草丛之间一次次寻找着自己一次次迷失了自己,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穿过乡村把模糊的诗意烙印在了未来的图画上,我们踩着厚重的石阶将古老的记忆从过去拉回到了现在,现在的印象粘连着繁华的景致在正确的地方感知到了虚晃的幻梦,我们走走停停不愿错过亮丽的风景线又不想忘记坎坷的朝圣路,突然我们听到一声惨叫从某个屋舍中传了出来,我们没有多想加快步伐朝着那个方向狂奔了起来,只见一个男子手趴着门框一点一点倒在了门前的血泊之中……
真实交织着虚假就像飞驰在天边的暮霭和光焰,一半凝结在忧伤里一半燃烧在明媚里,节制约束着贪婪就像藏匿在沟渠的死水和花香,一半深埋在恶臭里一半飘溢在芳馨里,仁慈搅动着残暴就像堆积在心田的感性和理智,一半搁浅在平庸里一半封存在高尚里,复杂经历了简单的锤炼拥有了世俗里最好的规矩,最好的规矩扼杀了人的天性让疼痛埋藏在了博爱的深渊里,一切得到的总以为是自己最想要的,回头却发现最想要的永远在路上。“我的丈夫为何会惨死在屋舍之外,他的死肯定与你们脱不了干系。”一个女子摇晃着这个男子,急忙从外面赶了回来。“你的丈夫不是我们杀死的,我们听到惨叫声本想救他一命,可是看到满地的鲜血我们知道已经来晚了一步。”我望着血泊中的男子,替我们辩解道。“凶手肯定是你们,你们不要推卸责任,我的丈夫浑身是血死得好惨啊!”这个女子趴在男子的胸脯上,大声哭喊着。“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我们赶过来时你的丈夫已经倒地身亡,真正的凶手可能早已逃之夭夭。”我的妻子花仙橙水瑶安慰着这个女子,耐心地分析着。“你们既然死不承认我就去找村长分辨是非,等他查明真相后你们就免不了要遭受牢狱之灾。”这个女子低着头,咬牙切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