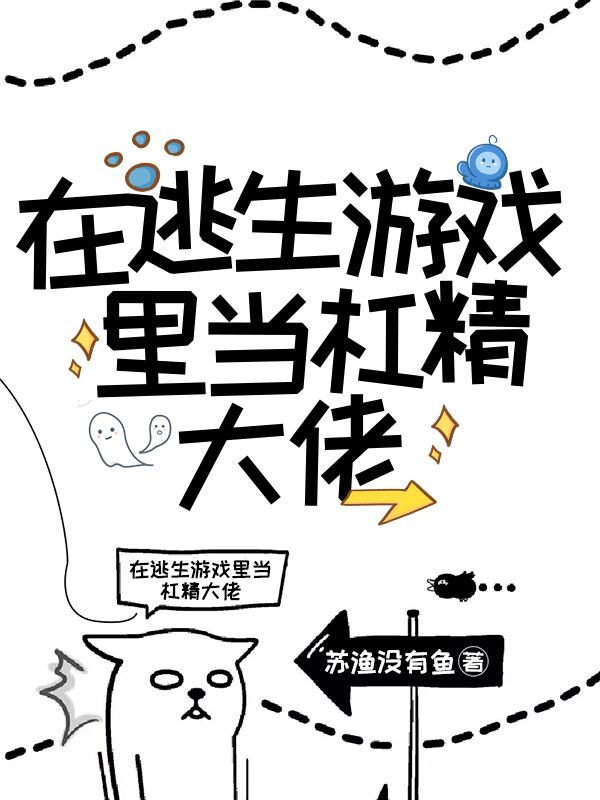倾语只身坐在桌前,面前盛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汤,热气微氲,却无法融化开他那霜冻般的面部轮廓。他握着汤匙的右手微微有些颤抖,身上的伤处一阵又一阵地抽痛着,而胸口那个完好跳动的地方,却有着比伤处更深烈的撕绞!
这是一碗,她亲手为他熬的药;
也是一碗,送他上路的绝命汤!
“丫头,你当真希望我喝了这碗药么?”倾语强笑着,有些哽咽地向妆衣问道。
面前的药汤略带酸涩,只一闻,他便知道药里下了毒。而这毒药他恰巧又最熟悉不过,正是二百年前他被强灌过一次的‘乌夜啼’。那种苦中带酸味道在他的脑海里,伴着关于夙桐和那个人的记忆,清晰如昨日。
本以为已深藏于心底的事情,如今又一幕幕清晰地席卷而来。
他期待她能说点什么,说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只要她说,他就一定相信。但妆衣只是用怅然地笑笑,对他说:“快喝了罢,再不喝药就凉了。”
她真的不想这样做,但她又必须这样做——
耳际回响着阿弥的话语:“倾羽如果继续待在这儿,那他一定会死。”
她不要他死,她要他好好的活下去!
活下去。
哪怕……没有她。
妆衣红着眼,尽量甜美地对倾语微笑着,虽然不管她笑成什么样其实都没多大的干系,但她很害怕,害怕这是最后一次对他笑了。她在药里加了阿弥给她的‘十日醉’,等他睡着后阿弥就会带走他,从此天各一方,上穷碧落下黄泉,恐怕也再难有相见之日。
她是不愿再和他在一起了吧?她心里一定是气他一直在骗着她吧?他什么也给不了她,甚至那日在城外差点还带她带来危险,他什么都没有,过的不过是朝不保夕的日子,更许诺不了她所谓的幸福……呵,幸福?连他自己都没有东西,又怎么许诺给别人?
他不过是个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甚至——甚至连人都不是!
“丫头,不管今天你做过什么,要记得……这一切都是我愿意的,你永远也不用内疚。”
妆衣只觉得心口仿佛被利刃刺了一下,霍然抬起头来,他知道了么?他都知道什么?他知道她在药里放了会让他陷入昏睡的‘十日醉’?
“以后在教坊里,自己还是多长个心眼,天字号有个叫莹衣的,你且多加堤防,另外对于自己屋里的人,也不可过于交心……”他想起小柚为他查过之前鞋底藏针那件事,轻声说道。虽然他觉得她如今有了现在这番心思,应该已经根本不用他来提醒。
原来他真的知道……妆衣心头一紧,莫名的冷意爬上她的背脊,他竟然知道她在药里下了十日醉的迷药!可他为什么不责问,为什么不反抗?难道真的如阿弥所说,他深谙人妖殊途,心里想着的也是要离她而去?
胸口有些淡淡地撕痛,她低头沉默着,听他继续说下去——
“卫疯子这家伙虽然说话不着边际,却是个靠得住的人,但今后关键还是要靠你自己……”
他抬起空茫的眼眸,悲哀地‘看’了她最后一眼。
“如你所愿。我喝。”收回那深情的凝视,倾语从无尽的哀痛变成了淡然地笑着,他不再多问,只是端起那碗药,开始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他喝药的样子很好看,可能好看的人干什么都是好看的。
嘴里传来的,是熟络如二百年前的酸苦,心头浇灌的,却是比二百年前更陌生的灼痛!
因为她是她的妆衣,是他最离不开的妆衣,是他最放不下的妆衣——
是他最心心念念的妆衣!
——只要她要,只要他有。
哪怕如今,她要他死,他也绝不会做半分的迟疑——如果这真是她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么他愿意接受这份她亲手捧给他的死亡。
命运对他何其慷慨,让他在死的时候都还能喝上自己心爱的人为他所熬的汤药……
他应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吧?
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仙逝的祖母曾说过,千万不要去触碰人类的感情,那是世间最危险的东西,因为他们只需短短一瞬,就能轻易毁灭你冗长的一生。
没有听祖训是可怕的,他现在终于明白,但为时已晚。
只是,这一次,不会再有一个夙桐来替他吸走身上‘乌夜啼’的毒了。
落雪了。
他轻轻放下手中已空可见底的碗匙,起身往门外走去。
“不要走。”妆衣忽然起身从背后将他环腰抱住。她抬起头,极力控制着不让眼泪流下来:“陪我一会儿,一会儿就好。”
但倾语没有过多的理会,只是极温柔地将她的手拿了下来。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他疲倦地说道,语气也是极温柔的。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入了外头那片白簌簌的大雪之中。
单弱的身影渐渐行远,只在苍茫的世界里留下一记萧瑟的符点。
“不……”屋内,妆衣无力地瘫坐到了冰冷的地砖上,顷刻泪如雨下。
他每走一步,她的心仿佛就碎裂掉一点。
就这样,她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出畅音阁,走出她的视线。
走出,她的生命。
落雪自辽旷的天际蹁跹而下,纷纷扬扬,铺天盖地的静寂中,依稀可以看见那个人离开时留下的轨迹……雪地上的脚印还残存着某人身体的余温,像是一场最清晰的眷恋,只等时间来将它结成伤疤,最后无声掩埋。
白雪皑皑,余生茫茫。
乌夜啼,啼别离——
旧日繁华尽,娇花洒落千重。
春犹未到身先老,独教坠幽丛。
君梦还如妾梦,妾心不与君同。
从今月下难携舞,至死不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