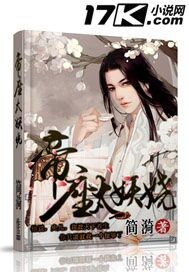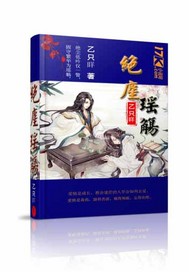小书童童言无忌,梁智铭笑而不语。
只有倾羽一直不知道妆衣正在女扮男装,听到这话便没来由的感到一阵莫名的喜感。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妆衣长得什么模样,不排除这丫头雌雄莫辨的可能,可是明明就是个女孩子,非要说她长得‘像个’女孩子?
“她本来就是……”倾羽刚想纠正,妆衣已经踮着脚一把捂住他的嘴,笑嘻嘻地说了一句:“我们本来就是来吃饭的,刚好这衣服也脏了,梁老板,不介意我们去你店里换套干净的吧?”
“当然,当然。”智铭是生意人,听妆衣这么一说自然是满心乐意,伸手往门边一引道:“二位里面请。”
妆衣大摇大摆地挽着倾羽就往馆子里走。
“不是说这家店的人都很可怕么?”他小声问她,“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因为我看那个梁老板……”妆衣说着偷偷回头瞧了一眼,只见智铭正被那群粗犷女子围着,高瘦的身板上一颗脑袋显得特别圆大。
确定智铭离他们有一段距离,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后,妆衣这才鬼鬼祟祟地附在他耳边说了一句:“那个梁老板的样子,真的很像个冤大头。”
……
二人进了店门,沿着大厅中央的旋转台阶环璇而上,见少东家智铭在后面跟着,馆子里的人自然是纷纷退避,所以妆衣也走得特别大摇大摆。偶尔有几个端酒托菜盘子的侍婢从他们身边走过,看他们颜好也都是一路飙着媚眼满面娇羞。
妆衣只能一路躲啊躲,心中大汗这个梁老板雇佣侍婢的眼光真是与众不同。
两人上了楼梯,到了二楼的一个开阔处,妆衣四里张望着,很快地找到这座‘铎戈食府’中的琴台所在。
只见在楼梯相反的方向立着一道圆拱形的香木隔屏,下方左右相对地蹲着两只彩塑狮子。圆屏内是一个微高于地面的木榻,里面坐着个五六十岁的老琴师,方才二人在门外听到的那首塞外胡谣就是从这里弹奏出来的。
拱门外有一口红瓷大缸,名曰聚财盆,是安川的习俗,用以客人打赏,里面浅浅地装着一层碎银子和钱票。木塌周围一圈都摆放着香气宜人的时令鲜花,屏门两侧还分别挂着一条木对,上书:睡草屋闭户演字,卧樵榻弄笛声腾。
妆衣第一眼看到这对联子,心中暗赞了一句好漂亮的字,不免将连上内容轻念出声,但她念完之后立马就拉黑了脸,连一旁的倾羽听了都将手握着拳放在鼻下轻咳了两声。(读者亲们,看不明白的多念两遍,这里有内涵-。-)
“你念的这是什么鬼东西?”倾羽皱着眉问她。
“呃,屏门上的对联……”妆衣表示很无奈。
“两位喜欢这对联子吗?”不温不火的声音再度从身后响起,智铭已经被一群侍婢围着从后面迎了上来,一脸陶醉地自卖自夸道:“实不相瞒,拙作正是梁某自己写的。”
倾羽只能又咳嗽了两声,不置一词。
“呵呵,原来如此。”剩下妆衣无可奈何地干笑了一声,打圆场道:“梁老板的词作真是内容饱满,一……”她想说一鸣惊人,但话到了嘴边忽然觉得太犀利了,不妥,于是腔调一转变成了委婉的:“一语双关啊。”
倾羽觉得妆衣真是特不容易。
智铭是播月城出了名的学究,平时最喜欢附庸风雅地收藏一些诗词字画,自己心情好也会书上几张,然后得意洋洋地挂在店里供人看赏。不过因为水平中庸,因此少有人对之夸赞,听妆衣这么一说,他自是心花大开,兴奋道:“这位小兄弟果然独具慧眼!所谓知音难遇知己难求,二位若是喜欢,在下这就叫人把联子拆下来送予二位如何?”
“……咳咳。”倾羽本来越狱出逃伤势就没全好,听完这话差点没把肺腔中的一口老血给喷出来。
妆衣也是给智铭震惊得嘴角微微抽搐,按捺住性子忍道:“君子不夺人所好,如此个性之作更应好好藏之,梁老板的美意我们心领了。”
智铭呵呵一笑,经过之前的一番折腾,他现在已经莫名地对妆衣和倾羽充满了好感。海内存知己,两个来自南方的异邦之客,却能看懂他并且欣赏的诗作,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见两人还站着,他又殷勤道:“楼上还有雅厢,两位请随我来。”
“不劳烦梁老板。”妆衣笑着指了指拱门旁的一张临窗小桌,拒绝道:“就坐这儿吧,我们刚好想听听曲儿。”
智铭瞥见倾羽背上背着个大琴袋,估摸着大抵也是懂琴的人,刚好他自己也有这种对感兴趣的事物倍加留心的习惯,于是也欣欣然表示理解。
两人走到窗边坐下,桌上摆着一个琉璃花瓶,插着一长一短两支蝴蝶兰,而窗框边上的墙面上,又挂了一张画。这幅画可谓用色张扬奔放,整张纸全是明晃晃的黄色,妆衣愣是歪着头看了很久,才明白原来这幅画画的是彩霞满天,菊花遍野。
这回妆衣很是识趣,看完之后只是咽了一口唾沫,不做任何表态。
在智铭的示意下,提着茶壶和早就准备好菜谱的高壮侍婢恭恭敬敬地迎了上来,一面斟茶一面把菜谱往二人面前一摊,“二位随便看看,要吃点什么?”
只瞄了一眼,妆衣就被菜谱上那同样明晃晃的菜名和价格给亮瞎了!——
大葱蘸大脓、狼心狗肺、沙仁如麻、骨肉分离、盐刑烤打、豆你丸……
妆衣觉得这家威武无比的‘铎戈食府’简直就是在考验她的心理承受能力。
倒是倾羽很自然地和那个又高又壮的侍婢交谈着店里的特色菜式,先问了店里有什么比较好吃,然后在那个侍婢的强烈推荐之下,几乎是把最贵的那几道每种都全点了一份。
那智铭只当这两个人是有钱的主儿,所以招待得也特别殷勤,不但催厨房给有限张罗,还特地差人去对街的裁衣铺里给妆衣买了一件干净的新衣裳换上,然后就乐呵乐呵地暂辞了二人又到楼下拉客了去。
“他走了。”妆衣小声地提醒倾羽:“我们开始么?”
倾羽提着茶杯轻抿了一口,说: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