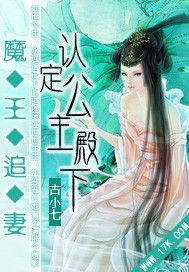灵夕回到租住的小房间里,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欢愉,她并不感到孤单,独自一人住在异乡房间里的经历,她有过很多次了。找出一件旧棉布衫擦竹席,已经是傍晚,洗过来不及晾干,只好用湿抹布擦洗。
洗好坐下来吃超市买来的全麦吐司面包,切片面包上看得见麦麸颗粒,但灵夕知道这当然不是纯正的全麦面包,纯正的全麦面包口感粗糙,不被大众接受,就连改良过的,似乎也不太受欢迎,至少灵夕没发现过身边有人喜欢吃,她们对她说,“这样干的没有味道的面包,你为什么喜欢吃?”,或许自己老了,灵夕想,只有年轻才寻求味道的刺激,而她已经承受不住,高热量食品会让她的身体燥热不安,她的身体还是只能适应从小被母亲养成的清淡温和的饮食,不习惯吃辣,酸,甜腻食物,但是小时候惧怕吃苦瓜,现在反而喜欢吃,咖啡的苦,巧克力的苦,她都喜欢。仍然记得一种牛甘子,味道真正的“苦尽甘来”,苦味之后,一阵甘甜,拇指头大,白绿色,圆核上带着软刺疙瘩,在集市上已经很难见到了,是她念念不忘的野果子。
她吃了三片,削了一个苹果,就是今晚的晚餐了,三片是走路了一天适合的量,再多就会胃胀不舒服。中午的米粉不合适她的口味,一股油腻味道,她没有吃完。与粉相比,其实她更喜欢吃面,湿面尤其喜欢,细细感受有淡淡的麦香味,但在南方小城市,很少有卖挂面的店,卖的面就是伊面,油炸得过度,酱油色,除了浓重的咸味再没有其他味,而且油汪汪的,只让人感觉到吃了一碗味精调味。
她带了一张很薄的毛毯,一张棉胎被套,照这个天气,晚上一定冷,她今天没有买被子,也不想再出去了,在网上看棉胎,填地址的时候不知道,截图问周峰瑜,他告诉她,因为是截图问,他看到了她买被子,说网上买要等几天,夜里会冷,叫她去超市买,她应了,但没想去,但是天一直没黑,她也不知道做什么,夜幕降临的时刻,发着呆,又是在异乡,太容易感伤,她觉得还是离开房间。
在路上走着也很奇怪,还是往超市走去了,她看了被子,适合的最便宜的九十九元,她还是没买,她不确定在这里住几天,找房子时,她已经预感到她不会待得太久,一股湿腻感让她融不进去这个环境。
她已经很累了,想早点睡,但是睡不着,她起来写信,不知道写给谁,没有知道她的近况,可以不用解释现状直接说话的人。但她还是写了。
此刻接近零点,我在异乡,一个寂无人声的房间里,我很累,但是无法入睡,因为很冷,清明刚过,仍旧凄冷,而我没有厚的被子,只有一张很薄很薄的常年带在身边的毯子,一张淡黄滑面被套。
我来到这里是打算在这个陌生小城里工作,生活,甚至报考了这里的图书馆秘书职位,但是在此刻,我感到深深的孤单和害怕,原来即使我就算考进去了,也还是不敢在这里定居,融入小城市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从前我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并不感到孤单,我喜欢那种孤独感,但这次竟然与以往不同,我终究还是有了些变化。
我跟一个实习时认识的朋友说“我明天去找你”,这是我在这里,感到很冷的这里,不至于放声哭泣的支撑。
把所有退路都想过一遍,都是十分艰难,我知道这是做自己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我知道往后的路非常艰难,也对这后半生没有希望,也许没有好起来的可能,我必须做好这种准备。
我真正感到社会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该做的已经没有热情,田园已没有,家也不适宜再停留,我该何去何从?
写得有点累了,也许能睡着了,灵夕睡下了,半个小时多过去了,还是冷得睡不着,她又起来了,开热水器水还有点温暖,她接了半盆,把双脚放进去泡着,尽管不够热也觉得舒服。
关灯时说一句,“不管生活如何艰难,也要熬过去啊”。
早上听到此起彼伏的关门声,流水声,知是人们起来了,或上班,或日常生活,灵夕看到窗外的天光,迷糊中说一句“天亮了”,又继续睡去,整个晚上,只在这一刻能好好睡一下,她仍记得,凌晨三点四十四分,最冷的时刻。
九点钟她起来了,清洗过后,仍然是全麦吐司面包,呆呆地坐着,一点一点咀嚼吞咽,是很享受的时刻。
她写昨晚的梦,或者是早上的梦。
我看见妹妹哭泣,但没有问为何,应该是工作的压力,像自己很崩溃的时候。尽管就一起坐着,但通过打字交流,才知道她做南瓜泥是幼儿园的工作任务,要求学会做好吃的南瓜饼,当时我竟呵斥她有闲心做吃的,心境又回到和母亲在一起时,特别窘迫的时候,妹妹当时竟不辩解。
去一个什么地方,走在路上,她的头包着白纱布,问她,说是哥哥打伤的,我怒火烧起,去呵骂笠柯,他是童年时候的样子,瘦,穿着膝盖处打补丁的棉布裤子,被我呵骂,哭得颈项青筋暴现,母亲又打骂他,比我更甚,直至打他的头,对他说不要他了,快步走了,把他遗弃在路上,那条山路,周围全是茅草,只有很小的路,是小时候去做活的地方,他的哭,和小时候因担子太重而发怒大哭的情景一模一样。
她打骂他,走得很决绝,在小孩眼中是真的不要他了,他摸着被打痛的头站在小路上大哭,我回去找他,告诉他,他没有被丢弃,他擦了眼泪,抽噎着跟在我后面。
不时做梦回到童年,那段贫穷,苦难,不安的日子,对一切不满,又无力改变一切,常常是在母亲的发怒声中上山去,或下田去。其实母亲并非无端愤怒,是我的落魄与不满,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满,对抗的方式是与母亲对抗,与农活对抗。但多年后的今天,终于发觉,我所有的心平气和,皆是从无休止的锄田中习得,从锄草中习得。
或许是母亲装的担子确实重了,以她成年人的方式来衡量,她的不重,已经重。或许是当时身子太单薄了,无论是担柴,担木薯,扛木,担茅草,总是一上路就哭着责怪母亲,一半原因一定是吃不了苦,怒气转向母亲,总是把担子摔在半路上,捆的柴草松开丢掉一半,以这样决裂的方式对抗,而母亲由开始时的安慰,好言相劝,好说歹说,到最后被激怒,一路上就这样不欢而回。
而制造这一切的多是我,弟弟并不如此,妹妹也并不如此,弟弟纯真,爱玩,不计较一切艰苦落魄,只是跟随大人做着一切,他专心玩,对苦难无觉知,梦里的他大哭,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被发怒的母亲牵连,突然被打骂,被告知抛弃。他对生活,人生没有不满,只是在悠悠人世中对大地,一切生物充满好奇与兴趣。
贫穷,匮乏,哭泣,不满,无力,这是深处隐藏的记忆,它是我的前世,是底色,是印记。
下午灵夕出门,在一个人工湖边环湖而走,一般景色,碧绿的水,齐整的柳树环湖而栽,翠色的叶子,涂上白石灰的根部,已经近在市区闹市,空气还是非常好。这就是小城市的好处。
要上桥回去了,才看到一处种植花草盆栽的“植物超市”,倒很有点诗意,看花草总是让人愉快,灵夕看着地上种的多肉类植物,原来有这么多种类,插着一个小牌子,写着它们的名字:世之雪,雨燕座,玉珠莲,紫阳,白凤,因地卡,黑法师......灵夕看得入了迷,一路看进去,恍然间不知置身于何地,仿佛在一个仙境中,她知道她要到去一个朋友那里去,但她恋恋不舍的不肯离去,其实心里也是想多挨些时间,朋友在上班,去早了不好。
她不确定公交车到车站要多长时间,也还是提早回来,在路上感到饿了,早餐到现在也没吃东西,好容易找到一个粉店,螺蛳粉辣,桂林米粉昨天中午吃过不想再吃,要了老友粉,老友粉在她心目中的印象一直还是高中时和敏华去吃的那家,木耳,香菇,还有那么多块鲜瘦肉,她在学校的伙食极其差,新鲜瘦肉从来没有,炸过的肥猪肉皮和豆腐煮,瘦肉难得的有一两颗,也不是新鲜的,一次她去敏华学校,她从食堂打饭出来,灵夕看到瘦肉鸡蛋,才想到原来自己学校的伙食有点差,她一直没注意。
她说不要辣的时候,老板娘告诉她会有一点点,灵夕接受了,也没有别的可以选。煮上来就已经感到不对,果然吃了第一口就呛得不行,以为是自己太长时间没吃东西或没讲话,喉咙不适,再吃两口还是辣得吃不了,她看到对面一个男人在吃粥,她去跟老板娘要一碗粥,她让她自已舀,她在忙着切小菜,灵夕舀了半碗粥汤,想就着粉吃就能吃下去了,一碗粉没吃实在浪费。付钱的时候,老板娘仍然收了她五块钱粥钱,灵夕这些地方在别人看来总是很傻的,总替人着想,然而人们是粗糙的,草率的,细腻是难以被注意到的,甚至是被故意忽视的。
她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坐火车,看着车窗外朦胧的天色,有种凄清感,是万物归家而浪子无家可归的心情,她竟然觉得安心,她不懂。
到了L市,天色已完全黑下来,方莉说她也正要下班,顺道过来接她。车站广场灯红酒绿的,大屏幕上播着广告,热闹的人,似乎飘着几点毛毛雨,倒像寒冷的冬天,方莉骑着“小电驴”在人行道树下等,灵夕拖着皮箱绕过去找她的位置,皮箱的笨重似乎是去投靠亲戚,她出门时母亲说先不带这样多东西去,工作也没定,她真后悔没听,她是抱着一去不回的心出门的。
是实习时认识的朋友,那时实习生一起去吃饭,饭有些干,灵夕胃不好,吃得很慢,吃快了胃就不舒服,别人都吃完走了,只有方莉等她慢慢吃完一起走,周末灵夕大早起来去办公室里,看电影,忘记去吃饭,方莉从宿舍过去食堂,总到办公室叫她一起去。方莉喜欢网购,灵夕也常陪她走路出去拿快递。
后来很少联系,倒有一次说过去找她,没去成,灵夕几年来很少出门找朋友。
见了面也很自然的说着话,笨重的箱子还以为放不上车,她的“小电驴”还搭着防风衣,冬天时防冷的,还没拆下来,箱子很重,灵夕心里非常抱歉。
她带她到一个面馆里吃面,这个城市比灵夕过来的小城繁华,北方人来这里开面馆,也算吃上挂面了,漂着几片薄薄的牛肉,撒了许多绿葱花和香菜,方莉让伙计切了一盘烧饼,她说泡到面里很好吃,灵夕试了,也还喜欢。
方莉预先跟她说,到了家里“妞妞”认生会朝她叫好一会,但不用怕,它就是吓唬人,虚张声势而已,灵夕笑了说:“应该没关系,”她不怕狗。
小电车进了一个城门似的大门,里面是热闹的菜市,更多的是在卖水果,往里拐没有路灯了,感觉到在一排低矮房的小巷子里停下来了,方莉把车放到矮房子瓦房里,带灵夕上了对面的楼梯,这一带的房子很古旧,灵夕也很能理解,普通的外来教师,在一个高消费水平城市里扎根,终究还是不容易。
正在上楼梯,已经听到狗叫的声音,在拼命爬着门,果然一开门闻到陌生人气味,它叫得更凶,方莉捉住它,灵夕提着皮箱进门,门阶有点高,方莉的母亲过来帮了她一把,灵夕同她打了招呼。妞妞挣脱了跑过来,灵夕站着,它直往她身上窜,灵夕转头不看她,感觉得到它的爪子在刮她的牛仔裤,方莉无法,去拿了它的零食来,是一支牙膏样的膏状食物,她挤给它吃,它果然安分下来了,方莉笑说它是个吃货,灵夕也笑了,方莉又让灵夕喂它吃,和它熟络起来,灵夕喂着它,它舔着“牙膏”头,发出声音,坐下来后才闻到它的气味。
怕它胖不能再给吃,拿走了,它也不闹,这时候算是熟络了,且一直跟你套几乎,攀到灵夕的膝盖上,到怀里抱它的姿势,灵夕侧着腰,环着手臂,她今天穿带领的开衫毛衣,乳白色,黑色镶边,很担心被它的爪子抓出毛来,灵夕想躲却无处可躲,它涎着舌头,似要舔人,方莉叫它它也不理,说:“你有洁癖吗?上次我表姐来,她有洁癖很介意它碰她”,灵夕勉强笑着:“有一点,但现在没洗澡它爬一下没关系”,方莉还是说等下洗了就回房间里,不给它进去,“她会跟你睡吗?”,灵夕问。“不会,床高它上不去的”。灵夕放心了许多。
她坐了一会去洗了,去到哪妞妞都跟着扯她的衣服,像要人关注的小孩。
灵夕洗出来了,逃到房间里关上门,开门的时候它还是进来玩,向着你叫,要跟它玩,方莉说你别理它,不然以为你跟她玩,她就没完没了了。
她带很重的皮箱,是打算不再回去租屋了,那阴湿的环境。
但是她跟方莉说她明天要去找一个朋友,在G市,方莉很惊讶,“怎么才来就要走?”,灵夕抱歉着笑说趁她在休假,和她去玩几天。
聊到很晚,就一直上厕所,灵夕简直怕出门,妞妞听到开门声从阳台外冲进来,拉扯你的衣服,穿着拖鞋,非常怕它舔她的脚,它的爪子刮到她的脚。
早上她们已经都去上班,灵夕起来开了房门,妞妞冲过来,热情不减往她身上蹭,她逃进卫生间关上门,她闻到它强烈的气味,她想起方莉昨晚跟她说厨房里有面,可以煮来吃,坐密封空调大巴车的感觉马上回来了,一阵眩晕。
她下了楼,不太确定方向,昨晚回来天黑看不太清楚,问一个卖水果的阿姐,她很热情的告诉她公交车站的方向,她一再道谢,不禁说“这里的人真热情”,阿姐笑说:“欢迎再来玩”,灵夕微笑着走了。
她犹豫要不要回出租屋放下行李再去找曼君,最终决定直接去,她改了票,离开排着的队伍,她才感到饿,近十二点,早上是什么也没吃,她包里带着苏打饼干,开了一小袋,还是感到晕眩感,看到二楼有吃食店,反正改签后也还有时间。
吃了一碗南瓜小米粥,她非常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