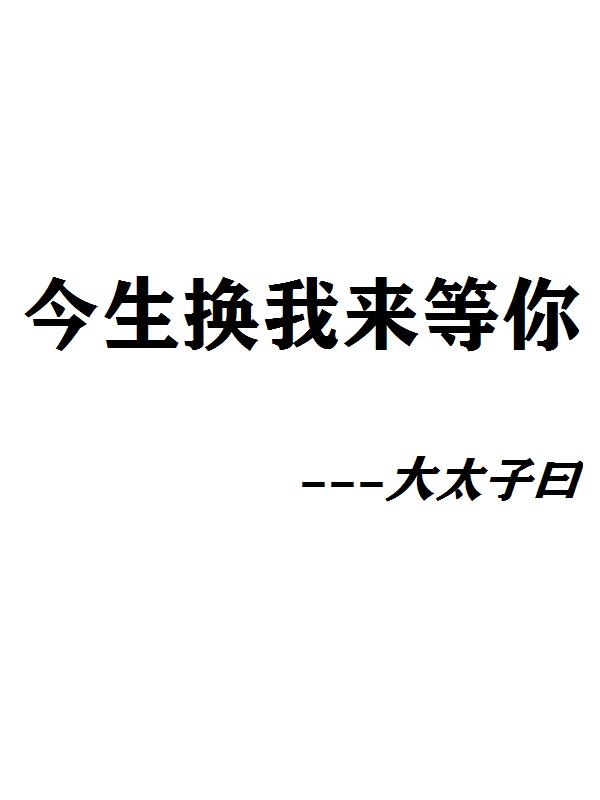灵夕母亲回来了,不知道去做什么,总是零碎的农活,她叫灵夕摘门外菜地里的空心菜来煮,灵夕很快去了,她洗澡。
菜没择好,她洗好下来了,坐在门口扇凉,灵夕问她上次在哪里摘石蒜苗,她说做什么,灵夕说煮鸡蛋,她说不好吃的,她不喜欢吃,煮把青菜得了,煮多吃不完。灵夕也没说什么,她总是自己不喜欢就否定了别人喜欢,但灵夕想了想还是要煮点鸡蛋,头发掉得那么多,想着等下自己过菜地里看,刚才没想起来。
择好把菜拿回里面洗,不然她一定要说灵夕在外面洗,水倒掉浪费,在里面洗就可以留着水冲卫生间,尽管农村不至于这样节水,但从整个地球看,节约用水也挺好的。她母亲还是问:“洗过了?”。灵夕回道:“没有”,她知道了她是回屋里洗,说道:“在外面洗一次再回去洗嘛”,灵夕说洗过一次了。
洗好了菜,灵夕到菜地里看,没有石蒜苗,看到小时候煮汤水的豆苗叶,摘了几根,和鸡蛋煮。
厨房里蚊子叫得很厉害,灵夕出去点蚊香再回来煮,她母亲坐不住,进来看见灵夕没把豆苗叶子摘下来,说她连梗也不摘掉,其实她已经摘了一根放在那里,不过是出去点蚊香了,但灵夕懒得跟她争辩,她母亲又说她把梗都洗了干什么,灵夕说顺手就洗了,看她母亲的语气像是灵夕洗了梗浪费了非常多的水。
她母亲的语气带着怒气,她也有怒气了:“洗多了几根梗到底会怎样的?”,我真想不明白了,这都要计较吗?接着又说:“又叫我来煮菜,又来抢着做,叫我来干什么?”,她母亲缓和了一点:“你炒菜去”,灵夕开了煤气,她把叶子切碎了,怕灵夕整张煮,其实也才拇指大的叶子。
灵夕用盘子接了一点水,烧开,她在边上说:“烧一点就好了,烧那么多”,灵夕也打算只烧一点的,把盘子里剩下的一点水倒掉了,她母亲又说:“清水都这样倒掉,留在盘子里等下洗锅不行吗?”,“等下放菜盘子也还是要倒掉啊,就倒掉那么一点”,灵夕无奈的语气。她母亲说:“为什么要用盘子接水,水瓢做什么用?”,“为什么非要水瓢才能接,用盘子就不行了?用盘子接还不用再洗一次盘子”,因为前面说得有点愤怒,后面那句让氛围和缓一点。
她们始终在极力避免严重的争吵。
水烧开了,灵夕抓菜放到锅里,她母亲看到了,“油都没放就放菜了?这样菜要变色”,明明是这样才不变色,相悖的理论,急得懒得解释的心情,把菜一翻过来给她母亲看,“你看变色了吗?这样才是不会变色的”,从前问一个厨子怎么炒出那样翠绿的空心菜,他说先滚水里过一下再爆炒,仗着这点,她把她母亲看得很无知。
她母亲又看到火候不够,说灵夕开煤气开得太大,火苗窜走了,浪费了煤气,锅里又不燃,本来水煮的青菜就爆炒不起来,也因为煤气火候没有从前柴灶旺,才水煮,保持翠绿。
她母亲又是这套理论,认为火候不够旺是煤气开得太大了,听到她这种反人类反物理的理论,灵夕气就不打一处来:开大了都不够旺了,调小了就会火候旺吗?又如她母亲认为烧一壶水和烧半壶水要的电是一样多的,她总是用她的无知认为别人是错的,她是对的。
“你出去行不行,叫我来煮又要来指点,不如你自己煮好了,你就是有一种控制欲,要别人都以你的方式,别人做事由别人的方式,你不管行不行的?”上次就已经这样说过了,还是这样,又讨厌地再说了一遍。
青菜炒出来了,灵夕把鸡蛋打到盘子里,和刚才她切的叶子搅拌,她母亲大叫且愤怒起来:“你疯了吗,这样打鸡蛋进去?又不是葱花这样能熟啊”,灵夕也愤怒,但不形于色,“你不吃的,你管我怎么煮做什么?”,“你这样说就是不给我吃”,她是真生气了,“你自己说的吃青菜就行了”明明心里不是希望她不吃,灵夕就是不想被她指点她的做法。
她出去了,生气地坐在门口扇着风,过一会才进来舀饭端菜,“你的事我不帮你做,我也不要来管,各做各的,你们这样的想法!”,末句把“这样”拉得很长,灵夕知道她的意思是亲情冷漠,一家人各做各的,各自不沾边。
他们在灵夕小时候起就是争吵,冷战的多,似乎从来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他们以为他们小不懂,小孩子的眼睛冷清清地看着这一切,印在他们的记忆里,成为一生的印记。
从小父母和孩子没有建立起连接,他们长大了,终究难以和他们亲近。他们如果没有在饭桌上感受过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注定隐藏着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一面。
灵夕阿婆又到她们家住了,又轮到她们家照顾她,但她过来第三天,又病了,像之前几次一样,老毛病复发,从前她病灵夕都不在家,没见过她病的样子,这次陪在她身边看着她受苦,父亲又回不来,心焦得什么也不能想,自己的事也只能搁在一旁。
从前工作从早忙到晚,不知一天怎么过去了,一周怎么过去了,一个月怎么过去,回家停下来,忽然有一天看着时间数字跳跃,惊觉一秒钟跳得这样快,眼睁睁看着它一跳一跳,时间的流逝,什么也没留下,有什么方式可以留下点什么?从未有过的对时间的焦虑感。灵夕开始记录,在每一个发呆的时刻,记下看到的,感受到的一点什么,随时随地,她没想过要对抗时间,她或许只是茫然。
她最痛苦的时刻应该是全身瘫软,发烫,声音突然停止,闭着眼睛,伯父强力扶起她,慌忙着,说“迟了迟了”,他是说给药吃给迟了,烧起来了,心狂跳起来,觉得阿婆很像要走了,轻声呼唤她,观察她,伯父不看她,要把药灌给她吃。
下车的时候,她还在疼痛着,喘着气,两天不进食,虚弱得只剩半条命了,但是抱歉着对司机说,没来得及封一个红包给他,说她是病人,封个红包吉利,我对她说我父亲给了,不用操心,她才安心。其实她是司机的媒人。
伯父让她在检查外伤的病房里一张床上躺着,因为他们上次来就是在这张床。后来医生让移到隔壁房间病床,那是专门打点滴的房间,阿婆打了针,又打一瓶点滴,疼痛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对她说我们移到隔壁房间去,扶着她艰难地起来,仍然问,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了?她的意识很清醒,没有表现出对周围环境、人事不管不顾。
在寻找空床位时,有人轻声叫我小时候的名字,一看是从前的邻居敏嫂,她陪同她婆婆来,也是打点滴,在里面长椅上躺着,她在走廊长椅上坐着等待。她说以为不是我不太敢叫,我说戴着口罩也许不太看得出来,但是心里想着我也老了,她说也是太久不见了。忽然她整个脸都红起来,我尽量不看着她,朝里张望她的婆婆,说:“人老了真是难啊”,她也说“是啊”,只简单交谈了几句,便去找床位了。
原来之前看到有点像的人,真是她,当时想着她怎么会在家,一定是有点近视的眼睛看不清楚。避开了不细看。
小时候,去和她住过一晚,还有她的孩子,还很小,孩子父亲不在家,她说有天夜里听到窗外有声音,非常害怕。
曾借她的一张CD来听,似是刘若英的专辑,不确定。
上高中,假期回来到她家楼顶玩,她问我:“只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太孤单了?将来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帮助”,告诉我她的婆婆劝她再生两个。我说不会,他的堂兄弟姐妹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会帮助他。
她现在是三个孩子,还是四个?和农村大多数人一样。
常常是很长时间后,想起说过的一些话,觉得天真,当时完全不知道。
四瓶点滴滴完了,疼痛还是没有得到缓解,但是医生已经下班了,她忍着疼痛等下午上班。
伯父说知道医生的名字后,他想起来了,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他到过医生的村里运材料,和这个医生谈过天,只记得他当时说的一句话,“在镇卫生院工作”,“我记得他,他不记得我了,那时他还很年轻,二十几岁,现在看来有五十多了”,他说。
伯父从前养一匹白马,帮助别人运送建房子的砂石。他现在的工作是帮助别人养猪。
医生来了让去照b超,在二楼,我想到阿婆上来一定精疲力尽,伯父会不会背她上来?但是伯父也老了,更危险,我想下去试试看,走到楼梯,已经喘着气上来一半楼梯多了,只好扶着上来,她好不容易走到走廊的椅子,坐下来大喘着气,头埋在臂弯里。
结果出来,胆结石发炎。
疼痛消缓一会,又发作起来,她转过身来说,“这样痛怎么过得了这一关?”,我默然。说不出安慰,我心里想这把年纪还要受这样的苦,宁愿安详地没有苦痛地好好离去,最难的是,偏偏这口气不断。
父亲会不会是一时收不到钱,觉得回来也没用?还是要核酸检测回不来?汇给他两千块钱,说万一阿婆怎样我也还有另外的钱,不用担心。他没领。
伯父在电话里和人聊天,说到三姑姑年轻时做活很拼命。从阿婆,父亲,姑丈,姑姑的儿子等人口中听到类似的话,三姑姑有口皆碑。
我告诉阿婆明天还要来,她说明天伯父要卖桂皮没有空了,下一天又要去工作,耽误他。
伯父让我们在后等姑丈送刺荔枝来,等很长时间,非常不耐烦,事实上非常累了,折腾两天,早起,睡不好,饥饿,抱怨伯父答应要,小弟已经说好不去摘了。
但是心里想着,不管怎样等会姑丈来了,一定不能表现出等了很长时间的样子,他这么远送过来。
姑丈来了,欢喜着说:“姑丈你终于来了”,“等很久啦?”他笑问。“大概一个小时吧”,我竟然实话实说。他大笑起来,抱歉的样子,我说:“是挂了电话到山上摘了送来?”,他说是啊。啊,这下到我感到非常抱歉了。
他要请我们吃粉,我们不吃,他掏出钱,捺了一张红色的递过来,说给阿婆,我不拿,他塞在车上,又捺出两张十块给我和弟弟,算是吃粉钱,非塞在我手上,我已经让小弟开车走,想放开手里的钱,怕被吹走他要弯腰捡,他喊着“不要放手!”。只能远远喊着“辛苦了姑丈”,他远远回着:“不说辛苦!”
昨晚深夜,迷糊中听见伯父过来询问阿婆,阿婆耳朵聋,话说得很大声,其中有一句“我这边耳朵也聋了”,在深沉静谧的夜里飘荡。伯父七十二岁,他的母亲九十五岁,他对她感叹或倾诉“我的耳朵也聋了”。
我到的时候护士把针拔出来了,伯父在压着针口,他告诉我肿起来了所以拔,护士拔完走了,老不来,他又去找来,又重新针上了,他说他也去找医生看看耳朵,把他耳朵突然听不到的过程告诉我一次,说是昨晚刚洗澡出来,耳朵嗡了一下,流点水出来,周围的声音就不很听得到了。我像是刚知道听得很认真。
他去一会就回来,说没想到今天这样多人,以为是端午节人不会在今天来,我笑说病痛就不管节气了。他说人多医生看不准的,因为匆忙,我只笑笑,他又出去了找医生了。
好长一会时间才回来,一小袋药让我放到阿婆的布袋子里,问是他的药吗?说是,看了耳朵后医生开给的,说买药花了17.4,挂号费十块,只能报销几块多。我忽然想问办理有残疾证在医疗上没有特别照顾吗?但是没问,我不太确定他是否办理有,似乎堂弟提过一下,实在不记得有没有了。他的一边眼睛在上小学时一次发烧,失明了,只用一个眼睛看,他昨天踢到一个木板凳,骂了一声把它移走了。
他说要出去找药店买药给阿婆,出去了,要我很注意看药水,滴完了叫护士来,其实我坐着也不看手机,他还是叮咛一下才走。
对床是一对年轻夫妇,女人在打点滴,看起来十分痛苦,躺下后眼睛一直没睁开,男人在床边,抓着一个布袋口,一会才在床边坐下,忽然女人说想吃点粥,男人出去了,在门口回头确认:“只要清粥吧?”,女人没动,他出去了。
刚出去没多久,女人醒来,叫我帮移垃圾篓过去给她一下,我把阿婆床底下套着黑色袋子的垃圾篓移过去给她了,她马上吐了出来,我马上想自己呕吐后,最需要什么?因为没有水,在她吐得差不多了,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模糊地说了声“谢谢”,翻回身仰躺着,仍闭着眼睛。
男人回来了,喂粥她吃。
点滴停了,叫来护士,拔了针搁着,看来是药水进不去,又要重新扎,两边手扎了四五处针口,肿了或黑了。
带她去小便,又看到敏嫂,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
对床护士问女人要拔了吗?女人点头。她的头晕没有缓解,决定到市里医院去,男人扶着她走,来了医院,看到很多是夫妇同来,或是妻子陪同丈夫,或是丈夫陪同妻子,年老的,或年轻的。
忽然发现垃圾篓的黑袋子不见了,是男人刚才拿去扔了?护士应该没有空也不用做这个,这个时间也没有清洁阿姨来。
伯父回来了,他去了很长时间,告诉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父亲说的那间药店,但是要买的药没有了,关于药的价钱,他说比我父亲说的价钱更贵。后来回家看到药盒上写的和药店卖的是一样的,原来是我父亲记错了,发现这个解答了他的疑问,他似乎很高兴。
听他提过年轻时有过一小段时间卖海带,他对事物的价钱很感兴趣,他的口算能力比我们读过很多年书的后辈要好,他保留着贫穷年代精打细算居家过日子的品质,从前的人这样热爱生活。
他说,早上请的摩托车司机是从前认识的人,昨天刚巧遇到,“我不记得他了,他记得我”,那人当时到村里做征收木头的生意,来过我们家住和吃粥,后来到过他家去,他父亲是卖猪肉的,有点钱,送了我三匹布料。
本来喊W伯骑车送来,他不肯送,说这样老了,他不敢送,叫去找有汽车的司机,“老人就是受不住汽车才找摩托车”,他说得很平常,没特别表现W伯不肯帮忙的不快。他们从前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一起打牌。
他昨天遇到的“老友”存了电话刚好用上了,对方不帮忙后他打了电话,请他到村子里接送到卫生院,“钱不紧要”,那人对他说,“但我们也肯定照数付”,他说。
车开到院里的台阶前,是壮大的老汉,头发白了,并不老,很热情,“开慢一些,辛苦了”我说。
记起堂弟说过似乎他父亲认识的人很多一样,到哪都能遇到有半点交情的人。从前的人见过一面也是交情。
二姑姑打电话来,阿婆在病床上对她说,“帮我问问能过今年吗?”,二姑姑信佛。
下午祭祖的时候,她能自己起床了,颤巍巍走出来说要洗个澡,病了两天没洗。她问,“龙王酒洒在屋四周了吗?艾叶晒好了吗?”,端午节的习俗。
从前的一个学生问我还在学校吗,想带西瓜给我吃。
清晨,坐面包车到镇上,车里老人年龄七十岁左右。忽然看到车窗外两个小女孩牵着手上学。
三个妇女肩挑装粥锡罐,到山上做活,像农村二十年前轰轰烈烈的干活时代。
腹部隐隐作痛,胃胀,背部,腰部,手臂,全都胀痛,整个人不安乐,难捱得过一日,早上,阿婆这样告诉我。
大多数时间不得睡,迷糊中做了一个梦,梦见那边是下大雨天气,浑浊滚急的洪水从她面前流过,她似乎常做下大雨的梦,之前梦见离去多年的阿公,也是下大雨。
腹部还是久不久痛一阵,胃部感到非常热,我碰她的手臂,小腿,却是凉的,“全身感到软”她说。她记得从初三开始病,意识很清醒。
我说让伯父修一根拐杖给你用,她说好,走路艰难但至今没用拐杖,她现在病着,也勉强到厕所洗漱,洗身体,有时忘记带拐杖。
那天夜里,问她开着灯睡如何,她说不用,房门也不用开着,怎么能做到在病痛中仍不惧黑暗和隔绝境地?
“痛的时候愿死去”
“有条路让我去就好了”
半夜痛得很要紧,“喊你们起来又有什么用?该吃的药也吃了,反正也是痛了”
和她坐久了一点,就说:“你去看书吧,不用陪我坐了”。
帮她捶背一会,说:“可以了,你也累”。
“身子很软,今日比昨日更软”,扶着她去小便时说,“小便都要人扶,顶没用了”,她一点不感到理所当然。
扶她的手臂,松塌塌的冰凉的皮包着骨头,生怕握痛她。她侧身而卧给我捶背,突出的肩骨头,像是和身体分离的多余的一部分,妨碍在那里,让她翻身像翻不过去一座岭。
听到她喘息声就下去,生怕是感到难受无力叫得出声,常常是因为起床费力而喘息,她说你下来这样巧,我正想小便,我说我听得到,今晚告诉她,夜里疼痛或要起夜叫我,我能听到,她应了。
总感到胃部灼热,放一瓶凉水在腹部降温,劝她喝水:“多喝点水就能把热气排出来了”,她太想能够舒服一点,难以吞咽也喝了下去。
她不想吃任何东西,“难吞得下去”,吃药片却从不需要哄,她很相信吃了药就能好。
每晚八点半叫醒她起来吃药,有时她睡得迷糊了,“还要吃什么?”以为是叫起来吃粥或是喝水,竟完全忘记了吃药。帮她扇蚊子,下帐子,把帐子塞到席子里,她说:“每晚你都辛苦了”,我一惊。阿公走的前一晚,叔叔问他有什么想对阿婆说,他说她辛苦了。
相敬如宾,不单是夫妻间,普及到子女子孙,在审视父母的婚姻的同时,常常拿阿公阿婆对照,他们如何相处,怎么对待彼此,我得以学习。
她很正经喊我的名字,我一震,以为她要交代什么,
“我很想看到你出门(嫁),不然实在不愿做人了”
“你出了门弟弟再娶进门就更好些”
“不用担忧,儿孙自有儿孙福”,但她听不清。
她才终于不痛,每次吃半碗粥,常常回房躺着,没有精神坐,这天看到两个脚水肿了起来,她让婶婶找她房间里的一支冲剂吃,我看了,不过是滋阴补气的保健药品,不是消水肿的药,但她坚持说从前吃了这个消了。后来是吃药才消了。
外出一周回来,听她们告诉我:
才消了水肿,她的腰扭到了,洗澡的时候挪了一下那桶水,或许没想到已经这样没力气,她痛得要去诊所打针,但已经傍晚,医生已经回家。她忍了疼痛挨了一夜,向来“病了也只得自己受着,没人替得了”。
一个星期不见,她更瘦,只是一个骨架子,一边肩膀高,一边低,左肩膀下凸着弯骨头,两腿,两手,只是一层皮包着里面小小的骨头,她躺下床的那瞬间,你有种一不小心全身骨头散架堆在床上的感觉。
她的心性变得很坏,讲话变得没好气,问她腰还痛不痛,“这是什么话,当然痛!”
医生终于来打针,她说要打三针,医生当然不敢打,她寄希望打得多就能不痛。
还说要去打针,一定还是痛得不安,但是没有人可以车到小诊所,听说她很生气,在她的立场看,儿孙很不为她着急,无人可以体会她的疼痛,她心态很差,讲了一些气愤的话。她挪步也要出去打针,她果然挪步出去了。
她一定想到,她这样受着病痛,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她的疼痛无人真正着急,连出去不远的小诊所也无人可以车出去。
她们告诉我,她那天从厕所里出来,裤子没有拉上就出来了,但她竟浑然不觉。
听着这些,脑子总响起一句完整或不完整的话,
“哪知老境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