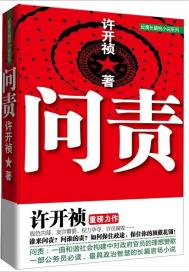“你没死?”路小花瞪大双眼呆呆地问。
“你是认为我死了才哭的吗?”那人眉头往上一挑,冷气森森。
自己是因为他死了才哭的吗?嗯……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反正刚才就是想哭一下嘛。路小花脸有点红了,不敢看他的眼睛,目光下移,忽然发现他拿剑的手似乎紧了一紧。哎哟!这可是个有剑的江湖人啊,江湖人可都是喜欢胡乱杀人的,该怎么回答他?她瞥见手中的篮子,急中生智地说:“你不是要吃的吗?我给你送来了。”
“哦?”那人的手缓缓地松开剑,慢慢地从路小花的篮子里取了一张面饼,咬了一口。
路小花觉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似乎也被他咬了一口,大气不出地紧抓着篮子。
那人将饼在口中嚼了一会儿,费力地咽下,皱眉道:“饼太干,再给我送点水来。”
路小花瞟着他,小心地说:“我还给你买了酒。”
“我不喝酒,给我水。”那人沙哑地说道。
“马上来!”路小花如蒙大赦,转身就跑。
那人望着路小花的背影,眼里闪过一丝莫名其妙。这个小姑娘刚才好像还因为他死了而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怎么他没死却像见了鬼一样害怕地跑走了呢?不过大多数人见到他都是这个样子,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他冷然地想着,将长剑归鞘,继续闭目调息。
路小花拼命地往家里跑,到家里拿起水桶,从缸里舀了半桶水就又往回跑。刚才实在是太丢人了!打从父亲发疯离家不归,她大哭了一场,发誓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活下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大哭过了。怎么今天忽然哭成那个样子,关键是还让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看了个够!路小花越想越羞,越跑越快。
喝过路小花打来的水,那人精神似乎好多了。他抬起头紧紧盯着路小花的脸看。
路小花不由自主地使劲擦了擦脸,莫非刚才哭花了脸?想起刚才自己哭得那么可笑,她恨不能马上变成只兔子跑掉算了。
看了她一会儿,那人忽然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路小花说:“你家在哪里?带我去!”
“嗯?在那边。”路小花从困惑中解脱出来,指了方向,起身带路。
“等一下!”那人又说。
路小花停下脚步回过头看他。
那人犹豫了一下,下巴一抬,冷硬地命令道:“扶我起来!”
哦,对了,这人受着重伤呢。路小花马上过去扶他。
路小花一手扶着那人站起,一手拎着水桶和篮子。嗯,这样可真有些难度。别看那人坐着的时候觉不出高来,可站起来还是满高大的,路小花大概也就刚刚到他的胸口。好在那人并不把全身重量放在路小花身上,他一手撑着剑,一手扶着路小花,饶是如此,二人也走得踉踉跄跄,直走到天快黑了才回到家。
哎哟喂,可算到家了!推开院前的篱笆门,路小花吁了一口气,擦了擦满头的大汗,转头问那人:“我叫路小花。你叫什么名字?”
“徐绍风。”那人从泛白的唇中吐出这几个字后,眼神一滞,搭在路小花肩上的手一软,整个身子跟着就往下滑去。
路小花“哎”了一声,可一只手根本扶不住他,他一下子倒在地上。
路小花一惊,连忙放下水桶和篮子,双手扶他。只见他双目紧闭面色惨白,头无力地垂在一旁,显然已经昏过去了。
好重!路小花奔走了一天,现在正是浑身没劲的时候,使出吃奶的劲去抬他,可是他比路小花长了好多,路小花好不容易将他抬起,却发现他的大半个身子仍赖在地上。没办法,路小花只好绕到他的身后,双手抱在他的腋下,把他从院子里一直拖进屋内。
啧,可真够沉的,也不知是吃什么长大的!路小花虽说是自小就自食其力,可从来没搬过这么沉的活物。一路上小心翼翼的,生怕磕碰了他,到得屋里,已经累得一头大汗,一下子坐倒在地上。
要先做什么呢?看着他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伤口,路小花真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啧,江湖人干嘛总把自己弄得这么惨兮兮的。
嗯,好吧。先把他搬到床上吧。总不能让一个受伤的人就这样躺在地上吧。路小花准备把他搬到屋里唯一的大床上。
一抬手,路小花看到手上脏脏的黑印,不由愣了一下。她转头看向床上的小花床单,虽然已经用了很久,但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当初可是千挑万选的啊。……嗯,算了,还是先把他身上的脏衣服脱下来吧。这衣服又湿又脏的,对受伤的人来说总归不好。
路小花解了他的披风放在一旁,再去脱他的外衣。左手这边倒不算费事,但他的右手紧紧地握着剑柄,衣服根本没法脱。路小花想把剑从他的手中弄走,可他的手握得死紧。没办法,路小花只好去掰他的手指。刚费力地掰开食指,突然长剑“当”地一响,出鞘寸许长,本是躺着的人忽地坐起,怒气冲冲地瞪着路小花。
诈尸啦!路小花只觉全身寒气嗖嗖,吓得往后一跳,结结巴巴地说:“你穿湿衣服不行,有剑,衣服不好脱。”
徐绍风“哼”了一声,将脱了一半的外衣从剑上甩了出去。回头看见有床,一撑掌就坐了上去。路小花根本来不及反对,事情就已经发生。我的小花床单哎!路小花低下头绞着手,在心中哀哀地叹着。
面前寒气袭来,路小花一抬头,正对上徐绍风冰刀一样的目光,只得收拾起悲哀,挤出一个笑脸,刚想说“你想躺就躺吧”,却见徐绍风头一歪,人又倒了下去。
路小花愣住了。过一会儿,见他确实不动了,这才再次上前。
先伸手在他的面前晃了晃,没有动静。再伸手戳了戳他的身体,还是不动。路小花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推动剑鞘,直到把他的剑全都收进鞘里,这才松了口气。
什么玩意嘛,这柄剑又重又沉,一点儿用没有,偏他死不放手地握着,真是个疯子!路小花越发觉得这些江湖人令人难以理解。
这人里面穿的大概是一件白色的内衣,但因为染了血和泥,变成了黑红相间的花衣,顺便把小花床单也染上了泥血花。路小花鼓起腮帮又气又恼地瞪着他,这些江湖人到底知不知道挣钱有多么不容易啊!
二话不说,路小花立刻动手去解这件罪魁祸首的衣服。然而,这件衣服因为伤口上的血水已经粘在身上,根本就脱不下来。路小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么重的伤这人怎么可能还活得下来?她光是看看就觉得疼得受不了啊。从这点上说,她还真是佩服这名江湖人,好像一点儿都不怕疼不怕死。
歪头想了想,路小花取了把剪刀对着床上的人说:“生病的人是不能穿湿衣服的。你这件衣服脱不下来,我只好把它剪开了。”
床上的人紧闭着双目没有回答。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路小花决定算他答应了,小心地把衣服剪下。
然后她烧了一大锅热水,用一块干净的布蘸上热水,轻轻地擦洗他身上的伤口。当一盆热水变成黑红色后,就被路小花倒出屋外。一连倒了七、八盘水,才把他身上的血迹洗净。路小花又从床下拿出珍藏着的草药给他涂上。
整个过程中,床上的人一直一动不动,路小花生怕他已经死了,三番五次地去试他的鼻息。他的鼻息虽然一直是轻飘飘、慢悠悠的,万幸的是总还是有的。路小花总算把心放在了肚子里。路小花一边弄一边数,总共17处大小伤口,把她这阵子储备的草药差不多全用光了。
终于弄完了,路小花累得手软脚软,床上有人躺着,她只好坐在床边的地上。真是累人的一天!她趴在床头再也不想动了。
虽然累得没有一丁点力气,但救人的感觉说不出的美好充实,她即自豪又满足地长长地舒了口气,欣慰地看着床上的人。
床上的人脸色苍白如纸,两道上扬的剑眉蹙着,鼻梁挺直,薄薄的唇紧紧抿着,双目紧闭,几缕发丝无力地垂在额前,完全没有刚才那副冷冰冰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个无助的孩子。
唔,如果他不老是板着脸看起来不算难看呀,想起刚看到他时他那双可怕的眼睛,原来闭起来就大不一样了啊。
伸手把他额前的发丝捋到脑后,路小花继续欣赏自己的“杰作”。胸部和腹部的伤口完全弄好了,只要不再破开,希望能慢慢的好起来。她的目光慢慢下滑。天啊,他的腿!一道深深的刀痕从大腿侧部一直延伸至膝盖,深得几乎可以看见白花花的骨头。刚才他是怎么跟着她走回来啊?路小花大吃一惊,不过这个江湖人已经给了她太多的“惊喜”,“惊喜”得她都麻木了。
哎!接着弄吧。路小花认命地继续给他包扎,顺便再查查他的腿下还有没有别的伤口吧。救一个人可真不容易啊。难怪庙里的和尚们总是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简直比造浮屠还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