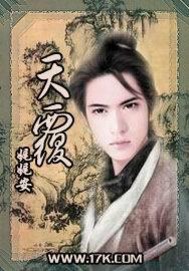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哥,前面就是南京了吧?洪武帝的陵寝,应该还在吧?我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这次应该好好拜祭一下洪武帝吧?”
朱林骑在马上,侧着头向朱崇祯问道。
朱崇祯摇摇头,“洪武帝的陵寝空置了这几百年,恐怕这时正热闹的厉害。我们自然要去,却是不能和这些人一起去。”
一旁载泓听到这番对答,不自禁的乐了,“没想到你们朱氏子孙,连拜祭一下祖宗的陵寝,都要这么小心翼翼!难不成是顾虑我们在吗?”
朱崇祯苦笑一下,却不再接话,打马上前,那南京城,已经就在眼前了。
走到近前才发现,这南京城门下,挤挤挨挨的已经排了很长的队,隐隐的还有哭声传来。有些人排到了城门口,不知怎的,没过几个呼吸,就听见城门口几声长长的尖叫,几个人四散奔开,疯了似的逃去。紧随其后,闪出几个兵丁的身影,有几个端枪上膛,冲着天下就“砰”的一枪,大喝道:“再跑,就要你们的命!”
那几个人跑到半途,就被枪声吓住,一会儿就乖乖的走了回来。那兵丁们骂骂咧咧的说道:“跑什么跑?不就是要剪个辫子吗?当奴隶当惯了是不是?要你当人还不会当了!赶紧过去剪了,后面还老多人等着呢!”
朱崇祯一行人见到这等情状,互相看了看,打马上前,来到城门口的文告区,纵目看去,却见上面的赫然贴着一张剪辩令,令上赫然写着“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方信孺见到这等文告,嘿嘿一笑,冲着旁边的白发德豪说道:“这文告,还真有点当年睿亲王多尔衮剃发令的意思!”
德豪长叹一声,“天道循环,真是报应不爽!”
几人也不排队,驱马直闯到城门口,却见王文庆早已在那里等候。有王文庆相引,一路无话,一行人不一会儿便进了城,这一路上煞是有趣,不时看到一队士兵跟在一个穿着皮袍子的人身后,有时还碰的上两队兵丁相互火拼,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在那里用广州话叫骂……林林总总,难以描述。不过这一路走来看去,南京城果然无比繁华,尤其是两楼——酒楼与青楼,门口竟然有许多靠着墙根排队等着进去的兵丁。
这南京城的种种乱象,王文庆显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一路上,他见朱崇祯的脸色越来越差,心中知道不好,便迅速挑了一间酒楼,上二楼寻了靠窗的一处雅座,众人团团落座。
甫一落定,方信孺便笑着向王文庆说道:“王兄,这南京城如今重做都城,真是好生热闹!这一路上我听过来,至少有着十几种的方言,看来这南京城,如今真真算是群英荟萃,风云际会了!”
一边的载泓却轻笑道:“六朝繁华如梦,不知道这一场梦,又能迷人到几时呢?”
朱崇祯却无这等玩笑之心,端起茶盏饮了一杯,沉吟了一会儿,却对王文庆问道:“马雷如今在何处?”
“去了海军那里,如今海军人心不定,各方都在拉拢。萨镇冰有些弹压不住,云堂恐怕海军牵涉到变乱当中,失了根本,就亲自去了!”
“他不在,南京城你就弹压不住了吗?”朱崇祯冷冷问道,一股怒气随着声音,慢慢荡漾开来,压的王文庆头上满满的都是汗水。
“公子,我……”王文庆张张口,想要说些什么,还不及说出,就又被朱崇祯打断。
“孙文建府我不管,我只问你,如何这南京城如此混乱?”朱崇祯越说越怒,一掌狠狠击在案上,“沿路我听闻,王金发占了绍兴居然称了大王!我只问你,光复会规矩何在,你们当这是在唱戏吗?!”
“对对对,我说怎么觉得少些什么东西呢?”二楼中间一处桌上忽然有人接道:“有酒无歌酒不欢!酒家,酒家,你们这里有没有唱曲儿的?早听说秦淮风月甲天下,如今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卖命,总要听一次才不白来!”
酒楼伙计麻利的一声喊,不一会儿自楼下窈窕的走上来一个歌姬,怀中抱着琵琶,冲着楼上众人施了一圈礼,便撩拨琴弦,在那里唱了起来。随着这个歌姬的歌声缥缈,楼中逐渐清静了下来。
一曲歌罢,不过数息间的功夫。那一桌点曲的,像是某地来的富商,穿的绫罗绸缎,富丽的很。为首的一个,长的有些粗豪,听完一曲,拍着桌子就大声赞好。
歌姬听到赞声,便起身冲着那桌低身一福,旁边有伶俐的小厮,便一路过去收钱。谁料想正是这时,那粗豪的汉子忽然站起身来,一把推开小厮,走到那两个歌姬前面,低头看了几眼,哈哈的笑起来:“这南京城的歌娘,果然不一样。白,而且滑!我说,你们也别卖唱了,随我李三刀回去吧!以后荣华富贵,少不了你们的!”
这情景,想来那歌姬已经见的惯了,也不急也不恼,站起来对李一刀轻轻一福,轻轻说道:“李爷看的起奴家,本是奴家的福气,可奴家家中还有老父老母需要奉养,几个幼弟也还未长大,奴家实在离不得金陵。”
听到这等解释,李三刀脸上瞬时便怒色腾起,“我李三刀等闲说的出这种话吗?这是看得起你!父母幼弟算什么,一并接过去,还怕老子养不起吗?”
“养得起?”一旁桌上,也有一群相似穿着打扮的人,见李三刀这般模样,哈哈笑道:“李三刀,你凭什么养得起这等如花似玉的歌娘?是凭你在广东的横财?还是凭这一路发的飞财?”
话音一落,楼中便是哄笑一片。那李三刀怒气上脸,红似关公,右手往腰间一摸,“砰”的一声,砸在桌上,歌姬拿眼一瞥,顿时“啊”的一声惊叫,转身想跑,慌忙间却带倒了椅子——李三刀砸在桌上的,赫然是一把手枪!
“老子凭的就是这个!”李三刀环视当场,一副睥睨天下的样子,“老子手中有枪,天下任我纵横!一个小娘子,我养不起吗?”
李三刀说完,一把抓起枪,大步走到掌柜那边,拉栓上膛,打开保险,抬手冲天就是一枪,“砰!”
“掌柜的,把钱拿出来!”
那掌柜的听到枪声,莫名其妙,忽然听到这句话,吓的一激灵,“李爷,这好端端的……”
“别废话!老子现在要你的钱!”
“李爷,李爷,这朗朗乾坤,总统脚下,您做这个,做这个干什么呀!咱还跟往常一样,记账,记账,不,不,免账,免账……”
“爷缺这些钱吗?也告诉你,甭拿总统吓唬我!总统也是我们广州人!没我们这些广州老乡,他做的稳总统的位子?别再这儿废话,把钱拿出来!”
“李三刀是吧?我们金陵龙蟠虎踞,只怕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广州兵在这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谁?给老子出来!”
旁边一张桌子上,霍然站起一个清俊的小伙儿,冷目看着李三刀,“你以为如今这南京城,就没有王法了吗?”
“王法?王法是我们广州人定的!”李三刀大声笑道:“管天管地,管你们这些小鱼小虾,管的了我们这些革命元老吗?”
“他们管不了,我管得了!”那清俊小伙儿说完,迈步便向李三刀冲来,谁知没等他走几步,方才起哄的那张桌子上,有人便伸腿一绊,那小伙儿不防之下,顿时被绊了一个嘴啃泥。
李三刀哈哈大笑,大踏步走到那小伙儿身旁,一脚踩住,哈哈笑道:“如今这南京城,是我们广州人的!”
“也许过几天,这天下,就姓袁了,我抢姓袁的东西,关你什么事了?”
说着,李三刀一横枪,对准小伙儿的头,便要搂动扳机。
正在这时,一旁角落里的忽然传出低低一声:
“杀!”
此声未落,角落里忽然风声激荡,一物飞出打在李三刀手上,李三刀一痛,枪“当”的一声落在地上,随着手枪落地,角落桌上站起一条大汉,大步流星,几步间走到李三刀身前,一言不发,出手如电,一把捏住李三刀的喉咙,只听微微咔嚓一声,李三刀便软软倒在地上,双眼翻白,抽搐几下,死去了!
这二楼上的,满满当当,却多数是广州来的北伐兵丁,他们到了这里,便成了革命功臣,不少军官脱下制服,换上了绫罗绸缎。不等天凉,又换上了皮袍。朱崇祯一行在路上所遇的巡逻兵,就是极平常的一例了。
李三刀在楼上的这一番表演,终于惹动朱崇祯。朱崇祯本想等到见过孙文之后,再来理会。可最后还是忍无可忍。
德毅刚杀人之后,已惹动二楼所有的广州兵丁。几声呼喝之后,无数碗碎碟裂,桌倒椅翻,众兵丁便向德毅刚围了过去。
德毅刚微微一笑,便展身手,开杀戒,与兵丁们战作一团。一旁方信孺和王文庆此时也已经站起,方信孺顺手捡起一张椅子,找准前面一名广州兵丁,用力便砸了过去。椅碎之后,方信孺便捡起一条椅腿,加入战团。
王文庆却闪到窗边,从袖中取出烟花火箭,一拧机关,呼啸声中,一朵流星便在空中炸开。随着这一朵流星炸开,南京城中忽然静了一静。这一静之后,就是全城震动,无数长啸相应,马蹄声烈金陵,不一会儿,酒楼前就聚起数百人马。马蹄声不绝,渐次还有人来。但王文庆已经面窗而立,手持铁底玉面飞马令,大声喝道:
“振武堂精士与台州光复军听令!”
“传汉王令,各军即日巡查东南诸省,”
“沐猴而冠者,杀!”
“不遵军纪者,杀!”
“军中欠账者,杀!”
“扰乱地方者,杀!”
“屠戮良民者,杀!”
“劫掠民财者,杀!”
“奸宿民女者,杀!”
“遵汉王七杀令!”
楼下千百精兵大声应道。拨马回转,各自领兵去了。马蹄滚滚,不一会儿便响遍金陵城中,过不多时,这滚滚马蹄,便会踏遍东南,重整乾坤,再造秩序!
却有一骑逆流而来,奔到酒楼之前,翻身下马,不及上楼,便冲着王文庆大声报道:
“上海急电,光复军总司令陶成章昨夜遇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