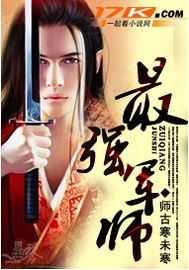世凯与紫皇密议,不知云何。数日后,世凯送诸孙辈于夏威夷一叶书院。其后若有孙,辄令送往。时人皆以为此乃世凯以血脉为质而得天下之权。后乃知,此实为托孤也。
《民国史?袁世凯本纪》
冬已经深的透了,泼出去的水,不过一个转身间,就能结成一层光溜溜的冰。街上本就不多的行人,因这气候,愈发的少了。前几日满清的皇室王公们一阵折腾,终于也在昨日车马成行,从水路往天津去了,据说要在那里乘船出海,去美利坚避难。他们这一走,让迭经欺辱的北京城,真真的有了些末日的荒凉。
荒凉中也有几处高楼在起。那荒废的清华园,前日挂上了清华书院的牌子,实实的放了好一阵的烟火,让这北京城似乎也有了些生气,那寒冬的枯木中,仿佛也生出了一些新芽来。
晨曦过后,恭王府前,洪清诸人,错杂而立。
“国史馆果真要设在这恭王府吗?”端方听到要他任国史馆长一职后,一直有些恍惚,到现在还有些在云里漂浮的感觉。今日一早来到恭王府前,忽听要将恭王府改做国史馆。他更有些晕眩,“有些不合制吧?”
“有什么不合制的?”载泓淡淡说道,她看着这座富丽堂皇的府第,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是与这座府第相伴,如今留给国史馆,也算是一种托付,毕竟以后国事纷乱,恐怕只有国史馆,才能庇佑它不遭毁弃,“大清都亡了,还有什么制?这座府第,是我们清门百十年来的中枢所在,如今改作国史馆,有午桥你坐镇,也能好好传承下去,不至于做了青草碧瓦堆。”
“门主说的极是,”朱崇祯在一旁也插言道:“我看肃王的府第,不如就做了清史馆。”
“如此说来,那紫禁城前宫,不如也改作汉留的藏书楼吧?”载泓转过头,似笑非笑。
朱崇祯闻言,洒然一笑,“若是门主愿意,倒是非常之好。有我洪清两门相镇,即便再有些不通礼法的,想必也不敢轻易生事。”
“你对世凯说,汉留也要留人在国史馆,究竟是谁要留下?”载泓不再玩笑,正颜问道。
“我留下!”方孝孺闪身上前,朗声答道。
“哦?”载泓不意竟是方孝孺,她本以为是前些日子随船而来的那些汉留人手中的一人,没想到,却是方孝孺,“你是武胜关前纵马冲阵斩将的白马少年吧?”
“不错!正是我方孝孺!”
“你可知这国史馆,不同以往。若是真进身其中,须与政治断绝,不言不语,只能与故纸书堆相伴,不聋不盲,要秉笔直书,却是会有生死之险,你年少名成,扪心自问,可受得了这种寂寞?”
“门主将我觑的忒也小了,”方孝孺大笑道,“我名为方孝孺,方孝孺何人?五百年前,建文帝师,孤直忠臣,我既得其名号,岂会在乎这些虚名蜗利?实不瞒门主,这次我来故国,便未打算回去,汉留之业,我才是继往开来之人!”
“好!”载泓击掌相赞,“有你此言,国史馆便后继有人!”
一旁的方信孺却不知道此事,听到方孝孺之言,愣了一会儿,好久才失声问道:“二哥,你要留在这里?”
“三弟,我平生所愿,你也深知,留在这里研习国学,是我求之不得之事!”
“但……”方信孺张张口,却尝到眼中之泪,心中感伤,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朱林在一旁呆呆站着,忽然抽出自己的短匕,紧跑几步,翻过门槛,站在门廊内,双手握匕,猛一使劲,将匕首刺入廊中,
“二哥,你放心,若是这里有人敢在国史馆生事,让他先问问么弟我手中的这把匕首!”
众人见到朱林小小年纪,无名无力,却做出这等事来,讶异之时,又觉几分好笑,没等笑出声来,方信孺已经大步上前,行走之中,沧哴一声,抽出自己佩剑,却一把插在门廊地上,
“若是有人敢在国史馆生事,须问过我方信孺之剑!”
宫本义英与宫本义雄对视一眼,也大步上前,抽出腰中太刀,一把插在地上。洪门众人之后,清门众人也不稍让,德毅刚等人也纷纷上前,将自己兵刃插在门廊之中,一时间,门廊中林林杂杂,两侧插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刃,刀枪剑戟,弓斧短匕,肃然之极。
载泓与朱崇祯相互看看,微微一笑,两人飞身到一侧马车旁。掀开遮步,现出里面的物什来,众人看去,才发现是两块大大的石碑。
朱崇祯与载泓一人一边,运力抬起。这两人是何等样人,做这等事,自然是小菜一碟,不一会儿,便将两块石碑,竖在恭王府门前。
石碑高约丈余,阔约三尺。两人选的地理深合术数,两块石碑与王府若合一契,更增许多威严。
朱崇祯拍拍手,对载泓笑道:“门主先请!”
载泓摇摇头,“一起吧!”
“好!”
两人说完,纵身而起,挥出手中长刃,在石碑上挥刃落笔,只听石粉簌簌而落,洪清中人纷纷闪到碑前,要看二人究竟要写些什么。
顷刻间,两人落定,一阵北风吹过,拂去碑上残留的石粉,现出字迹真身,众人放眼看去,只见右面载泓所写为“千古风流”,左面朱崇祯所写为“江山留与”。
“千古风流!江山留与!”
“有这八个字在,若有人生事,也要拍着胸口问问自己,当不当得起我洪清之怒!”朱崇祯笑道。
这时,忽然袁克定骑马奔了过来,奔到恭王府前,大声喊道:“孙文回电!”
袁世凯大步走过去,从袁克定手中接过电文,自己却不看,双手恭恭敬敬捧着,送到载泓面前。
谁知载泓却摇摇手,“政事已然委托于你,这电报,你看就好。”
朱崇祯在一旁也点头笑道:“不错,不错,如今你才是中华之主。”
袁世凯见两人都这般说,只能拱手告罪,打开电文来看,却一边看,一边高声念了出来:
“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听到这电文,在场的洪清众人,都扑哧一下乐了出来,连袁世凯念完,也禁大笑起来。
孙文在这电文上说的清楚,他虽做了这总统之位,却不过是“暂时承乏”,临时过渡,将来若是袁世凯果然逼清帝退位,他自然虚位以待,将总统之位让与你袁世凯。
一旁的朱林年少,不明白众人在笑什么,便问向旁边的方孝孺,方孝孺哈哈一笑,却反问朱林道:“阿林,你应该开始读史记了吧?项羽本纪中,刘邦入了咸阳,是怎么应付楚霸王的询问的?”
朱林侧着头,仔细想了一下,朗声背道:“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
众人听得朱林这童稚之言,忽然止住笑声。德毅刚已然说道:“那孙文一介乡野村夫,不通政务,不事生产,果然有如此野心,定要学那刘邦,做这中华之主吗?”
载泓不言,却把眼看向朱崇祯,眼中那意思,便是在问:“当日紫禁所言,如今果然应验,项羽已出,刘邦归位,这一场楚汉之争 ,看来,正是要开幕了!你究竟要如何做?”
朱崇祯脸色凝重,忽然向袁世凯问道:“那孙文做的,究竟是总统之职,还是临时总统?”
“并无临时二字,实为总统!”
“一心邀名的东西!”朱崇祯眉头一皱,已经有些不悦,“此刻南国无钱无粮,政府都是临时,哪里来的实名总统?文不成武不就,又在中华无甚根基,如何做的住?见局不明,恣意妄为,真是好胆!”
见到朱崇祯这般怒气,载泓倒是轻笑起来,“素闻这孙文在海外筹钱是把好手,说不准这次他归来,带着重金也说不定呀!”
“重金?”方信孺笑了,“以前他靠其兄在夏威夷的资产,数年前,我们到夏威夷时,他就已经将德伯的钱败的光了。美利坚致公堂处的资金,已被我们用来做汉留的费用,他能去何处寻来重金?说句实话,若是我们洪门不出人不出钱,他孙文便是一文不名!”
“怕就怕在这上,”朱崇祯怒气过后,已然冷静下来,他默默想了一会儿,便知道辛亥之事,随着孙文建府,又平生了许多波折,“这孙文当年便能接日本的资财,如今身为总统,若是逼得急了,恐怕更会与日本订立私约,以换取日本人相助!”
“你们革命党人,不是因为我大清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才要将我们驱逐吗?怎么此刻当了家,也要做自己反对的事吗?”德毅刚有些惊疑不解。
“不当家哪里知道柴米贵?”载泓叹道,“如此说来,我们等不到国史馆成礼那天了?”
“不错,只怕我们即刻便须出发,”朱崇祯也叹道:“若是等孙文当真签了私约,就麻烦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