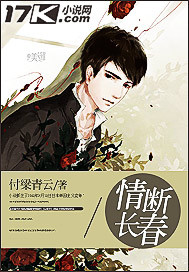邓子咴收回枪,摇摇头,对着一旁的朱林苦笑一下,
“没得让阿林笑话了。原本这江南多水匪,山贼倒少。可能是前些日子西边又闹了水灾,这乡民们就越发的没规矩了。”
朱林盯着那几个山贼连滚带爬远去的身影,有点想笑,心里却忽然像梗着些什么。人不能迷,若是脑中总想着一件事,总会想着通了他。这朱林也便如此。早上那一通胡思乱想,到现在仍在脑海里盘旋,许久未见的中华故国,许久未见的中华故民,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来迎接自己?自己成人后第一次回到故国,又期待着遇上什么样的故国和故民呢?
只摇摇头,朱林便催马前行。这一路虽多江湖印迹,说起来除了那几个山贼,竟是出奇的野旷无人,不单是田野,便是先后路过的几个村落,竟也空无人烟。只是处处都有些大水冲过的痕迹,田地里更是成了污泥池,杂乱点缀着些破衣和木条。显然果如邓子咴所说,一场大水刚刚来过。不过大水既然已经去了,这乡民都去了哪里?
又行了多半个时辰,看看界牌,已到了昆山县的境内。一行人歇脚喘了口气,又起身而行,行不多时,转过一片树林,翻过一座山丘,眼前豁然开朗,山脚下一个小镇炊烟袅袅,依稀还有人声传来。
一行人都长长的舒了口气,行了这多半天,总算有一个歇脚的地方。这江南的雨虽不恼人,可总泡在雨里,也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邓子咴行在前头带着驾车的几个伙计,打马便进了小镇。 朱林走在最后,东瞧瞧西看看,忽然见一旁有座石碑高高耸起,石碑上面还盖着一座帽檐。朱林纵马过去,见石碑右面写着“昆山县奉敕禁革漕弊条规”,碑上有些字迹已不可辨。朱林略略读过去,却是康熙十七年所立的碑,禁止浮收的条文。说来这样的碑文一路走来见过不少,或是立在会馆,或是立在城隍庙,像这样孤零零立于镇子门前的,倒是头一回看到。
这碑文有些意思,上面林林总总的说了十余项禁止,朱林又回头数了一遍,见这短短数千字碑文提到浮收花样精打数十种。举凡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一而足,也不知道这碑立在这里,究竟是明文示众禁止,还是做个备忘录,告诉那些税吏这些花样。
朱林正自看的入神,冷不丁远处吵闹的厉害,跟着风声呼啸,一块砖头凌空就向朱林头上砸来。
一侧头,一伸手,朱林便将那块砖头抄在手中,也不看,仍回头去看那碑文。依朱林的料想,不多时自然会有人来致歉,不成想等他看完了碑文,那边只是吵闹的厉害,却根本没有人理会这块砖头。
“这故国的人好生无礼!”朱林暗自苦笑,摇摇头,便向吵闹处走去。
那边已经围了不少人,里三层外三匝,只听的里面一阵吴侬软语的叫骂,依稀是什么交租之事。可看不清楚,究竟无趣。朱林四处看看,正见远处一颗大树枝叶繁茂,其中一枝横斜,正正压在圈子中心。朱林扔掉砖头,绕到树前,脚尖一点地,身形窜起,伸手一搭树枝,借力一个翻身,落进树中,三两下便攀到树枝上。朱林选个舒服的姿势坐下,这才看向人群的中心。
那里面其实不过四五个人,其中两个瘦瘦干干的男子穿着满清衙役的服饰,一个嘴上留着八字须,一个光着头,脸上却有一块刀疤——看模样应该是来收税的;剩下几个应该是一家人的样子,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壮健汉子,手持尖刀,神情凄厉,身旁一个女人正在哭泣。
那汉子横眉怒目,手中尖刀摇摇晃晃,大声的抗辩着:“赵老四,胡麻水,你们不能这么没有良心,上月我刚交过了粮,今天你们为什么又来收?你们这些吃皇粮的,真是填不饱的黑心狼,就是洪水都比你好,洪水说来时还有个信,你们这些吃皇粮的,说话就是放屁!上月交粮的时候你们怎么说的,都忘了吗?”
赵老四便是那个嘴上留着八字须的家伙,他见到那把明晃晃的杀猪刀就在身前来来去去,却看也不看,只抬眼向高空,右手在耳里抠来抠去,好半天抠出一块耳屎,拿在眼前瞧了瞧,随手一弹——竟是全然没有理会!听完汉子的话,赵老四斜眼看看,眼光却更多在那个哭泣的女人身上流连。赵老四冷冷哼了几声:
“马三儿,别给脸不要脸!这是新来的张县令亲自交办的,你有几个脑袋,敢违朝廷的命令?”
“呸!”马三儿手里摇晃着杀猪刀,一口浓痰砸在地上,“赵老四,要脸不要!上月你还说是苏县令,怎么这月又是张县令?你当我马三儿是好哄的吗?”
“马三儿!我赵老四敬你死去的父亲在这常熟地面上算个人物,可别当我赵老四怕你!你今天若是不交粮,我便是往张县令那边一报,张县令若是恼了,你这一家就别想活了!”
赵老四声色俱厉的说完,脸色忽然一拉,变作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
“马三儿兄弟,不是四哥说你。这朝廷的事,跟你说了,你也明白不了。哥哥我在昆山县衙当值也有些年头了,今儿跟马三儿兄弟掏心窝说句话,自从这大清变了天,你晓得常熟县令换了多少个?我都数不清,宣统三年一天就换了仨儿!如今袁大头是死了,可咱常熟县四周边还在打仗,这年月,换个个把县令算个球!”
这一番话软硬皆施,一番揉搓,马三儿高昂的头渐渐就低了下去。这四年的民国,地方的稳定说来竟是远远不如满清。四年的民国,一省之地动不动便是闹独立,两省之间动不动就是开战。若是省独立,下面地方也多半各有归属,或独立或自固或讨逆;这时不单两省之间开战,两县之间也常常开战,有时便是战事消解了,县际的战事也从未结束。四年的民国,对于许多地方,便是打了四年的糊涂仗。至于这城头的大王旗,便是一日换上几次,乡民们都不觉得出奇。只是一点,这每次换了大王旗,总是要新收一番税粮。不但要收现在的,也要收过去的,如今又要收子孙的。
“你莫哄我!”马三儿忽然像是算清了账,手中紧了紧杀猪刀,张口便是大叫:“凭什么换个县令我就要交一次粮?还有没有王法了?我马三儿交粮是给朝廷,换个县令也是朝廷的县令,难不成皇帝不在了,就这么欺负人吗?”
“嘿!”一旁胡麻水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张口便骂道:“马三儿!四哥敬你是条汉子,才跟你推心置腹说这些话,给你脸就兜着,再多嘴,说不得,我们回去禀了张县令,让你尝尝大狱的滋味!”
转头瞧了瞧周围看热闹的人,胡麻水唾沫横飞:“看什么看?我告诉你们,都回家准备粮食去,张县令说了,这回的粮税,他也不多收,刚发了洪水,张县令也知道乡亲们生活不容易。张县令特发了善心,这次的粮,只收到民国二十年的。”
“哈哈,”朱林在上面听的,再忍不住,扑哧就乐了出来。
听到笑声,胡麻水左右看看,却没看见发笑的人,“都回去准备去,若是谁家少了一粒米,别怪我胡麻水不念情面!”
谁知胡麻水说完,围着的众人仍是不动地,只是看着场中。胡麻水不过刚做衙役,自然不知道这里面的行道。这马三儿虽然不过二十多岁,但马家在这鲁家浜极有声望,几次流兵乱匪来抢劫村子,都是这马三儿的父亲领着众人将流兵乱匪打了出去。这赵老四当了衙役也快十年了,自然晓得这里面的规矩,若是压不服马三儿,让这个刺头顶在这儿闹下去,这鲁家浜的粮,就甭想着能收了去。
“马三儿!你可想好!”赵老四忽然又翻了一下脸,厉声把唾沫喷向马三儿:“新来的张县令可是同盟会出身,最恨的就是满清的走狗,你要是非要往这刀口上撞,回头问你个满门抄斩都是轻的!”
“老子不是革命党!”马三儿张嘴骂道:“你才是革命党,你们全家都是革命党!我马三儿今天就讨口气,凭什么换个县令就要交次粮!还要多交十几年的?禁弊碑我们鲁家浜也有,就在那儿供着,”
“好啊!马三儿,你可真是执迷不悟!”赵老四嘿嘿笑了几声:“那碑文是什么?是满清朝的狗皇帝康熙立的,如今是什么年月?是民国了,你居然口口声声念着满清,说不得,哥哥只好向张县令禀告,这里有个叫马三儿的,守着满清的法,抗拒民国教化!”
赵老四说完转身便走,一旁哭泣的那个女子被赵老四的话哄的一呆,见赵老四要走,急扑过来,一下跪在赵老四身前,大声就哭道:“我家男人不懂事,赵四哥,您可千万不能这样回告县令啊!”
看着眼前哭的梨花带雨的少妇,赵老四的心扑腾扑腾跳了几下,咽了几口唾沫,赵老四正要开口,冷不丁那边马三儿飞来一脚,一脚踹在那女人肩上,那女人一个不妨,一下就被踹趴在地。
“赵老四!你要民国二十年的粮,我跟你说,我马三儿活不到民国二十年!这粮,我交不了!”
说着,马三儿挥着杀猪刀猛地就向自己胸腹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