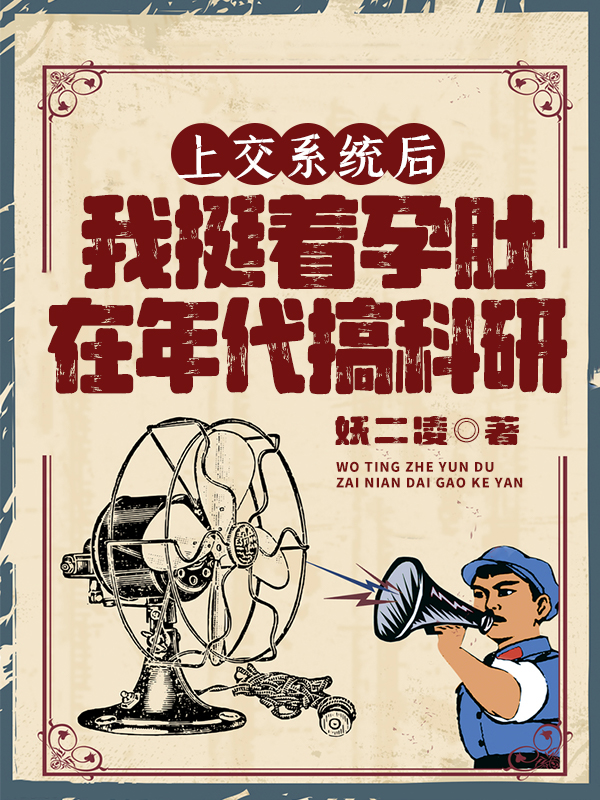包房内烟雾缭绕,音乐的声音充斥着耳膜,伴随着轻微的呻、吟声,长桌对面的一对男女已经是被氛围烘托到了一定程度,几个呼吸间就变换了姿势。
弹掉指尖的烟蒂,赵权之端起酒杯小抿了一口,站起身的时候眼角扫到旁边玩闹的金衡,轻哂了下,赵权之伸手将搭落在一边的衣服搭在小臂上走出了门。
转身关上门时,耳根顿时清净。楼道里回旋着《克罗地亚狂想曲》,鼻尖是有种似有若无的青涩的味道,像是西柚柠檬一样,闻着很是醒神。
包厢位置在楼层最里面,是club最后剩下的一间包厢。
由此可见,组局的人排面也不怎么样。
抽完手里的烟,赵权之刚想离开,身后的门就打开了,金衡一脸严肃的走出来后看见赵权之殷勤的笑了笑。
“一起啊哥。”
赵权之瞟他了一眼没说什么,转身走向另一边电梯。
临近深夜,这个点回去的人不是很多,是以电梯很快就上来了,赵权之率先迈进电梯,在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楼道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还有一点便要阖上的电梯门又打开来。
一双精致的黑色高跟鞋出现在楼道与电梯的交界处。女人身材纤细高挑,戴着一副遮住半张脸的墨镜,只露出了轻抿着的红唇。
一种压迫感油然而生,赵权之不禁站直身体,视线随着女人的动作,看到了一张熟悉的侧脸。
比几年前稍显精致,但多了几分冷冽成熟。
女人摘下墨镜,接通电话,用流利的英文交代着对方明天去公司之类的话,熟悉的声线就这样,在寂静的空间之中,一点一点的进入到赵权之耳膜,继而向下流走??????
几年不见,他压抑在心底的那份情感就这样突如其来的被唤醒,想知道她生活的好不好,想知道她有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想知道她几年间是否喜欢上别的人,想知道她??????还需不需要他。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他此刻昏昏沉沉的头脑里,想的都是她。
不时地有车子从对面驶来,昏黄的车灯照亮她整个人,她就这样在路边走着,走着。
这让他想起几年前她亲人离世的时候。
内天是周一,排了整天的课,从早上起来的问安到第一节公共课下课,他都没收到她的任何消息,等到问她的室友才知道她一早请了假。
本来有些生气的情绪顿时被慌张取代,在打了几个电话都不接的情形下他偷偷来到女生宿舍,趁着宿管阿姨没注意的情况上了楼。
他看到本来一脸沉静的人在见到他之后一秒就红了眼眶,沙哑着声音跟他说:她走了。
去到办公室找导员拿假条时,她戴着口罩,红着眼睛,只是呆呆的坐在一边,他去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像是一具没有意识的躯壳。
两人没有交谈的坐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高铁,她就只是望着一个方向出神,不哭不闹,安静的像是个娃娃。
走到殡仪馆时,她才有些紧张的攥紧了他的衣摆,也是内天,他向她的家人们介绍自己为她的男朋友,在内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身上好像多了一份责任,沉甸甸的却又很满足。
他看着她慢慢的走进房间,然后默默的趴在床上那盖着白布的人身上,呜咽着,像是小兽的嗡鸣。
工作人员走进去时,她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小小的一张脸除了眼睛鼻子红肿外,冷淡的不像有感情一样。
回学校不久,他们就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很离谱,离谱到他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就是这样,从那以后,他们像是陌生人,不会在食堂碰到,不会一起上公共课,就连学生会她都离开了。
在他不受控制的日渐颓废的那段日子,她争取了很好的实习机会,拿到了出国深造的offer。
在所有人跟他说她是在利用他、她是渣女、她不值得的时候,他收到了陌生的短信:对不起。
看到了那三个字,他突然很想笑,就好像之前他所有的幻想所有的希冀都灰飞烟灭了,在那一刻,他确实觉得自己没必要这样。
整晚宿醉后果严重,但是他却从没有这般清醒,他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他知道,如果他现在放弃了,那以后也就没机会了。
看着她走进公寓,拉亮灯,赵权之笑笑,抖落烟灰,这趟差真没白出啊。
回到酒店已经凌晨一点多了,看着桌上还未修改完的企划案,赵权之下定决定,将厚厚的一沓扔进碎纸机里,然后订了回国的机票。
或许,他也能将“被利用”转换成自己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