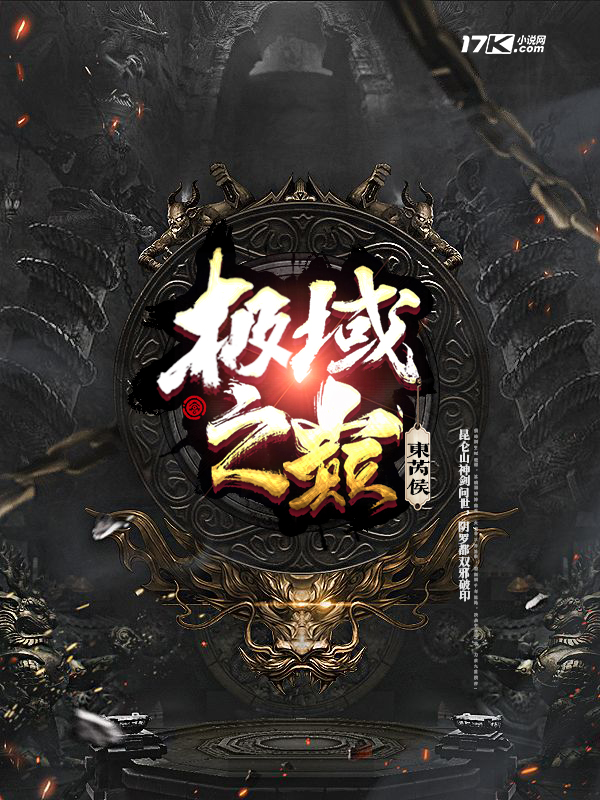天明再次醒过来时已是烈日当空。强烈地太阳光刺得他的双眼睁不开,嘴唇也因为这么长时间的阳光暴晒变得龟裂。他感到口渴不已,同时腹中的饿鬼也袭过来。光是这两样已经够人受的了,但是从腿上传来的疼痛胜过了干渴和饥饿,钻心的疼痛让他一下子将干渴和饥饿全部抛到脑后。他看到自己的左小腿此时已经肿得象馒头一样了,更为可怕的是整只左腿已经成为青紫色,估计是在接骨时伤到了经脉,或许跟本就是被马踩成这样的...
无意中摸到了胸口那个鼓鼓地银两包,拿出来仔细一瞧,只见银两的包包上绣着南宫两个字。天明双手死死地捏着包包,暗暗地想:有钱就了不起啊,踩断了我的腿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在脑海中慢慢回忆那几个人的样貌。现下回想起来那几个人的样子似乎并没这般凶神恶煞,隐隐觉得在那群人里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那身装扮应该是个女人才对…
忽然又是一阵钻心的剧痛从断腿处传至大脑,他痛苦的**了一下,脑子闪现一股恨意:总有一天我会叫你们也尝尝这种痛苦的滋味。
这种钻心的痛一阵接一阵的来,那感觉就像别人用尖刀在他的心脏上一刀一刀的刺,却又不一下子将心脏刺破,刺破了倒好,他也可以一了百了了,可偏偏就是这种缓慢地痛苦法。就象亲眼看着别人用刀在自己身上一刀一刀的将肉一块块从身体上削走,最终自己看着自己慢慢死亡。
天明恨恨地用双手在地面上敲打了几下,这种发泄会让他暂时忘掉疼痛,同时更能让他记住这所发生的一切事务。他要将这种痛苦尝还与所施之人。心中存在了仇恨,同时勇气也会由此而至。
在痛苦之中他想到了父亲教的心法,虽说天天练习,只是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心法叫什么名字,小的时候父亲每天都逼着自己练这种心法。现在终于得到好处了,每次自己被人欺负后,他就用那种心法来疗伤,每次运行过那种心法后,自己总是能很快的恢复过来。
这里离村子较远,平时三五个月也少有人来。他也是一次在找水喝时无意发现这处奇地的。他环顾四周,周边全是丈许长的茅草,而此刻自己的身体刚好躺在茅草中央,就算是有人来了也不会知道这草从里有个人在练功。不正好是一个修练的天然屏障吗。
天明想坐起来运功,可是此刻身体的状况由不得他来做主。任他怎么样努力,就是坐不起来。本来腿断了就不是小伤,后面又硬是托着断腿爬了几里路才到了这个有草药的地方,虽说是草药敷上了,但却令他的身体遍体鳞伤,真是伤上加上。加上缺水和肚中的饥肠漉漉,却是哪里还有力气坐得起来哟。
一番挣扎后,天明放弃了坐起身,因为他根本就坐不起来。同时在他心中浮现另一个想法:平时练这种心法都是要坐着练,为什么不可以躺着练下看看呢,反正自己现在也无力起身了。想到这里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当下微闭双眼,大脑尽量不去想腿上的伤痛,心中黔黔念起了那段法诀。
过得片刻,天明觉得丹田内那股清凉地感觉就像线条一样朝四肢散射过去,只要是线条所经过的地方都会无比地舒畅。那些凉丝丝的冰线在他身体内到处穿梭着,只是运行到左腿的那些线条却总是不能如愿以偿。那些线条每次走到断裂处,就被一种无形的阻力弹射回来。冰线游走一圈后又不停地向断骨处冲击过去,每冲击一次,那里的阻力就好像减少一点,冰线为了那一点点进步,就这样来来回回重复着这个过程。
却不知,这个简单的过程正让天明的断腿慢慢好转起来。只是这个过程在外表看来没有什么变化,他尚不知道,那些凉丝丝的冰线正将断腿处那些断裂地经脉进行修复、改造。断裂的腿骨也在冰线的冲击下缓缓逾合。冰线每冲破一分其实也就是对断腿修复了一分,只是这个一分却要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天明尚自不知,自己所用的这套心法却是所有修真者都梦寐以求的“开天法诀”。这套法诀也是他父亲留给他唯一的东西,在天明还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整天逼着他练这套法诀,当时他也不知道天天练这个有什么用处。但在威逼之下,还得服从命令。有一次为了偷懒,自己悄悄地跑到树林里玩起来,结果被父亲发现了,硬逼着自己实实地练了一个晚上,也自打那次之后,他再也不敢偷懒了,每天都按着父亲的要求练。再后来父亲走了,至今再也没有出现。但是这套法诀已在天明的脑海中深深烙下印记。
有一次他在街上找吃的,被一群流氓戏弄,最后还将自己一顿狠揍,搞得他当时是遍体鳞伤,天明逃到一个无人地方想起父亲教他的这套心法,一练之后,身上所有的伤痕竞然在几个时辰之内全部逾合,那些伤似乎跟本不曾出现在自己身上一样。小乞丐知道那套心法对疗伤有莫大的好处。直到那时他也确信父亲逼他练还真是正确的。
天明尚却不知,这套功法在今后却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这些尚且是后话。
现在天明仍然用同样的心法来修练,只是这次他的练功姿势却不同于往常任何时候。殊不知,其实这么躺着练,虽然运功的时间要得长久一些,但是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天明此时完全进入了忘我的境界,身外的一切事物都被他置之度外,他的身心和思维完全沉浸在身体内那些凉冰冰的到处游走的丝线上,他就陪着那些冰丝线在体内到处游玩…
在这一刻起,时间感和空间感对于他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