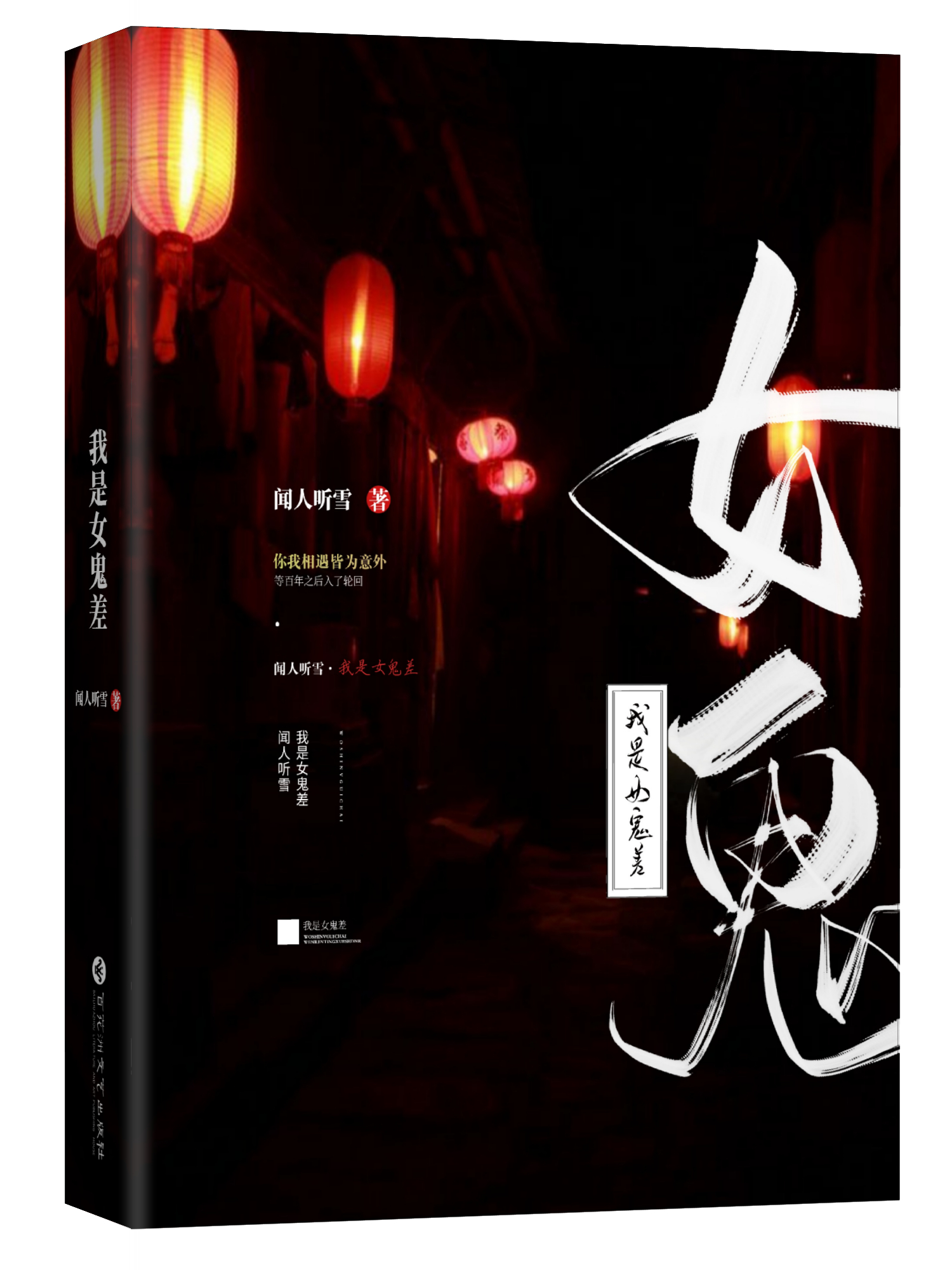孟昔年见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才缓缓放下书包,默默问了句:“令郎这是?”
许洲一听,兴趣来了:“莫见怪,孽子粗鄙。”
孟昔年因为昨天的事还有不想面对他,就故意不看他,又没好气地说:“好了,演够了吗?”
许洲看她也觉得奇怪:“嗯,你怎么了?”
听后,又掩饰性地找东西,装作一副不甚在意样子说:“我没事啊。”
“你不会还在因为昨天的事生气吧?”
“没有啊,我没那么小气。”又转过头,不想和他对视
“今天怎么这么别扭呢?”下意识就想揉揉她的头发,还没伸出手,就被付佳尖锐的声音打断了。
“你俩搁着演啥呢?一个月了也没见你俩多好似的,今天都嗑药了?”又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审视着俩人。
许洲伸在半空中的手,不知道该不该放下。发现自己被盯着看,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反向摸了摸自己头。
孟昔年也感受到了此时的气息,本来只想装模作样地混过这一天的,现在只想给付佳磕个头。
“转过去吧你,下午考试不担心了。”还使眼神地眨了眨眼。
不明白所以的附佳,发出了心底的疑惑:“你眼睛怎么了?一直眨。”
“啊?没…没啊。”又把手伸到课桌下捏了捏付佳的手。
这次付佳脑袋没走丢,立马变回原样:“哦哦哦!去厕所吗?”
然后就把人拉走了,孟昔年忍住想把她掐死的冲动。
七班就在厕所旁,教室里宋彻坐在后门旁边,整个人都还在睡着。旁边的人打打闹闹的,俩男生正在“讨论”真理,宋彻被吵的睡不着。
出奇的是今天他没生气,靠着墙,眼神微眯。皮肤白嫩,眼睛透亮,没有了许洲身上的书生气,却显出了一股子痞气。
不说话时,能给人看出禁欲男的气质。
付佳拉着孟昔年在七班门口停下了,一幅了然的样子,微微抬起头:“说吧,什么情况?”
“我和他能有什么情况…”还没说完就被付佳手扣嘴。
“闭嘴,我要听真话。说!”
孟昔年向后退了一步,紧贴着墙壁。秋天里,阳光都是刚刚好。走廊对面的水杉树沙沙落叶,只剩下树影倒落在身上。
“就是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学那会有点讨厌他,但现在不同了。”
付佳也表现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你喜欢上他了?”
孟昔年闭眼喃喃了句“喜欢?”
又抬起头,用一种付佳分辨不出悲喜的眼神看着对面的水杉树:“付佳,我不会喜欢上任何人的。”
少女的初恋美好,纯真。
付佳不再说话了,她和孟昔年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她能感受到有什么东西牵制着她。
她从来不会提及家人,对男生有莫名的厌恶感。
之前有一个高二校队的同学来班上找她,打着认识同学的名号叫人出去,她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就头也不回的转头离开了,让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这和她大大咧咧的性格不同,附佳本以为孟昔年是任谁都能打好关系的。后来发现她不是,她对于超过友情的感情丝毫不感兴趣,包括亲情。
一墙之隔,宋彻整个人听得是怔一阵愣一阵,
暗暗嘀咕:啥玩意?不喜欢任何人?这不是啃到硬骨头了,这是啃到石头了。
许洲看着书,读到了一个词“Forelsket”,看了解释后,又笑了笑。
费也今天却出奇地巡课来了,刚走进教室,吵闹声就停了。
一个叫郑硕的男生,属于每个班都有的那种勇士,叫嚣着:“干嘛的,一个个。嗨起来呀,下午就考试了,考完野哥的脸指不定是绿的还是红的。”
“绿的。”
“我也怎么觉得,只不过哥们…”
“说呀,继续呀,后面站着去。”费也笑着说,底下同学一个个的都看得发毛。
平时费也其实是个好说话的,性格直率、坦然。有时候大家请假,闯祸,都是能遮掩过去就遮掩过去,可今天的确撞枪口上了。
立了立身体,扫了一下人,眉头猛的皱起,正要发火,
“报告”
俩个女生仿佛察觉到气氛不对,明明是英语早读的,徐老头平时不管的。
抬头定睛一看,费也整个人脸都黑了,但秉持着不责骂女生的原则,没好气地说了句:“还不回去坐着?”
俩人默默埋下头,不同于平常的气氛就可以告诉她们今天不能撞枪口。
一坐到座位上,费也也发话了:“下午考试好好考,以后再被我发现这种情况就和我去办公室喝茶吧!郑硕,回座位,放完假来三千字检讨。”
“啊?”这可给郑硕整不会了,本以为站完早自习就过去了,谁知道还有这么一出。
付佳一如既往地不怕死,费也出教室还没3秒,立马转头问许洲:“啥情况啊?他今天吃火药了。”
郑硕就着破罐子破摔,自嘲着向人叙述了一遍,又感叹了一句:“估计他今天嗑药了,算了,要怪就怪我不是个女生。”
“这关女生男生什么事?”孟昔年此刻兴趣来了,完全没了刚才那副焉了吧唧的样子。
“他有个原则不罚女生”,许洲淡淡出声。
“你怎么知道?”女孩觉得不理解,为什么呢?男女有什么不一样。
“我舅舅原来是他的学生,据说是他们班有一个女生考上大学后没多久自杀了。虽然说和他没多大关系,但可能给他留下悔恨吧。他觉得是自己逼得那个女孩太紧,才会有那样的悲剧发生。”许洲不带任何情绪地说,像在诉说一个通知,不会带有个人的同情,悲伤。
但其实只有许洲自己知道,当初何洧川说这些时悲伤。一个拥有独立思考的人,一个男人每每诉说的情绪难掩。
“我没想过她会自杀,她自杀前一天晚上我遇见她了,我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不同,她只是对我说了句‘谢谢你’。我以为没什么的,都结束了,结果她走了,永远地走了。我恨我自己,我在想如果我和她多说一些,她会不会动摇?会不会有别的可能?”
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丑恶,贪婪,自私的那一面。
我们在情绪地荆棘里爬行,各种焦躁不安,所谓悲观的想法都像一根根刺,扎在我们身上,要我们用血珠去换取更为强大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