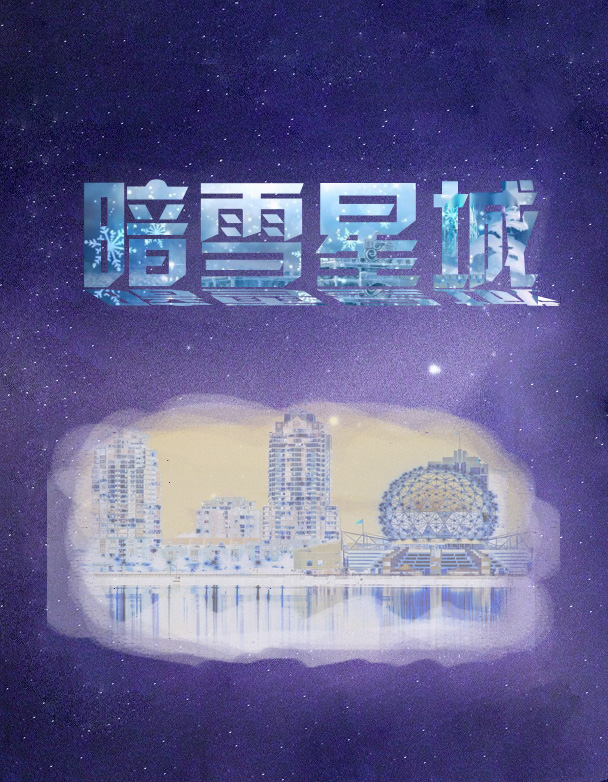十年已过,也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当年他哄过她睡觉。秦王如此纵容她,现在的她恐怕任性不减当年。
身后的杜太傅依然躬身站着。
申生说到:“这些年,太傅辛苦了。”他往暖炕上添了柴木,火苗渐旺,蓝烟渐浓。
太傅闻言立刻跪下:“臣愚昧,未能替殿下分忧。”望着他孤漠的背影,他也知道太子努力做好本分,却像是和自己的心背离,无法开怀,却又不知为谁执着。
申生深深吸了口气:“我知道太子这个位置坐起来不容易,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它,努力地想怎么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我……确实很讨厌!”
“殿下……”
“但是我会做得很好,连父王都没理由废立我。”他喃喃道:“我一定会是晋国未来的王,一定是!”
申生捏着手心那块玉,手指一遍一遍细腻地滑过上面的纹理……
☆
☆
☆
晋国,蒲城。
是夜,月色朦胧,星辰昏暗。
油灯之下,重耳手中那封竹简书信有些沉重。
远处不时传来叮叮的敲砖声。
侍臣介之推往他的兽面青铜觥杯里倒上一杯清茶,说道:“二公子,城墙加固的工程已快完毕,公子可以放心回绛城。”
他摇首道:“你不明白。”
“公子是担心大王因为当年的事,对你心存芥蒂。”亦臣亦友的介之推对重耳说话从不顾忌礼节,“还是……公子怕面对骊夫人?”
思绪如狂潮涌入,努力去模糊那张娇颜,可那双怨怼的眼睛时时闯进他的梦里。
望着桌子上那杯茶,犹记得父王立新夫人那一天,他也是举着一杯酒上前道贺。她也把酒杯举起与他碰杯,朱唇微启:“多谢二公子!”
那一天父王很高兴,脸被酒气熏得红润,骊姬把他扶进寝宫。
大殿之上所有人都醉倒,惟有他独自清醒。
也是唯一一次,他走进大牢,冒犯上之罪,把郭偃放走。他虽不相信卜神问鬼之说。但郭偃罪不致死,他也想在她新婚之夜做一件好事,为她积福。
郭偃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公子为帝星下凡,江山迟早会到公子手中。”
他终于知道父王为何要杀郭偃,他那番话,是在股动他篡位。
所以第二天,他便要求出走绛城。
蒲城虽然荒凉,但比王宫舒适。
他的臣下好友也义无反顾地追随他,介之推,先轸,赵成子,狐子犯,辅助他治理蒲城,也力劝他回晋都。
但王宫里有他不愿意面对的人,不愿意面对的事。
重耳把书简合上,说道:“我也很久没有看望父王了。还有申生,夷吾,不知道他们过得如何?”
介之推也在他身旁坐下:“公子手足情重,臣明白。”
此时,一个丰神爽雅之人抱着一堆竹简进来,大声喊着:“二公子,咱们蒲城的市集是越来越热闹了!”
重耳喜道:“有先轸大夫在,商贾都涌进来,怎么会不热闹。”
先轸把那堆竹书放下,拿起重耳那杯水仰头便喝,咕隆咽了下去,擦擦嘴便说道:“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晋商必定可以富甲天下。”
二人都很同意地点头。
“公子去哪里,我们都愿随左右,公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介之推道。
“什么?公子要去哪?”先轸急得跳起来。
“绛城!”介之推白了他一眼。
先轸喜得大拍手掌:“好……好,臣马上去准备!”说完便飞快跑了出去。
重耳拉着衣袖上的微小皱纹。
看来这里也不能久恋了。
☆
☆
☆
晋国,绛城。
骊夫人房中。
侍女都守在门外,房里弥漫一股特殊的香气,圆桌之上的博山古铜熏炉一缕缕青烟升起,房间里却是一个人也没有。
东阁的柜子放了很多摆设,每一件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
其中一只玉老虎双眼发出蓝光,当他的双眼被黑布盖住之时,机关便开启,宝柜之后,是一间暗房。
一片素白,是个灵堂。
骊姬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祈祷。
神案之上,无数的牌匾,最中间的一块,刻有骊戎国王的名号。
如此神秘的房子,没有人知道,即使奚齐也不知道。
房里的风铃响起。
门外有声音说话:“夫人呢?”
侍女答道:“回大王,夫人她……正在沐浴。”
晋王扬手便把门推开。只见骊姬坐在铜镜前,梳着一头乌亮青丝。正想起身行礼,晋王却按着她的肩膀,亲吻她的额侧。
“大王怎么有空来看望臣妾?”
晋王揽着她的细腰:“夫人是怪寡人冷落你吗?今晚寡人就在你房中留宿如何。”她则过头,恰恰碰到他脸颊,她轻吟:“谢大王。”
她偎依在他怀里,说:“大王,过几天您要到七星庙祭祀,您国事缠身,如果不便前往,臣妾愿意代劳。”
晋王欢心道:“夫人果然明白寡人心意,过几天我让里克与你同行,有他保护,寡人才放心。”
她心底波澜起伏,脸上却依然平静:“里克将军好像不太喜欢臣妾,让他同去不妥吧。”
“他敢?”晋王不悦。
她想到那炯炯双瞳,望着她和奚齐的时候总使她的心凛颤不已。当年反对晋王立她为夫人的,里克就是其中一个。
“谢大王恩典,臣妾一定向七星古槐祈祷,让它保佑大王长命百岁,大晋国运昌隆。”
透过袅袅轻烟,她的眼中有柔情似幽潭。
任谁都愿意溺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