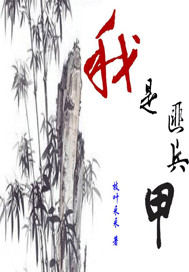云飞扬打劫淳于荷?他到底要搞什么名堂?野哥的脑子飞快旋转着,可是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
“地上死的这几个人全都是你们虎啸山庄的人吗?”野哥阴翳着脸问道。
“回大侠,他们几个全都是云飞扬的手下,刚才弄倒树木,投掷迷药弹也都是他们干的。”
“刚才用绳套把那位少侠掳走的是什么人?”
“云飞扬。”
“他现在逃往哪里了?”
“应该是去了虎啸山庄我家后宅。”
“带我去好吗?”
野哥友好地拍了拍李虎的肩头,脸上却是不容置疑的表情。
李虎十分小心地瞅着野哥的脸色,然后用半带交换半带恳求的语气说道:
“我这就带大侠去,只求大侠放过我们村的男女老少。”
“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但保你全家没事,也保证云飞扬会悉数退还你家财产。”
“多谢大侠!多谢大侠!”
李虎见野哥不但保证不伤他的家人,而且还保证帮他要回家产,他哪能不高兴呢,如果他刚才咬舌而亡的话,这好处往哪儿捡去?
迅速从丛林中牵出两匹快马,李虎和野哥一前一后便在夜幕下向前疾驰而去,只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二人便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大但环境还算优美的小村庄,跟着李虎转了两个弯之后,野哥便被李虎领着来到了一个院墙高耸的大门前,凭借不太明的夜光,野哥发现宽阔的大门上方隐隐约约悬着“李府”二字的大号牌匾,心里知道这肯定就是李虎的家了。
李虎下马,用手整理了一下衣襟,刚要上前敲门,却被野哥一把拉住道:
“咱们从别处进去!”
李虎看了一下野哥隐在星光里的神色,便马上会意道:“我家还有后门,只有我和我老婆有钥匙,要不,咱们走后门进去?”
野哥横了李虎一眼,心道,他妈的!就你这怂样也算是沧州一条虎?难道你这头虎连翻墙越院的雕虫小技也没学会?不过要紧的是先找到淳于荷,所以野哥理都没理李虎,一把抓起他的衣领,一个飞身已经越过李虎家的院墙,悄无声息地落在院子里。
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走动,只是在后院里影影绰绰有灯光闪烁。
“云飞扬就住在你家后院?”野哥压低声音问道。
“是,他昨晚把我和我老婆给赶了出来,独自一人就住在我的卧室内。”
“带我去。”
“是。”李虎此时已然知道了这个阴晴不定的年轻人绝对是一个比云飞扬更可怕的主,不过绝对不会比云飞扬阴毒,所以他也盼望着云飞扬能够栽在他的手里,并且顺利夺回自己的家产,所以他只是简短的说了个是就蹑手蹑脚地带着野哥向后院走去。
李虎家的后院挺大,以被荷花池环绕假山为中心,分别建有二十几间大大小小的房屋,其中正北略微偏右的一间非常豪华的房间内隐隐透着灯光。
“云飞扬住在什么地方?”
“亮灯那间就是。”
“你可以找个地方先歇息了,如果我发现你耍我的话,你全家照样一个保不住。”
野哥没等李虎说话,整个人已经掠向亮灯的房间,轻轻用沾了唾沫的手指透开一个小洞,野哥发现果然是云飞扬果然就在房中,只见他依然穿着他那身披金挂银的一袭白衣,面上洋溢着一丝得意的微笑。
淳于荷呢?荷美人在哪里?他妈的,莫非李虎那小子说假话骗了自己不成?不可能呀,再怎么着那小子也不敢拿全家性命跟自己开玩笑不是?
再一次用目光认真地搜寻了一下房间可能有人的地方,可是,依然没有淳于荷半点儿的身影。
突然,云飞扬抬步向房间内室紧闭的门走去,吱呀一声推开房门,寝帐垂帏,内室的一张大床露出一小半来,床上斜卧着一个人,只见下半身而不见头颈……
淳于荷!当野哥的目光落到床脚边的地上时,他赫然看到淳于荷的飞虹剑正躺在地上,野哥瞬间便破窗而入,整个人迅速袭向想要关闭内室门的云飞扬,一种想要杀人的冲动不觉又充斥在愤怒的胸膛之内。
云飞扬正要接近床上之人,突然听到窗户破裂的声音,于是慌忙转身,却见野哥已经堵在了内室的门前。
“野人,你要干什么?!”云飞扬迅速拔剑,怒目逼视着野哥。
“干什么?”野哥嘴角一扬笑道,“我要看看你在我老婆面前怎样被人割去你那杆习惯性阳痿的肉瘤呀?”
“你老婆?”云飞扬吃惊道,“难道朱依依会睡在我的床上吗?”
“当然不会,要睡也是你妹妹睡在哥的床上才对。不过哥今天不跟你讨论你妹妹怎样被我睡的事,哥今天只想问你愿意保上面这颗脑袋呢,还是保下面那颗脑袋?”
“野人你不要欺人太甚,淳于荷是我未婚妻,我怎么着她都跟你没有关系!”
“是吗?”野哥邪魅一笑道,“难道她没有告诉你她已经是我老婆了吗?”
云飞扬见野人把淳于荷说成他老婆时如同吃凉粉一样顺溜,而且说话不带半点儿脸红的,一时间竟气得嘴唇发抖,脸色乌青,但他最终还是冷哼一声道:“你除会耍嘴之外还会什么?有种你跟我出去大战五百回合?”
“他妈的,老子跟你大战五百回合,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配?”野哥说着突然迅速出手,刹那间已经抓起云飞扬向门外扔去,耳中只听见哗的一声响,前墙竟然被云飞扬的身体给撞了个大洞。
野哥看都没看被扔出去的云飞扬一眼,他的一颗心全都悬在淳于荷身上,所以野哥一跨步便上前掀开了一直垂到床沿下方的红罗帐,床上躺的果然是淳于荷,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乌黑的头发散落在白皙的颈边,眉眼紧闭,唇角鼻梁全都如凝碧般静止,唯有眉心的一丝尚未消尽的愁绪才让人知道她不是一尊玉雕的美人……
☆☆☆☆☆
还好,她没有被云飞扬那厮给非礼,望着淳于荷依身上然完好的男装,野哥不觉松了一口气,可是,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她弄醒,可是,怎么才能把她弄醒呢?
不管怎样,一定要先把她带出去,既然云飞扬那厮敢到半路去打劫,就绝对还有别的安排,如果放在平时野哥一个人的话,野哥肯定很乐意跟他耍一耍,可是现在——
野哥爱怜地望了淳于荷一眼,一伸手抱起仍在昏迷的淳于荷,把她的头搭在他宽大的肩膀上,左手托着她的翘臀,脚尖一钩,淳于荷落在地上的彩虹剑应声而起,野哥手握彩虹剑拔步就往外走。
刚到门口,野哥就凭他敏锐的直觉感到有重重杀机逼近,于是迅速往门后一闪,只见十数支箭光闪电般穿门而入,一阵噼里啪啦地声响之后,正对门口的后墙上便刺猬般钉满了精钢打造的弩箭。
他妈的,云飞扬你还是不是人呢?好歹淳于荷也算是你未婚妻吧,难道你就不知道这些箭很有可能会要了淳于荷的命?
“野人,如果你现在放下她一个人走的话,我云某人念在你我还算有些交情的份上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你就等着变刺猬吧,哈哈哈——”
“哼!姓云的你有种跟你野哥比上几招,你以为你弄几张破弩就能挡住你爷爷的去路吗?”
“当然,这几十张硬弩是挡不住你野人,可是,把你身上那丫头射成刺猬是绝对不会成什么问题的!”
他妈的,看来这厮的确不是个东西,竟然先用迷药迷倒荷美人,而如今又拿荷美人进行要挟,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想到这儿,野哥便说道:“云飞扬,我可以放下淳于荷一个人走,但是你要告诉你哥今天打劫的目的!”
“哼!告诉你打劫目的又能怎样?淳于荷是我未婚妻,我现在想让她提前变成我老婆,难道这关你的事吗?”
“云飞扬!你他妈的还是人吗?你简直就是禽兽嘛!哦,不不,哥骂错了,你要是禽兽的话,那禽兽与你为伍岂不是太委屈了?”
“野人!你——”
就在云飞扬被野哥骂得七窍生烟时,突然听见屋顶上哗的一声响,只见野哥已经抱着淳于荷穿屋顶而出……
用剑拨开箭雨,野哥的脚下的屋顶在迅速向后飞驰,眼看就要越出院墙了,突然一支飞镖从斜刺里向淳于荷飞来,想躲已经不可能,用剑格挡也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野哥索性来了个迅速侧身掩护,只听噗的一声,飞镖已经没入了野哥的左肩……
快步如飞地跨过高低错落的屋顶,闪过街巷,然后顺着旷野上的一条小路奔跑,终于,在一个渔火闪烁的河边停了下来,野哥望着悠悠的河水,驻足于一棵高大的柳荫下,轻轻放下软香玉似的淳于荷,星光下她脸如凝玉般恬静,恬静得让人惊叹。
该怎样让她醒过来呢?野哥望着潺潺的河水,于是便灵机一动,撩起衣襟就扯下一大块布来,一纵身就跳到水边,把手中的布深深地摁到水中,吸满水后,然后重新回到柳树边,用蘸满水的襟布轻轻擦拭着淳于荷的额头和脸颊……
“淫贼!你以为逃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吗?还不快把她放下!”
野哥一甩脸,发现云飞扬正笔直地站在身后,剑尖指着野哥,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哈哈哈,没想到你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我淫贼,哥就是淫了她你还能怎么样?你能吃了我吗?你以为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也配?”
野哥起身盯着云飞扬卑鄙无耻的脸上绽放的义正词严地冷笑,习惯性的并不辩解,而是在他正义的唇角悬挂出一脸透着邪恶的微笑。
“无耻小贼。”一个透着冰冷的声音从野哥耳侧响起,是淳于荷的声音,她什么时候醒来的?野哥脸上的微笑一下子被冰冻了起来,她早不醒晚不醒,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醒呢?
野哥万分绝望地回望着淳于荷冰冷的脸,知道解释已经毫无意义,所以野哥依然如以往般邪魅一笑道:“哈,美女,你睡着时的样子似乎比醒来时要好看一些嘛,为什么不再多睡一会儿?”
“多睡一会儿,正好被你这淫贼糟蹋是吗?”云飞扬恰到好处的用他冷如冰的声音敲打着迷蒙的夜幕。
“卑鄙无耻。”淳于荷缓缓吐出这四个字时,泪水迅速滑落,闪闪的泪珠在星光下流淌着难言的伤感……
弯腰拾剑,慢慢直起身子,散落的秀发的发梢在淳于荷迅速转身的一刹那间甩在野哥的脸上,轻轻地擦眼而过,颊上的轻柔瞬间消逝,而野哥的心却被那掠过的青丝给击成了重伤,溢满胸腔的血,只有他自己才能闻到的血腥味。
云飞扬开始追赶淳于荷的脚步,就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野哥突然出手,用十层的掌力拍向云飞扬的脑袋,他不能让云飞扬这如此阴险的畜生伴在淳于荷的身边,即使换来永生永世不被淳于荷原谅的痛苦,他也在所不惜,为了他心中女神般的荷美人,他什么都敢做。
云飞扬似乎早有防备,只见他的身子迅速向外弹射,在野哥紧跟的一脚踢到时,他的人已经躲到了淳于荷的身后。
当野哥发现淳于荷用她那杨柳般婀娜的身体挡在云飞扬的身前后,只好收起自己已经踹出去的那只脚,因为收势过猛,野哥一个不稳,整个人如一头巨狮般栽倒在地,可是就在野哥栽倒的那一瞬间,云飞扬的剑已经凌空刺出,剑指咽喉,一招非常凌厉的杀手。
完了,野哥一下子闭上眼睛,他不知道他的下一站是重新回到二十一世纪,还是会穿越到别的朝代,或者,被黑白无常领着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
“噗——”左肩一冷,野哥睁开眼睛,发现他尚未拔下飞镖的左肩又挨了一剑。
血,顺着云飞扬拔出的剑喷射而出,他看到淳于荷的剑在他眼前一闪之后回鞘,他知道,这次,又是淳于荷救了他的命。
“荷妹,你为什么要救他?像这种人渣,还是杀了他比较好,省得留在人间再祸害别人。”云飞扬盯着淳于荷的眼睛,满口热血侠义之语脱口而出。
“不要让他这种人污染了我们的剑,我们走!”淳于荷冷冷地看了野哥一眼,转身离开,云飞扬恶狠狠的盯了野哥一眼,亦随淳于荷一起转身而去……
月牙儿慢慢从东边的草丛间升起,一条渔舟打水靠岸,渔船上一个黑影跳上河岸,一个少女,看不清眉眼,抑或压根就没有人看她,野哥闭着眼睛,默默地静听肩头流血的脉动声。
“你这人好奇怪呀,受伤了也不知道包扎一下,失血过多一样会死人的!”少女的声音很柔,如河里柔柔的流水。
“你觉得我像是会死的人吗?”野哥一翻身坐了起来,他望着站在面前的少女的脸,突然觉得这脸在哪儿见过。
“你当然不会死了,你死了我嫁给谁呀?”
“你嫁给谁跟我有关系吗?”野哥再次望向少女,脸上的笑容不觉暧昧了起来,“看来孔子说的果然不假呀,失去一棵浪漫树,你将面对一片俏拔林。”
“你认出我是谁了?”少女脸上的笑不觉灿烂了起来,“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嘛,竟然在你失去一棵树木时,及时充当了那片森林的排头兵。”
“筠儿,孙怀远孙神医的女儿。”野哥悠然起身,看了一眼仍在向外渗血的左肩,咧嘴笑道,“你为什么不问我孔子到底有没有说过那句失去树木,面对森林的名言?”
“我是叫筠儿,但不是神医的女儿,神医只不过是我舅舅。”筠儿同样微笑地望着野哥,“至于树和森林的名言,我根本就不用问,因为我知道那句话是你家邻居姓孔那小子说的。”
靠!果然是钉子户,看来今天非被她钉住不可了,不过此时被神医的外甥女钉住也不算什么坏事,毕竟可以请她顺便处理一下伤口嘛,一想到伤口,野哥刚才还没感觉的伤口突然就疼了起来,于是野哥就指着筠儿的鼻子骂道:
“你真他妈的不是人,还说什么要嫁给老子,难道长着一双贼漂亮大眼睛的你就没看到老子身上的伤口在流血吗?”
“当然看到了,如果不让你流血流到知道疼的话,你怎么能忘掉人家云飞扬的老婆呢?”
筠儿咯咯笑了两声后,拉起野哥的手不容分说就跳到了渔船上,一猫腰钻进芦苇搭建的船舱,迅速倒了一盆热水,筠儿毫不羞怯地扒下野哥的上衣,望着野哥肩上深深的剑伤和依然钉在后肩上的那枚闪着绿光的飞镖,筠儿眼里的泪一下子就来了:
“云飞扬这个狗娘养的还真不是东西呀,把人家相公伤得这么重不说,竟然还在镖上喂毒,此仇不报老娘非女人!”
“靠,你别骂了不行吗?你再多骂一会儿,哥的血就多流一些。”
野哥见刚才还笑嘻嘻的筠儿竟然在剥开自己的衣服后泪飞顿作倾盆雨,心里就突然温暖了起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面对筠儿时竟然如面对墨白时一样,忍不住就想大爆粗口。
“我马上就给你包扎。”筠儿拔掉飞镖,用暖暖的小口往外吸了几口血之后,又用不知道加入了什么药的热水很小心地给野哥擦洗着伤口,“奇怪,明明镖上是喂了毒的,你怎么会没有中毒的征兆呢?”
野哥一听筠儿说那支飞镖上喂了毒,不觉又在心里把云飞扬的祖宗八代中所有女性同胞给问候了几遍,不过,因为知道自己有百毒不侵的肌能,所以野哥便大大咧咧地笑道:“中毒征兆?行走江湖,被对手一包小药就撂倒的人还算是人吗?”
筠儿见野哥对毒具有先天免疫能力,于是就一边替野哥包扎一边附和道:“对!被一包小药就撂倒的人,真他妈的不是人,自己不是人也就算了,为什么还偏偏害得人家相公也不是人?”
靠!这话听着怎么就这么像骂淳于荷呢?难道这小丫头一直蹲在旁边看热闹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