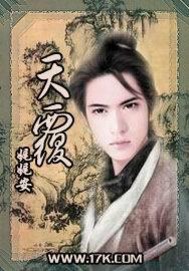夕月见此情景,却咬着牙跺着脚,连声说道:“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晨星不解地问道:“又是谁惹你生气了?”夕月指着吕伋的背影道:“除了他还有谁?那大叔只不过帮他捡了几块饼,他都还知道称谢。我可是救了他的命,他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这还不可气吗?”
晨星安慰她道:“姐姐,算了,这些庶民不知礼数,你又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夕月是个直心快肠的人,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晨星安慰了几句后,她便说:“唉,主公曾经教过我们,要施恩不望报。我之所以救他,也是听见那小女孩哭得可怜,这才出手相助,原也没指望他感恩戴德。”
晨星抿嘴一笑道:“夕月女侠扶弱抑强、打抱不平。向来只为匡扶正义,却不贪图名利,小女子对女侠素来仰慕,简直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夕月脸上一红,也笑着说:“哼,你仗着书读得多,就知道取笑我。我们还是快走吧,小姐该等得着急啦!”
两人沿着这条街并肩向西而行,晨星边走边说:“姐姐,我不是在取笑你。你一向都是舍已为人,难道我做妹妹的会不知道么?我只是不懂,你为何就是要跟周公子过不去呢?”
夕月知道她是在说周考,脸色立刻就变了:“那周公子一看就不是好人!之前在温泉谷的时候他就鬼鬼祟祟惹人生疑,只是那次没有抓到他的把柄。可是昨日在集市上,他刚到朝歌就买了两个女奴;这次可是我们众目睽睽亲眼目睹,他再也无法抵赖——他大概没想到会被我们撞见,这才露出了马脚。都到了这一步你还要帮他说话?”
“哎呀!我什么时候帮周公子说话了?!我只是觉得……他这么做,或许是另有用意……”
夕月打断她道:“什么另有用意?你难道忘了我们是怎么来到苏侯府中的吗?”
晨星低头不语,半晌之后才说:“我怎么可能会忘?我们被父母卖给奴贩的时候,才只有五、六岁。奴贩为了让我们听话,每天都要毒打虐待我们;还不让我们吃饱饭,生怕我们有了力气就会想逃跑。如果不是老爷把我俩买了回来,只怕……只怕我们会和其他女奴一样……”
晨星一想到幼年时的遭遇,便吓得浑身战栗,再也说不出话来。两个人沉默了一阵,夕月才接着说道:“有的女奴被奴贩逼迫,做出那些令人作呕的勾当,你我都是见到过的。只是因为那时我俩年纪太小,才得以幸免。但是我也听过,有些寡廉鲜耻的人却是专挑年纪幼小的女奴,买回去后对她们百般摧残。你自己也看到了,周公子买的那个女孩最多不过八、九岁的样子,你说他还是个人吗?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晨星摇了摇头,还是说道:“那不一样的。我见过的那些去买女奴的男人,他们的目光淫邪猥亵,看着便叫人害怕。可是周公子的眼神清澈、目光正直,却与其他男子不同。”
“唉,我的傻妹妹,你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什么眼神啊目光啊,这些统统都靠不住。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就只会凭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去剖析他的内心,这世上的男子任他怎么花言巧语,也休想骗得过我。”
晨星觉得夕月的话也是不无道理,她问道:“可是如果两个人不当面解释清楚,万一你误会了他怎么办?”
“误会就误会,我这叫做「宁杀错,毌放过」。反正这世上的男子没几个好的,就算误会了,最坏也不过是将来永不相见。总好过被他骗,为了他黯然神伤、痛不欲生。”
晨星听了,仿佛自言自语般说道:“就是因为世上的好男人太少,如果此生有幸能遇见一个温文尔雅、至情至性的男子,就更应该珍惜才是。怎么能因为一场误会便永不相见?姐姐如此决绝,就不怕将来嫁不出去么?”
夕月仍是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我就伺候小姐一辈子。我们这条命是老爷救回来的,主公教我剑法,小姐又教你弹琴作曲,苏氏一门对我们姐妹恩同再造,即使今生今世也报答不完。就算我将来孤独终老,只要能埋在苏城城外,那便死而无憾了。”
“姐姐说的是,我们能有今天,全是仰仗苏府的荫蔽,这已经是不知几世修来的福气了。如果还想着要嫁个如意郎君,那可真是贪得无厌,只怕是要折福折寿了。”
她俩这么边走边聊,终于渐行渐远,暂且按下不提。再说吕伋和邑姜回到逆旅后,吕伋全身无力,只能躺在卧榻上。邑姜坐在一旁陪着他,一边还在不住抽噎。之前吕伋还一直盼望着父母能早些回来,可如今他生怕自己这副狼狈样被双亲看见,因此又希望他们回得越晚越好。
有道是怕什么来什么,吕伋躺下之后不久,门外便传来父母的说话声。先是听吕尚说:“你为了这二十朋贝,竟耗了一上午时间,也不知值不值得。”接着琪姜道:“怎么不值?二十朋贝足够添置不少家具了。等我们搬了过去,要买的东西多着呢。”正说着,两人便推门进来,吕伋赶紧面朝墙壁侧躺着,不敢让他们见到自己脸上的伤。可是邑姜却不懂做作,一见母亲之面,便咧嘴大哭起来。
吕尚起初还以为是吕伋淘气把她给惹哭了;而琪姜一听女儿的声音便知道不对劲——她知道女儿撒娇时也会哭,但那哭声中总有些嗲声嗲气,只要哄得几下便会没事;而此时邑姜却哭得声嘶力竭,直听得琪姜心中一酸,差点跟着掉下泪来。她上前一把抱住邑姜,颤声问道:“出什么事了?”
邑姜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哪还说得出话?她把头埋在母亲怀中,却伸出手来指着哥哥。琪姜顺着女儿的手看去,只见吕伋仍是不敢转过身来,但他的后背衣服皱皱巴巴的,上面还沾着不少尘土。琪姜使劲扳过吕伋的身子一看,不禁惊呼道:“哎呀!怎么被人打成这样?!”
吕尚闻言大吃一惊,忙走过来看时,只见吕伋的头也破了,脸也肿了,上衣的前襟和两袖被扯得破破烂烂;吕尚又把儿子的衣裳掀开,只见前胸后背上全是一片片的红印。吕尚看了琪姜一眼,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是谁下手这么狠毒?难道仇家这么快就找上我们了?
吕尚于是赶紧追问事情的经过,吕伋开始还不肯说,但经不住父亲的再三追问,才将被打的始末完整的讲了出来。琪姜开始还埋怨吕伋道:“不是叫你不要出门么?你怎么就是不听?”吕伋自知理亏,不敢顶嘴。而吕尚思前想后犹豫再三,却对琪姜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们还是尽早离开朝歌为好。”
琪姜有些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伋儿不是说了?那些人不过是几个年轻的小无赖,想索要些财物罢了。为什么要离开朝歌?”
吕尚叹道:“我怕他们只是受人所雇,以索要财物为名制造事端,再借此机会对伋儿下手。”
琪姜仍是不敢相信:“不会的,如果真是我们的仇家,只怕伋儿和邑儿此刻已经遭了毒手了。他们……他们是不会留活口的。”
“唉,说不定他们就是要让我们看着两个孩子遭罪,让我们心里难受。等到他们将我们一家折磨够了,这才痛下杀手!”
琪姜想了想,自言自语道:“我们还不知道,救了伋儿的那两个女子,又是什么来历?”
吕尚“哼”了一声,说:“说不定那两个女人也是对头故意安排的,是用来迷惑我们的疑兵之计。”
“那,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吕尚在房中来回踱了两步,这才说道:“事不宜迟,今晚就动身。”
这时吕伋忽然勉强撑着身子说:“要走你们走,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吕尚大怒道:“混账!这件事不关你个人的荣辱,而是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岂能由得你胡来?”
吕伋却犟着说道:“那几个混混丝毫不会武艺,当时我但凡有件趁手的兵刃,也不至于落败。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
吕尚这才想到:以前曾有不少武艺高强的杀手来追杀我,尚且未能得手。如果这件事真是我那仇家所为,又怎么会让几个不会武艺的人前来挑衅?想到这里,他从一口木箱中翻出自己的佩剑,想要亲自去探探这几个混混的底细。吕伋见他拿出剑来,便问道:“父亲,你要做什么?”
吕尚答道:“你要报仇,我这就去替你教训他们。”
不料吕伋却说:“不!这个仇,我要自己亲手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