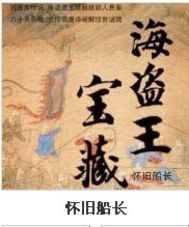西南地区某机场。一个“very special”机场。
咋说的,她占当今世界几个之最——海拔最高、冰面铺道、四周终年白雪皑皑、空气稀薄、对流激荡。当年抗战时期,许多中美王牌飞行员在此折戟沉沙,到现在,飞行员常能看到山谷里的飞机残骸、当年飞行员的护目镜、手枪等。
这里的天气更奇葩——刚才还阳光灿烂、银装素裹,转眼间就冰雹肆虐、大雪纷飞,如同得知你交不起房租的包租婆,变脸比翻书还快。
总之,这就是喜怒无常、高寒阴冷,非常人所可征服。
在这茫茫雪域高原上,矗立着一个海军特种作战部队的前沿基地。
当海军当到高原上,换谁都挺无语的。
熄灯了。夜凉如水,月光皎洁,操场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与周围的雪山上的雪光相映成趣,整个营区笼罩在银白之下,不禁让人想起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
在床上“辗转反侧”的高宪绅,索性爬起,悄悄跑出宿舍,换了一身体能服在操场上作曲臂伸。
白天的训练仅仅是测试他们的体质。尽管他跑过很多5公里,但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上跑,还是第一次。缺氧、气短让他呼吸困难、头脑昏胀,这些高原特质全都在他身上体现,让他严重怀疑自己的体能。
在高原当兵太难了!
凛冽的寒风奏响了第二天的黎明。
戴着氧气面罩、一身病号服的高宪绅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手上还打着点滴。
“你醒了?”一阵风铃般的问候声传入耳畔。这声音,犹如重获甘霖的春笋,使他焕然一新。高宪绅转头望去,发现床边竟坐着一个女军官:衣领上一杠三星,是个上尉;棕色的皮肤、娇小的身躯、过耳的褐色短发、樱桃般的小嘴,双眼中不加掩饰的征服欲,把一名特种部队作战主官的严肃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如同一泓清水的双目,又为她增添了几分高雅的气质,让人不能不魂牵梦绕。
她颠覆了高宪绅对高原兵的认识!准确说是高原女兵,因为即便是在海军水面舰艇部队等高科技含量的单位,都没有这么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兵。不,是女干部。
高宪绅的心“嘭嘭”的,比往常跳的更快了;想坐起来:“首长……”
她立马阻止了高宪绅:“躺下吧。”
“这是哪?”高宪绅躺下后,好奇地看向四周问。
“医务室。”
“啊?”高宪绅懵了,“我怎么在这?”
“我这刚回来,就看你躺在障碍场上,不冷啊?”
高宪绅这才想起,昨晚正在加练,后来好像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总教官推门进来,看到她后,眼前一亮:“嘿?你啥时回来的。”
“昨晚。”然后指着高宪绅,“我看他晕到在障碍场,就送过来了。”
总教官先是把高宪绅说教了一番,然后告诉他好好休息,今天集训队集体高原反应。还有眼前的这个女军官叫刘凌韵,以后是集训队的副总教官。
“副总教官好!”高宪绅想敬礼,但身体没答应。
“省省吧。”刘凌韵摆了摆手,对总教官说:“你先回去吧,这有我就行,队伍不能没有主官。”
“行,那麻烦你了。”
高野走了。
刘凌韵走到床前坐下,问:“高宪绅是吗?”
“是。宪法的宪,绅士的绅。”
刘凌韵点点了头。看着他微微笑了起来。
高宪绅疑惑:“怎么了?”
刘凌韵:“我很喜欢你的名字。”
“谢谢。”高宪绅有些害羞,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您的也是。”
刘凌韵有一次笑了,“放松点。”然后,又想起了什么,问:“你刚才说是说,你喜欢我的名字?”
高宪绅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些什么,刚想解释,刘丽嘉却先发问:“说说看。”
“说什么?”
“我的名字。”
高楠想了想,又偷偷瞄了她几眼:“壮志凌云的凌,雅人韵士的韵。”
刘凌韵有些惊讶,略有所思。
“我说错了吗?”高楠问。
“想出去转转吗?”刘凌韵反问
“啊?”
“不去算了。”刘凌韵作势起身要离开。
“别!去,去!”
因为身体还依旧虚弱,所以刘凌韵用轮椅推着他。
“爸爸!”远处一声稚弱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个小姑娘欢快地跑向总教官的怀里。总教官抱起她,满是欢喜地和一个女人谈笑风生。
“她们是总教官的家人?”高宪绅好奇地问。
“对。”刘凌韵答道。
看着这一家人温暖和睦的场面,高宪绅的眼里有泪花闪动,但他还是强忍了回去。
但依旧没逃过刘凌韵的注意。仔细看着轮椅上的少年,一个熟悉的人进入她的脑海......
他们停在一个休息亭。
高楠率先问:“副总教官......”
刘凌韵打断她:“以后私底下,我是说就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一,不要对我用敬称,二,可以叫我灵云。”
这么豪放?高楠有点意料不到,但还是继续问:“家里人,怎么样。”
但回答他的,只有呼啸的寒风。
“我爸爸是个试飞员。”良久,刘凌韵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着高宪绅说。
高宪绅惊呆了。试飞员是航空兵部队最危险的职业。因为,鬼知道飞机第一次飞会出什么幺蛾子。
“小时候,总是吵着要见爸爸。10岁后,爸爸的照片摆在了客厅。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说到这,刘凌韵的眼神多了几分忧伤,“后来,我报考了空航校,追随了父亲的脚步。”
高宪绅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美女上尉经有这般身世。但又很纳闷,按理说,她应该是航空兵,现在却和高野一样一身猎人特战迷彩。
“后来,出了意外,我被停飞了。因为不甘平凡,当了特种兵,成了你们的教官。”刘凌韵微笑着说。此时,她收起了先前的伤情。
高宪绅虽面不改色,但内心已是波涛汹涌;一方面,这样的问题她居然会这么直白地告诉他,另一方面为她说这些,似乎和她毫不相干。
究竟是多大的磨难能塑造如此强大的意志,塑造出这种镇静与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