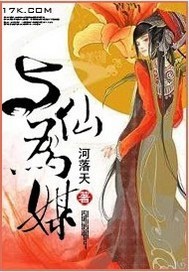说罢,洛然带着温瑶开始一一为帐中的伤兵查看伤势。
然后洛然与军医一起进行会诊、商议治疗方法。
温瑶则在一旁默默听着,不时帮忙做个记录,或者打一下下手。
直到两人商议一个士兵的伤势,温瑶才从记录的手札上抬起脸。
这个士兵叫王小虎,是苏将军手下的一个骑兵,也是伤得比较重的一个,陨石谷偷袭时,因为帮苏将军挡了一刀,手臂被乌兰人连着肩部砍断,失血太多,伤口又化脓了,一直处于发烧和昏迷的状态,都说是不行了。
军医的意思就是如今只能用汤药尽量吊着性命了,保守治疗。
而洛然却不太想放弃这个年轻士兵的性命,令弄哥将随行带来的三七等止血方子,先给王小虎服用,同时再进行退热的处理。
军医一听有三七,脸色松弛下来几分。
三七可是外伤用药中的金不换,行军打仗的人多半都知道,在军队中也会常备一些,只最近丰城战事频繁,三七早就用竭。
温瑶看一眼最里头的帘子里病床上正痛苦闭着眼的王小虎,深吸口气。
王小虎被连根截断的那条断臂连接肩膀处,包扎着纱布。
缠绕了好几层的厚厚纱布被乌血与脓液浸透,还鼓鼓的,应该是有个大脓包,看来已经感染化脓了。
而让王小虎高热不退、至今昏睡不行的原因,怕也是刀伤造成的严重感染。
三七固然对王小虎的伤势有些帮助,但,这士兵现在是急症,下一刻可能就会全身器官衰竭、断气,若想救下王小虎的性命,怕是得尽快消炎。
抗生素……
她头脑里第一个便想到这个在现代无人不知、使用得也相当频繁的药物。
只可惜,在现代没什么稀奇、人人都能用的这个药,在眼下这个年代,却是个空话。
“温遥——”
洛然的声音拉回温瑶的思绪,这才回神。
“快点记录,发什么呆?”洛然有些不满。
温瑶想也不想,脱口而出:“洛院使,不如放脓吧!”
这话一出,军医愣住。
洛然脸色也是沉下来。
半晌,军医才道:“小兄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伤者现在命悬一线,喉咙里只有一口气,别说用刀子割开脓液放出来这么大阵仗,便是连一个小小的咳嗽都可能经受不住。这样做,岂不是直接送他死?”
“我知道这样很危险,可若不这么做,他又能活么?”温瑶反问。
左右都是个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
指不定还能奔出一条活路。
军医正要再说话,却听洛然声音响起:
“我也同意。”
温瑶望向洛然,没料到他居然同意自己的风险极大的做法。
要知道他一路上可没睁眼瞧过自己。
洛然没看温瑶,只望向军医:“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念在伤者伤势太重,怕他受不住这激烈法子。但没料到我这位副手,倒比我更加干脆,果决,大胆。也罢, 那就按照他的提议做。劳烦你去准备一些麻药,还有剔骨刀,火炉,纱布,黄酒等物……”
干脆,果决,大胆……这是洛院使在夸赞自己?温瑶有些懵然,却已见洛然交代完,看向自己:“还愣着?”
温瑶忙点头,跟着洛院使走到王小虎床边。
…
放脓的过程,是洛然亲手操刀的。
温瑶在一旁则细细地观摩着。
果然是二十七岁就成为三品院使的当朝御医。
为王小虎伤患处涂上麻药。
然后将剔骨刀尖用酒与火频繁进行消毒。
待麻药药效上来,手起刀落。
手法极其利落,果决,与其人外表的文质翩翩完全不一样。
昏迷中的王小虎呼吸频率都没怎么改变。
手臂边地上的木桶里已经是脓血哗啦了一桶。
刚刚还肿胀得高高的脓包,就跟消了气儿的皮球,一下子瘪了。
温瑶见他操刀完毕,立刻上前为王小虎清理伤口,然后小心翼翼地包扎起来。
随后监察了一下王小虎的身体状况,转身汇报:
“洛院使,伤者脉搏略快,但尚算正常范围。呼吸也尚算平稳。暂时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
但还不算过了危险期。
只有体内炎症彻底消除,退烧了,醒来,才算过了一关。
洛然自然也知道王小虎眼下只能算过了一劫,但想真正脱离危险,还得看今明两天,只嗯一声,将剔骨刀放入盆子里,转身去净手了。
……
从营帐回到驿站时,已经是深夜了。
临走前,洛然又被苏将军单独叫去,便让温瑶与弄哥先回驿站。
回到驿站,进了房间,温瑶虽是累了半天,却毫无困意。
今天,还是没见到元谨。
离去的时候,她忍不住回头,那么多帐子,也不知道他住在哪一间。
是不是真的受了很严重的伤。
不知道苏将军临走前将洛然单独叫去,会不会就是让他去单独为元谨这个世子爷诊治?
倒也有这个可能。
她一下没了睡意,想等洛然回来再问个清楚。
夜色一点点加深,直到过了凌晨,才疲倦至极,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眼睁开时,她发现自己又来到了那个梦中的空间。
这次,在茂密的药田里,最先进入她视线中的,是一株颜色比较独特的孔雀蓝色药草。
也是她的知识范围内搜索不到的药草。
所以,应该也是与之前一样,是在这个空间里杂交而生长出来的药草。
按照以往这空间的尿性,这孔雀蓝的药草,指不定就是可以救王小虎的东西。
她蹲下身,采下几株,刚放进袖袋里,耳边响起砰一下开门的声音。
温瑶猛地从桌边坐起来。
隔壁传来开门声,洛然回来了。
她先从袖袋里拿出孔雀蓝药草,在灯光研究了会儿,才收好,然后出去,走到了洛然门口,敲敲门:“洛院使,是我。”
“进来。”
温瑶进去后,看见洛然刚换下了在营帐中的衣服,是一袭白色长衫,看着越发清隽如仙,又刚净过手,手上还散发着一股清新的胰子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