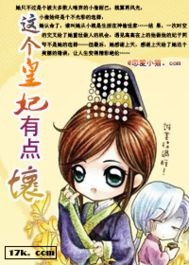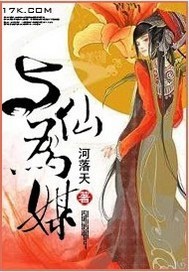“不是说你已经找到了解蛇毒的办法了,为何情况还会恶化?”盛君行着急的看着傅太医问道。
傅太医也说不上来,按照盛君行给他交代的,他也以为阮小小体内的毒已经好多了,可没想到就他给阮小小把完脉后发现,阮小小的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阮小小可是刘玉娇现在唯一走上荣华富贵的稻草,要是阮小小真的出事了,她日后该怎么办?
“原本阮小姐体内的蛇毒确实已有好转,可还是出了点意外。”傅太医看了看在场众人,对盛君行说道。
闻言,盛君行立马就明白傅太医的意思了。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盛君行抬眸冷视,瞥了眼在场的人后,向傅太医说道。
傅太医告诉盛君行,他在阮小小的房间闻到了一股苠秀草的味道。
苠秀草或许在别的毒面前起不到什么作用,可是当它遇到的是蛇毒那问题就大了。
它可以加快中毒之人的毒性发作。
“也就是说,阮小姐之前虽然有所好转,但在苠秀草的作用下,现在情况十分危险。”傅太医垂首,完全不敢直面盛君行。
盛君行一听,不由得紧握起了拳头。
“昨晚傅太医离开之后,谁还去过大小姐的院子?”老夫人看向陈嬷嬷立马问道。
“回老夫人,自傅太医走后,除了锦绣之外,便无人进过大小姐的房间,不过……”陈嬷嬷听了老夫人的所以对沉香院的一举一动很是关注。
老夫人拧眉,“不过什么?”
陈嬷嬷将视线落到了刘玉娇身上,“今儿一早,夫人回来去看过大小姐。”
刘玉娇顿时瞪大了双眼,苦笑道:“你们不会怀疑是我吧?”
她再怎么说也是阮小小的亲娘,更何况阮小小对她来说很重要,她怎么可能对阮小小下手。
“到底是不是很快就知道了。”老夫人冷眼一撇道。
傅太医嗅了嗅,确实有闻到一股苠秀草的味道。
于是,不由自主的跟着味道寻去,便走到了刘玉娇的身边。
“傅太医,你这是做什么?”刘玉娇看着傅太医的样子,内心是抵触的,“傅太医不会是认为什么苠秀草与我有关吧?”
“这可说不一定。”阮氏不嫌事大道。
“还请夫人将身上的香囊取出来给我看看。”傅太医向刘玉娇伸手道。
刘玉娇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想都没想就把香囊取给了傅太医。
傅太医从香囊的缝隙中找到了苠秀草的粉末。
阮氏见状,讽刺道:“你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小小的亲生母亲,可到头来要害小小的还不是你这个当母亲的,真是可笑。”
“不,不可能,我不可能害小小。”
刘玉娇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香囊里怎么会有什么苠秀草,她根本就不懂药理,如何知道苠秀草可以加重蛇毒发作。
“证据确凿,这还有可狡辩的,弟妹你也真够狠心的,小小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女儿呀,更何况虎毒还不食子。”阮氏一副看好戏的样子说道。
刘玉娇心里顿时来气了,情绪也是相当的激动,“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要不是你女儿嫉妒心重,才会害的小小中了蛇毒,说起来要不是你女儿的话,小小怎么可能会躺在那儿!”
“你没管教好自己的女儿,现在又有什么资格说我女儿。”阮氏立马又维护道。
“你……”
“都别吵了。”老夫人跺了跺拐杖,呵止道。
盛君行冷眸一扫,“倘若本王的未婚妻有个什么好歹,本王倒是不惜多些人给小小陪葬。”
听着盛君行冷如冰窖般的语气,加上他那幽深的眼神,不禁让大家打了一个寒颤。
盛君行说完,立马带着傅太医前往阮小小的沉香院。
同时让丁寻和随同前来的侍卫将前厅给包围起来了。
老夫人面色凝重的握着拐杖,刘玉娇呆滞的站在原地,阮氏更是胆战心惊的紧握着双手。
刘姑姑不由得摇了摇头,着实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娘,现在可怎么办?”阮氏走到老夫人身边,一脸担忧道。
老夫人瞪了一眼阮氏,“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
“傅太医都说了,小小中的蛇毒已经有所好转了,是她。”阮氏立马指向刘玉娇,“要不是她拿了什么草来,让毒性发作,小小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
“都说了,不是我。”刘玉娇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阮氏翻了一个白眼,“东西是在你身上搜出来的,不是你,那又是谁?”
“总之,我不可能害小小。”
“说不上来了吧,我看你就是个毒妇,当年也不知道继成看上你什么了。”阮氏一直都不太喜欢刘玉娇这个弟妹。
刘玉娇毫不礼让道:“你又能好到哪儿去?照样还不是被人家给休回来了。”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吵。”老夫人被阮氏和刘玉娇吵的头都疼了。
阮氏和刘玉娇相视瞪了一眼后,各自别开脸。
而盛君行刚才听傅太医那么一说,心里有些没底了。
“傅太医,当真没办法了吗?”
傅太医顿了顿,“苠秀草药力不强,但味道对蛇毒极为敏感,老臣……”
说着,傅太医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了。
“傅太医,无论如何你都要救救她。”
老实说,傅太医也是第一次听到从盛君行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
“倘若阮小姐不给点提示,或者自己没有提前预防的话,老臣怕是也无能为力。”
傅太医倒是想帮盛君行的忙,可自己也不是华佗转世,如何能将人从生死边缘拉回来。
可是谁又能想到苠秀草会是阮小小的亲生母亲带来的。
待傅太医再一次给阮小小把完脉后,整个人都有些无力了。
盛君行从傅太医遗憾的眼神中读出了答案。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盛君行的心情跟着跌落到了谷底一般。
傅太医摇头。
除了先后离开那时,这是第二次让盛君行有了前所未有的无助感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