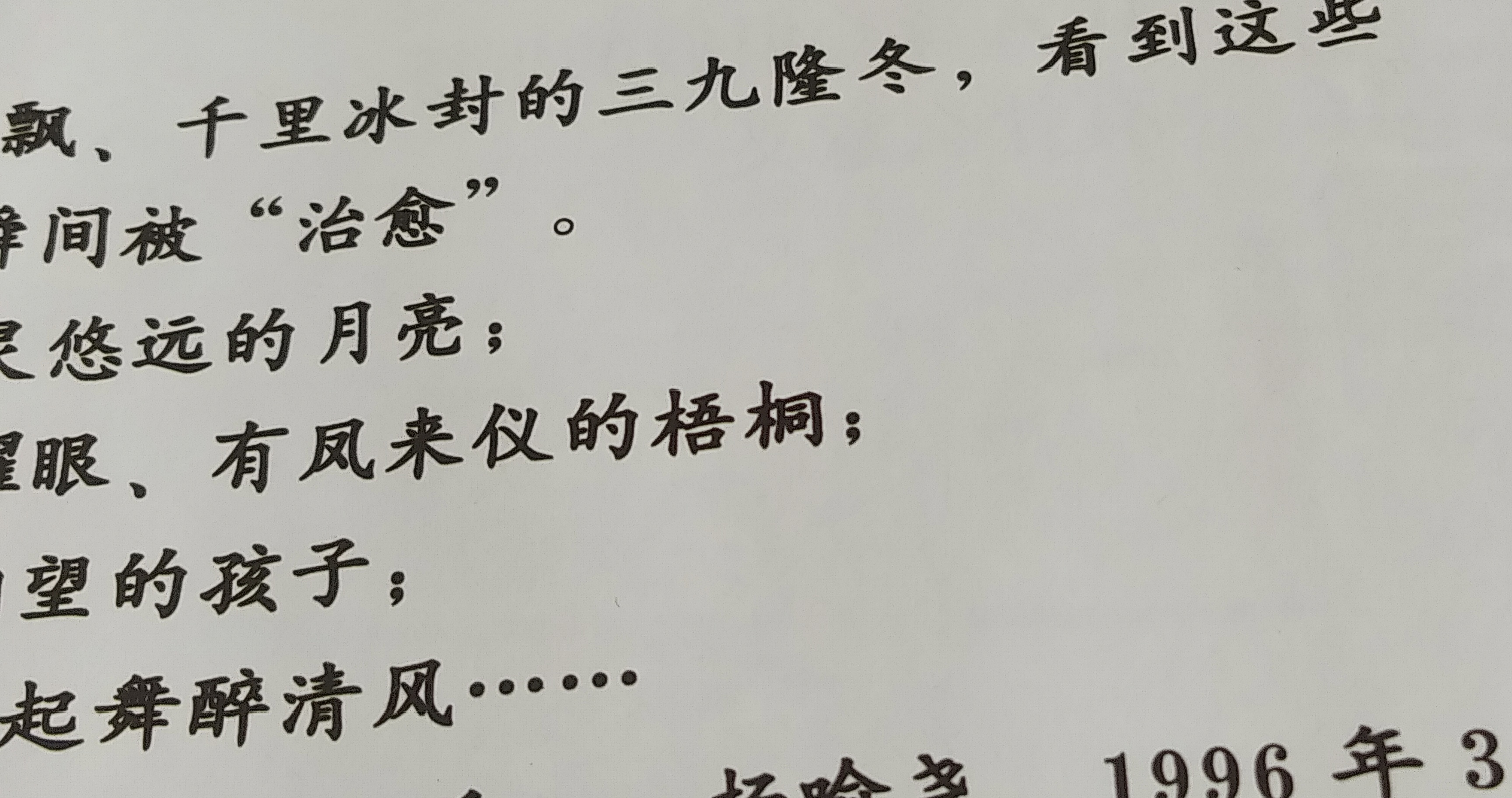“可最荒谬的事情就在于,杨长风找来的那个人,压根不会骑马。”姜蘅摇了摇头,叹道。
顾媺并没有怀疑她的话,或者换言之,她相信姜蘅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个胆子骗她。听着这么一桩奇闻,她瞪大了眼睛:“怎么回事啊!”
姜蘅笑了笑:“谁知道呢。”
语气轻淡,仿佛不是什么值得在意的大事。
然而顾媺心中却犹如激起千层浪。
小姑娘心思简单,回头第二天进宫就把这事当成热闹说给了宫中诸位娘娘听,当然,在场的还有皇上。
顾明华听她说这些,原本也就只是想着给孙女两分面子,奈何这中间种种越听越觉得熟悉,尽管当时孙女于堂中讲述时模糊了事主身份姓名,但是事后顾明华还是将人叫过来,仔细问了始末。
得知果然是盛安伯府闹出的幺蛾子之后,他龙颜大怒,又让人去彻查杨家找来顶包的男子,果然,出身农户,一辈子只知道牵牛耕田,哪里会什么马术!
但这也只是小事罢了,左不过一个农户子,但盛安伯府如此胆大妄为,还是该敲打敲打,只是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处理此事时,玉京城里忽地便热闹起来:短短一夜之间,不知怎么,城中各大茶楼酒肆里的说书人都开始讲起盛安伯府上这桩热闹事。
当然,民不与官斗,平民百姓怎么得罪得起盛安伯,自然是用春秋笔法模糊了一番故事的原本面容,但这层膜盖得薄,但凡稍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听得出来这讲的便是盛安伯府仗着皇上倚重,做下丧尽天良勾当的新鲜事。
舆论一再发酵,眼见着几乎控制不住,正值此时,信王又呈上一沓书信,便是蒋昼任职工部时,与淮城太守之间往来的书信,信中详尽地记录了两人是如何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地借由兴修水利之事,贪污国库公银。
“启禀皇上,臣得此书信,原欲立时上奏,奈何受奸人要挟,是故不得已隐忍不言,”顾远润位列群臣之首,转过头去望了一眼身后面色惨白的盛安伯,又继续道,“蒋昼与傅骋二人,欺上瞒下,目无法纪,枉为人臣!还请皇上明察此事。”
傅骋目光惊愕地看着他说完拱手,笔直的身板弯下去,一颗心如坠冰窟,全完了。有个声音在他的心底轰然响起,某些东西忽然坍塌,只剩下满目废墟,烟尘飞舞。他呆愣愣地站着,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很久之后,直到龙椅之上传来皇帝震怒的声音,顾远润才抬起头,直起身子。
到这里,蒋傅两家的事,便成定局——削爵的削爵,罢官的罢官,流放的流放。
散朝之后,傅骋跌跌撞撞地走到顾远润身边,恨声问道:“王爷是不是忘了,微臣手中同样捏着王爷的把柄!您就不怕到时候信王府与盛安伯府一般,落得个玉石俱焚的下场?!”
蒋家的人已经如同过街老鼠一般,走在众人前头,早早出了宫。
顾远润微微笑道:“什么把柄?盛安伯大可看看,究竟是你手上的把柄多,还是我手里的证据多。”他停下脚步,附到顾远润耳边,声音轻缓,“溪晟山上枉死的那个书生,你还记得吧?”
他说完,轻笑一声,大步往前行去。
铿锵有力的话语声尚且弥留于傅骋耳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傅大人。”
杨长风从后面出来,跟在傅骋身边,面带狐疑之色:“伯爷难道不曾发现,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凑巧了?简直就像是……”
像是有人提前设好的局,将他们所有人都算计在了其中一样,甚至这里面还牵扯到郑宴的死。
周遭陆续从大殿中走出来的文武大臣们,纷纷将好奇的目光投射在杨长风和傅骋身上,傅骋被他们看得如芒在背,深觉这张老脸实在丢不起了,只得轻声对身边的年轻人道:“回去再说。”
……
顾远润回到王府的时候,姜蘅已经等在后院了。
上次姜蘅离开之后,顾远润就吩咐过管家,如果以后姜蘅再来找他,那么就将她请到后院。
见着顾远润回府,姜蘅连忙迎上去,虽然其实已经笃定事情的发展会按照她的预料进行,但等真正见着顾远润时,她心中还是有些忐忑:“王爷,怎么样了?”
顾远润点了点头:“你找人将舆论散布在玉京城里坊市之中,本就已经在皇上心中种下了怒气的种子,再加上傅骋还胆大包天为了蒋昼要挟本王,更让皇上怒火中烧,而因为溪晟山书生的事,傅骋却不敢轻易将我的把柄放出来,自然只能吃下这个暗亏。”
“但是皇上终究顾及老帝师,将此事高拿轻放,看起来重惩了蒋傅两家,然而实际上,他们除了名声扫地,损失一些蝇头小利之外,并无大碍。你有没有想过,你做的事情被他们查出来之后,会迎来怎样的报复?”
姜蘅戒心很重,现在也没有告诉顾远润葬身溪晟山的书生是郑宴。故而两人言谈间,始终以溪晟山书生代指郑宴。
将顾远润的话听进耳中,姜蘅笑了笑,道:“怎么会没有大碍?皇上猜忌心重,经此一事,定然不会觉得蒋傅两家欺上瞒下,运作的事只有这么一桩。就算他顾及老帝师,不忍重惩傅家与傅家的姻亲,但老帝师也是人,人生一世,也不过草木春秋,终有枯败之时。到那时,王爷且看,老帝师的名头究竟还好不好用。”
她这么一说,顾远润仿佛眼前豁然开朗,他呵呵笑道:“罢,是本王着相了。你倒是一桩桩一件件算计得分明。”
姜蘅欠身,面带歉色:“臣女知错。”
顾远润说她算计,不仅是在说她对傅家的算计,也是在说她对顾媺的算计,如果不是她和顾媺说的那些话,顾媺又怎么会进宫和帝妃们说起,从而牵引出这之后的诸多事件。
姜蘅也正是为了这事道歉。
顾远润摆了摆手:“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姜蘅正色道是。
一旁蹲在假山后的小丫鬟将两人的对话悉数记在心中,而后悄悄返到顾媺所居的堆云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