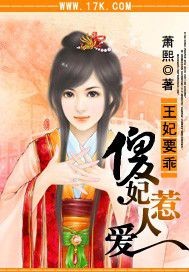灯火通明,云雪澄澈里,忽然有飘渺乐声从云外传来:“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旧年山川,如今心眼,还似故人楼……”
姜蘅偏过头,看向顾远洲。
顾远洲的心思一向不好猜,姜蘅也无心去想顾远洲究竟是有感而发,还是话里藏了什么深意。
但无论是什么意思,话总是没有说错的。来这世间走一遭,总要行远,总要登高,不然没什么意思。
“好了,夜里冷,我让衡暝送你回去。”顾远洲低头看着她。
姜蘅“嗯”了一声,转身走在他前面下楼。
到马车前,她转过头望了一眼,但见楼前挂了一块匾,看得出来已经有些年头,连角都缺了一块,上面用行草书了名字:梦鱼台。
她将这个名字记在心里,然后转身进了马车。
顾远洲和衡暝交代了几句,也从一旁牵了马,一车一马,便于此地分道扬镳。
马车将行时,姜蘅撩开帘子,看了一眼顾远洲离开的方向,她微微拔高了声音,问衡暝:“你家殿下,今晚有事?”
衡暝挠了挠头:“姜小姐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姜蘅“啊”了一声,反问他:“我应该知道?”
衡暝低声嘟囔了一句,他这不是不知情吗,还以为姜小姐知道,殿下才特地到姜家找了姜小姐呢。
他不再说话,一路上沉默着,等马车驶进槐花巷,到了姜府两座石狮子前停下,姜蘅提了裙摆下车之后,他才叹了口气,道:“姜小姐,今天是殿下的生辰。您也别怪他先前走得急,想必他走的时候,宫宴已经开了,若是到得晚,朝堂上那群老匹夫,指不定要说得怎么难听。”
想到顾远洲之前说的“着急”,姜蘅心绪复杂起来,又有些愧疚,如果早知道今天是他生辰,那在马车上,她就不会给顾远洲下毒了。
她揉了揉眉心,将身上的绣囊接下来,这里面装了她之前让人去打的平安锁,原本是想着送给花月,如今却只好拿来借花献佛。
她把绣囊递给衡暝:“代我祝你家殿下生辰安康,喜乐顺遂。这是生辰礼。”
衡暝高兴起来,觉得姜小姐心里也不是没有他家殿下的嘛。
他笑着收下,态度都殷勤许多:“您放心,小的一定将您的心意带到。姜小姐早些回去,夜里风寒露重,再有两天可就是除夕夜,您多保重。”
姜蘅点了点头。
她回到芳汀苑里,用了晚膳后又在灯前坐了一会儿,而后很快去榻上睡下。
日子流水似的在一年的花枝春草尖上淌过去,淌过蝉鸣烈日,淌过白露秋风,总算淌过了荒苔云梦。
除夕到了。
说来也没什么新鲜,但到底是好日子,姜家上下都摆出了笑颜,所有人都好像忘记了从前不愉快的日子,只觉得一年总算到头,新的一年里有无数新盼头,众人都打心底里高兴起来。
过了除夕,便迈入正月。
正月里的玉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回老家丁忧奔丧的盛安伯府一家,回来了。三年孝期已满,盛安伯府傅家的姑娘们俱已经长成了花一样的容貌年纪,公子们也都到了适婚的年纪。
虽然傅家离开三年,玉京局势早已变换,但是傅家的功绩摆在那里,更别提帝师犹在,傅家重回玉京权势中心,不过是时间问题。
由此,盛家姑娘公子们的行情,在玉京里还是很吃香的。
这不,一家人刚回来,不过半月,拜帖请柬就已经收到手软。其中真正和盛安伯府有旧的,想要叙叙旧情的,无非那么几家,剩下的,则全是存了相看的意思。
盛安伯府,书房。
盛安伯傅骋坐在主位上,打量着面前面色霜白的年轻人。
“你方才说,可以让杨将军举荐我出任兵部左侍郎?”他笑了笑,“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我傅骋任官,何时需要旁人举荐?”
论私交,他与皇上打小一块儿长大,几十年的情分做不得假,何况他父亲是帝师,单就凭这一点,皇上也不会眼看着傅家没落;论公理,他曾镇压叛军,清扫流寇,是皇上手中最得力的一把剑,如今丁忧归来,皇上如何会不重用他?
在见杨长风之前,他还听说这是杨家如今最出色的人物,却没想到果然闻名不如见面,竟是这么个不知深浅的黄口小儿。
他难掩失望,甚至懒得和杨长风虚以委蛇:“杨将军素来治家有方,却教出你这么个儿子……”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杨长风打断:“伯爷且听我一言。”
“诚然您简在帝心,是皇上心腹,阔别三年,而今归京,皇上当然没有不提携您,提携傅家的道理。但您再想想看,三年未有往来,皇上真能对您放心?”
“这是其一。”
“其二,如今皇上年事已高,虽储君已定,但诚王,信王俱是人中龙凤,超凡脱俗之辈,乾坤未定,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待将来……您说,您是该忠君还是忠国?”
“若是忠君,您忠的是哪门子的君?若是忠国,您忠的,又是哪门子的国?”
“但若是换成家父与朝中诸位大人举荐伯爷,您本身,兼之身后的盛安伯府,便不代表任何立场。至于老帝师,那是上一辈的事情,再加上老帝师已经不是伯府掌权人,更与您,与伯府无甚相干。”
他这一番话,可谓掏心剖腹,只差没有指着皇天后土,赌咒发誓了。字里行间,一句句,无一不是站在伯府的立场,为伯府着想。
不管他真实目的如何,但就这一番话,着实存了十成十的真心实意。
傅骋面色缓和下来:“是老夫看走眼了,小友说得不无道理。只是,此事暂且搁置,我倒有另一句话要问,你找到老夫,不会只为了说这些吧?你的目的是什么?”
杨长风抿了抿唇:“听闻伯府四公子尚未婚配,杨某家中有位三妹,德言容功,四者咸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