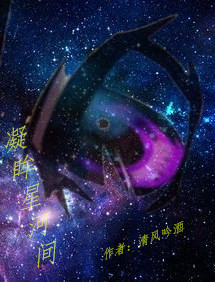楚离立在床边,身姿清朗,狭长的丹凤眼原本魅惑轻浮,却因多了分专情投入而夺人心神,惹人沉醉其中。修长俊美的身形投影在颜汐娇小玲珑的身上,楚离听着她一下一下的呼吸声,心不自觉地被牵动。
他在床沿坐下,像一个孩子似的不敢弄出太大的动静,怕惊动她,上回深夜前来藏月殿探望她伤势已是身不由己,这次更是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他只知道,每时每刻能见到她,于他亦是奢侈的。他不能再奢望更多。
楚离轻轻执起颜汐的柔夷,以掌握住,她的手白嫩细滑,骨节分明,比起上次又消瘦不少。他感觉到了她的心苦和挣扎,却弄不明白这份悲苦从何而来,她才只有十七岁,却好像是已然历经人世沧桑,看透世间轮回。
更叫他想不通的是皇兄和颜汐之间突然冷淡下来的关系。他越来越看不懂她在想什么。
楚离叹了口气,她始终是后宫中人,与她共处一室,传出去于她不利,他转而放下她瘦弱的手。此番确认她没事,他就安心了。
就在手掌即将松开之际,颜汐却牢牢抓着他的手不放——
“不要走——别丢下我——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昏迷中颜汐的神智模糊不清,根本不晓得紧抓着的是谁的手,只觉得心中异常悲苦,像握着救命稻草似的拉着楚离的手不放。
她像个逮住人就胡搅蛮缠、死抓不放的稚童。嘴中零散的话拼接不成完整的一句,带着孩子般的哭腔,让人莫名的心疼。
楚离瞧着她娇俏可掬的赖皮模样原本觉得好笑,等听懂了话里的意思,他温柔地拍了拍颜汐的手背,默默地安慰她。他很想知道,她有着怎样的过去。
第二天一早起来,天色已然大亮,估计是睡得久了,身上懒懒的没什么力气。
颜汐起身洗漱后唤了春进屋替她梳妆打扮,锃亮的铜镜里印出女子莹润的脸庞,她原本长得就美,不必刻意修饰依旧明艳照人。春挑了套素净的宫裙伺候主子换上,颜汐点头说好,穿上才发现是仿制江南的样式,整个人格外的清丽灵秀。
自入宫后,她便很少再穿朱红色的纱裙,那鲜血一般的颜色,仿佛是她双手所沾的杀戮浸染出的。
待喝下一小碗养胃的素粥,颜汐一人朝着皇宫最高处而去,春想跟去,她拒绝了。
独身而来,颜汐脚踏平整的玉石阶梯而上,整整一百层的石阶均是以白玉砌成,光泽柔美。这儿是整座皇宫地势最高的金台,距离地面近百丈,站在最高处可以将整座皇宫尽收眼底。深秋时节,寒意侵袭而上,她立在金台之上,果然,整座皇宫一览无余。
再向远处眺望,皇宫之外逐渐模糊不清,原来所谓的金台也只不过是将人困在这座冰冷的宫廷之中。风过无痕,撩动她耳边几缕发丝,身后有深沉的脚步声传来,她半侧过身,万丈的亮光里一身龙袍的皇上拾级而上,目光幽深,他也是只身来这金台。
颜汐托了李公公帮忙传话给皇上,有些事她只能向他求证,毕竟他是整件事的筹谋者,最清楚全部的细节。她没有想过最后竟要从自己的仇人口中得知那些被掩藏起来的事实。
“皇上能来,慕容汐很是感激。”皇上虽未挑明她的身份,但在萱美人病榻前她的言辞表现已经说明了一切,她的身份不言而喻。至于他为何按兵不动,不铲除后患,她仍未想通。
她要的只是报仇,将楚澈从皇位上拉下来,至于那把龙椅是谁来做,她一点儿都不在乎。
“汐儿——”这一声沙哑的呼唤,他期盼了十年。而她的冷漠是最锋利的刃,直击他的心。他们之间,明明不用这么漠然相对的。她对他的恨,深入骨髓。
皇上强忍着胸口的闷痛,微咳几下,愈显清瘦,涵妃曾说她一直在为皇上配药调理,莫非他有什么久治难愈的病症?
颜汐差一点就要心软,她望了望天边大片大片的云朵,攥紧了拳头,只冷声道:“你的汐儿早就死了,死在你的手上。”少时的美好邂逅,踏雪赏梅的光景一去不返,全被深埋在了时间的洪荒里,楚澈,你究竟明白几分?那些好时光,回不来了。
楚澈唇边唯余了苦到极致的笑容,他那样温润的男子,如玉石般清远,此时也只剩了无力:“我全都明白。”伤害她的悔恨和愧疚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十年来他遍寻她而不得见,每每想着怎样才能弥补她,他还不了她一个慈爱的爹,还不了她一个温柔的姐姐,还不了她一个完整的慕容山庄,除了财富地位他什么都给不了她。
他唯一拥有的是景国的江山,但纵使他把整座江山双手捧到她面前,她也是不屑一顾的。他看重的东西在她的眼中一文不值。
“还记得那年第一次遇见你,我被其他皇子打得趴在地上,狼狈极了。一个娇俏可爱的小女孩义正言辞赶走了欺负我的几个皇子,还扶我起来帮我在伤口上上药,药粉沾上伤口一瞬间很疼,我满腹委屈忍不住哭了。我以为小女孩会嘲笑我软弱没用,却没想到她奶声奶气地对我说她摔着碰着哭得比我大声多了。”
年少的烂漫时光总是那么美好,像新鲜的草莓,酸酸甜甜,和她在一起的十几天是他活到现在最快乐的日子。冰天雪地里,她的容颜比那傲立于枝头的红梅还要美艳夺目。
“若不是你在宫宴上为我求情,父皇大概早已忘记他还有我这个儿子。我承认,是我利用了你的单纯来引得父皇的注意。”
父皇膝下的皇子有十几位,向来子以母贵,那些皇子的母亲身家背景非富即贵,是父皇在朝中大肆笼络的势力。而像他这样没有外戚势力支持的皇子就只能备受冷落,无人问津。他们母子三人在芳华殿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他发誓要手握权势,成为人上人,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大臣宫人不敢再小瞧了他。
“讨得父皇的喜欢后我仍旧低调,伪装成体弱多病难成大器的模样,极少与朝中官员往来,而在深夜我就拿出《国策》、《兵法》独自学习,钻研个中精髓。你离宫的那天,母妃咳了血,我亲自去太医院请了张太医过来,直到母妃服了药睡下后,我才朝宫门直奔而去,可守卫告诉我你已走了近一个时辰。”
话到此处,楚澈站在颜汐右侧,与她一同眺望远方,不知不觉眼眶含了热泪,自眼角流淌而下:“楚熵骄横暴躁,李釜认为我易于控制暗中与我结盟,而我正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于是我允诺李云殊皇后之位。”
昨日冷宫传来废后暴毙的消息,他听了没说什么,只命人厚葬,云殊的悲剧又何尝不是他造成的?君临天下有太多的无奈,不得不让一颗心变得冷硬无情。
“慕容傲是楚熵最大的支持者,亦是父皇的至交好友,唯有扳倒他我才能击垮楚熵登上皇位。”楚澈顿了顿,这些话他本可以说得平静,成王败寇,在政治上无须同情对手,需要的只是除去绊脚石,可是真说了出来他才发觉其实他和父皇一样,为了坐稳皇位变成了冷血残酷的孤家寡人。他厌恶他的父皇,可到头来他也变成了父皇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