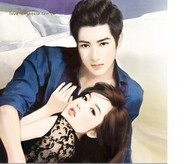【英瑞王府】
“你这些时候操劳过甚,如今新病与旧疾共发哪是能快些好的。”宋逸耐心答复。
“我只怕陛下受了委屈。”
宋逸笑了笑,“你的人不是已来报一切安好吗?她又非懵懂稚儿何至于如此挂心担忧。”
祈拯没回他,因为当一颗心只有一人时无法控制自己不想不念。这绝不是面对兄长的女儿应有的态度,他清楚地知道却依旧放任自己深陷其中。
“王爷能康复,此乃国之大幸啊。”平时与他疏远的大臣纷纷笑呵呵地向他道贺。
祈拯虽不大清楚缘由但依旧不失礼数地回了他们。他心里警惕起来,毕竟政见不同一向势同水火的人是没有可能突然缓和关系的,只能是别有目的。
重新立于朝堂上,祈拯很明显地感知到异样如今的朝堂已然乃陛下的一言堂。他心下欣慰的同时也不免升起几许失落,祈蕴已经不再需要他襄助了。他知她实力暗藏,却始终不忍心她委屈一分一毫。他甘愿做她手中的利刃,为她披荆斩棘。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至于那有违伦常的爱恋他只会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四国宴举行的日子到来,四国分别是云启、沧岸、水泧、煌枼其中云启和水泧皆为女帝。虽然各国意图不纯但面上仍旧是和和气气的,所以宴会的气氛维持着表面的融洽。直到有人高声道,“云启和水泧两位女帝正值妙龄,沧岸和煌枼两君更是后位悬空,不如两两缔结姻缘也好共续世代太平。”
祈蕴抬眼望向对面的齐烁,他同样望过来嘴角微扬勾出一个略带寒意的笑。祈蕴不用猜也知道,其中肯定有他的手笔。祈蕴冷冷一笑,“何时一国之主的婚事竟无法自行决断?”
齐烁舀起一勺汤,“不过一条谏言,不听也罢,何至于坏了心情?”
祈蕴不予理会,她可不想搭理无聊的人,冷处理是她喜欢的方法。有的人就是越搭理越来劲。
齐烁一见她这满不在乎的样子便来气也顾不上旁人拂袖而去。一时间桌上只剩祈蕴,水泧国女帝——水听澜和煌枼国的国君——旭钰远。国君们宴饮是处于独立的宫殿之中并无随同的人,所以外边无从知晓发生何事,这也是为了保守机密。
祈蕴淡淡开口,“见笑了,不若谈些紧要之事?”她略掉容貌不俗但生性软糯的水听澜,径直看向旭钰远。
出了封闭的宫殿,祈蕴感受到微凉的夜风心情微微放松,一下子就看到了一旁等候的祈拯。她略微有点尴尬,这种有人等候的感觉令她很不适应。她活到现在不曾主动靠近他人亦不与人深交,可是祈拯却不管她态度如何始终带着一颗真心守护她,哪怕不被感激且没有回报……原来他是慕元却也不是慕元。慕艳眼眶微微刺痛,双目泛红有泪光闪烁。祈拯见她神色不对不免心疼但他刚担忧地向前便被侧身避过了,祈拯看着她略显寂寥的背影眼底涌起一抹哀伤。他深深明白他的陛下从不愿与人有过多牵扯 ,因此她极少料理政事只为了少与他接触。他岂会不知?但仅能装作不知。
凉爽的月夜,月亮受浮云遮挡而朦朦胧胧。慕艳带来的官员对她十足十的畏惧勉强撑起了云启女帝深不可测的人设,今夜那违规的惩罚总算是消停了。但她却迟迟不能入睡,黑暗会使人的情感无处隐藏而刚才祈拯看向她那一眼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她脑海中。
祈蕴夜里睡得不安稳,一早上脸上都是掩不住的疲倦。祈拯见她这样也是放心不下,他隐隐察觉到这与他有关系但却始终猜不透想不明。
祈蕴是真没想到齐烁还有后招,她也是弄不明白一开始那容貌俊秀潇洒不羁的侠盗怎么现在这么的斤斤计较。花园里齐烁笑吟吟地向她走来,他安排的隐蔽于房顶和树上的人向下洒淡粉的桃花瓣。纷纷扬扬的花瓣如雨落,落于众人的发上、肩上。花园内不少大臣在场,祈蕴眉头一皱心底升起不小怨念。祈蕴向冷着脸的祈拯展露一个安抚的笑,她缓缓道,“昔时有冒犯在此致歉。”祈蕴慢慢走到齐烁面前,低声道,“你还要玩儿到何时?”
齐烁气急反笑,“你不信我的诚意抑或不愿信?”他将祈蕴和英瑞王间的无声交流收在眼里,心里是止不住的苦涩。
祈蕴仰面仔细观察见齐烁神情不似作伪,一时无言。说到底还是她的错,若不是她凭借先帝的信任留下了那份改立诏书又怎会有遗诏被盗之事?
齐烁看着祈蕴走远,眼底闪过一缕暗芒。果然是薄情寡义。
最终沧岸国国君还是未能如愿,祈拯松了口气。他心底终是不愿见到陛下与他人携手一世的。
【凉薄看着侧卧在榻上的慕艳试探性地开口,“齐烁好像真挺喜欢你的。”
“所以呢?”慕艳翻了个身,“不是所有情感都能得到回应的。我没有给人救赎的习惯,因为我自己就在深渊。更何况我对什么都喜欢不起来。”
凉薄被她的回答弄得一头雾水,只觉得她的处事态度很消极。】
在祈蕴午间小憩的时候,祈拯收到了挚友宋逸的飞鸽传书上面只有四个字“小心祈蕴”。他在后厨引火将字条烧毁而后净手 面不改色地做糕点。白皙修长且骨节分明的手将模具翻转,洁白如玉的糕点配合着雅致的造型散发出淡淡的甜香。
慕艳只是浅眠,察觉到声响便睁开了眼睛。祈拯见她醒了便把端着的那碟糕点放在桌上,“可是臣打搅了陛下歇息?”
她凝视着那清澈透亮的眼眸终是摇了摇头道:“并无。”虽然她心下烦闷但并不想迁怒他人。
“臣为陛下做了糕点,不知陛下可否赏脸一试?”祈拯语调舒缓捏起一块糕点向她靠近。
慕艳盯着面前的糕点在反应过来之前已经张开了嘴。祈拯注视着乖乖张嘴的陛下,脸上笑意不断。慕艳刚咽下最后一口糕点,喉间泛起一阵血腥味。她回了他一个微笑而后向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他离开,背对着他躺下。当房门闭拢,慕艳再也忍不住恶心呕出血来。当子蛊备受煎熬之时母蛊也会狂躁起来,她给上下官员下蛊如今也算是自食恶果了。宋逸发现异样后对中蛊者用了极刑吧,慕艳猜测。她苦涩地笑了,原来她没有残害忠良也改变不了剧情安排下祈蕴在世俗眼光里恶毒的形象啊,真是……她突然有些委屈,下蛊确实极端了些但她不认为有错,只有疼痛才能让人长记性更何况她从没催动过忠臣体内的蛊虫。
午后,慕艳倚在石栏边向水中抛洒饵料。水面上许多红白混杂的锦鲤浮出头抢食,激起圈圈涟漪。粼粼的水光映在她面上使脸色的苍白稍稍缓和。
水听澜鼓起勇气走进怏怏地喂鱼的云启女帝深深地屈膝行了个礼,恳求到,“恳请女帝出手搭救舍妹,令其不复返水泧。”
“带回云启?”慕艳搀扶起她。
“那便再好不过了。”水听澜听后感激地笑了,双手紧紧抓着祈蕴已然将她当成救命的浮木。
“一是挽回败局,二是不露于人前,当真是好名字啊。孤出手便不会无所取,你可想好了?”慕艳见她满脸真切的感激不由提醒了一下,也给她反悔的机会。
“绝不后悔,还望女帝相助。”水听澜手上不由用力了几分生怕她不答应,双眼噙满了泪,双手微微颤抖。
“可。”
水听沉和慕艳坐同一辆马车,这也让她有了思考怎么面对祈拯的时间。一边是挚友,一边是真心辅佐的侄女,慕艳不大想让他为难。她瞧了瞧水听沉只能说她眼前是一个清纯柔弱的女孩,她丝毫看不出他的破绽。从上马车到现在小孩就没说过话也没有左顾右盼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乖得过分。
水听沉低着头,他虽不知面临的会是什么但他知道他绝不能辜负长姐的殷切期望。他定会回去,堂堂正正地夺回水氏的江山。但他现今能做的是讨好云启女帝,只有如此他才能生存下去,才能……
慕艳看了眼瑟缩的孩子一个没忍住抱了抱他,她也曾有过害怕不安的时候但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慰藉全屏自己熬,那种不断习惯伪装坚强的感觉不好受。
这是除了长姐外第一个拥抱他的人,他其实是不讨厌的。厉家大权独揽更是操纵皇位继承他自小便佯装为女孩才得以存活。他每每见到长姐与窃国贼子逢场、方法可是……
水听沉醒来的时候马车已经停下了但他在车厢内不见祈蕴的身影有些无措,他怕自己睡过去招她厌烦。车厢内不知名的幽香也安抚不了他凌乱的思绪。
慕艳接过食盒并未转身进马车只是看着祈拯,“皇叔可否应承仅信孤一人?”
祈拯刚欲答应突然想到宋逸字条上的内容“小心祈蕴”,他怔了一瞬。慕艳并未立刻得到回答便猜到宋逸给他传了消息,她当即回马车总归有些失望。
水听沉在看到祈蕴时眼睛亮了起来。慕艳也不好在小朋友面前绷着脸,便抿唇笑了笑。水听沉察觉到了她笑容的勉强也不说什么,只是上前接过她手中雕花的食盒。食盒上雕的盛放并蒂莲让他动作滞了滞,因为听到了祈蕴和英瑞王说的话所以他甚至不敢深想。水听沉在慕艳的背后因而在她未落座前她完全错过了他如遭雷击的表情。
回到国都,慕艳叫停后径直掀车帘下了马车。水听沉乖乖跟着她下了马车。祈拯本想将祈蕴先完好送回宫却没想到她并不打算回去,眼下虽太平但难免有居心叵测之徒意欲行不轨,他怎能放心她独自一人呢?祈拯虽不明就里但还是立刻到她身侧,“陛下往何处去?”
“王叔府上。”
四国宴后英瑞王与小皇帝关系闹僵无人不晓,小皇帝的暗卫包围了英瑞王府执英瑞王的挚友的画面为不少人亲睹。
“端云公主以蛊驭臣下未免看轻人命过甚。”宋逸被结结实实地捆起,却仍不恼不怒。“端云公主”这一称呼暗含讽刺,为君者当以民为重,他不认可祈蕴的所为甚至认为她不堪为君。
“你大可执定所想,孤如何行事并非你可随意置喙的。”慕艳悠悠地道。
慕艳有意忽略门边的祈拯,直直地往外走。桑鹤率暗卫跟在祈蕴身后,众人皆着玄衣,腰上配的剑饰有荆棘藤蔓纹。他们只忠于主而非忠君,个个皆为利刃。
祈拯将目光从自始及终不曾回顾的祈蕴身上收回,他踏入屋内一时语塞。立侍身后的青锋上前将人解开。宋逸揉了揉因试图挣脱绳索而红肿的微微被磨出血丝的手腕,语间饱含无奈,“祈兄之托只怕小弟无法……”祈拯自然不可能强人所难,他吩咐青锋将人带去歇息而后看向地上的绳索,久久失神。
宋逸行走于雕花回廊下,一旁是青葱的竹从,阳光斜照,翠绿的竹叶恍若镀上一层金辉,光与影在他面上交错。
【安府】
虽临近日暮但大地还留有余热 ,慕艳远远看到安府前恭敬站着的安富心情不可谓不复杂。她有些后悔威胁朝臣时提到那蛊能让他们寻死不得了。其实说来简单,一个善用诡计的狡猾老臣因对幼子疼爱多方求医无果最后不得已取自己的血给幼子服下,希冀着那蛊能续他幼子的命。
安富十分不安,因他的缘故使女帝下蛊的事情败露他是真的怕女帝不给他那苦命的孩子医治。安富瞧见女帝来到赶忙跪下,一为请罪二为幼子求情。尽管不知英瑞王以名医的名头送进宫的人哄他喝的什么令他浑身疼痛,但他可不想没了礼数惹恼了女帝。
“起身吧。”慕艳之所以选择下蛊而非清洗朝堂也是秉承了能用就用的原则 ,因此对他们有一定容忍度。一世的好人难做,谁能担保起用的人一直忠心耿耿呢?她的注意力在人谢恩起身后便被吸引到了他鬓边,安富为人圆滑更是注重养生平时老态不显,而今却鬓边已皤。
慕艳不忍心水听沉一直默默跟着便让安富将人好生安置在花厅,自己则由管家带路去看看那以蛊吊命的孩子。
慕艳先挑起了个关于安洌的话头,管家便忘了恐惧一个劲地称赞。如果他所言不虚慕艳不得不说,安富自己虽不算个好人但独子养得不错。不过七岁,在明知自己时日无多而名医纷纷束手无策后知难而退的情况下也能处之泰然,实属难得。希望一次次破灭,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慕艳在知道安洌的卧房后推门而入,将管家留在外边。慕艳本以为他是睡着的直到靠近黄花梨雕花木床才发现他睁着眼睛,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动也不动倒是有些瘆人。
安洌在门发出响动时便睁开了眼,他睡的时候极少因为不知道哪天会无声无息地死去所以他总是不敢让自己沉睡。这样以亲人的血才活得的自己应该也不算人了吧,他宁愿死了可一想到父亲不惜损伤身体取血而后强逼他饮下,那样费尽心力令他活下去,他就下定决心不论以何种面目都要活下去……他看着出现在房中容貌明丽艳绝恍若天上仙子而非人间可见的女子少有地愣住了。
慕艳顺势坐到床边,右手抚摸他苍白胜纸而精致的面庞,“欲全性命乎?”
安洌早已无力气说话但还是拼命点了点头,强烈的渴望点亮了他的双眸。明亮的双眸璀璨如星似月。
慕艳无声叹了口气,暗想他年岁算小再加上如今身体只一息尚存应当不能记什么事便打定了主意。她抬手遮住他的双眼而后缓缓倾身将唇印上他冰凉的嘴唇。因为他体内有子蛊所以慕艳可以催动母蛊救他,不足就在于这会折损她的寿命。
在柔软的唇瓣覆上来时,安洌睁大了眼睛,嘴巴微张。哪怕眼前只见到她指缝间漏入的一两点光,他的嘴角还是忍不住上翘。忽然,倦意一点点席卷全身,他只觉得眼皮万分沉重,尽管他努力想保持清醒但只能感受到困意将他拖向一片朦胧。
慕艳忽然想到曾经那怎么也无法落下的吻,眼中浓郁的悲伤涌动,两行清泪划过面颊。
安洌感觉到了滴在脖颈温热的液体,他想睁开眼,费尽力气却也只能令眼睫微微颤动,眼前依旧是一片黑暗。
“陛下,小儿可还有痊愈之可能?”安富一将人安置好便赶到了独子的院中,他一见祁蕴出来便立刻行礼焦急地问到。
“不好说。”慕艳如实道。安富能寻她来救治必然是看过许多名医无果,名医都无法确定病症,慕艳自然也不能。没有缘由地觉得浑身疼通,慕艳觉得这病挺奇异的。每活一天都在忍受疼痛,慕艳有点佩服那个不大的孩子。她只能让活跃在安洌体内的蛊麻痹他,不至于让他日日处在疼痛中却没法治愈他。这也是蛊的其中一个不好之处,害人比救人容易。
安富听了这话立刻跪倒在地,满脸泪道,“还请陛下倾力一试,不说云启便是另三国的名医臣皆曾请来为小儿看诊过皆言……微臣自请献上祖辈所积蓄的家私和物产以充盈国库,如若不足,臣便向亲友告贷,只求陛下救小儿一命。”
慕艳轻声叹息,随后点了点头算是应下了。她不想让安富最后的希望破灭。他能说出那样的话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向素有恶名的端云公主求助……慕艳不知该夸他想法独特还是疼爱儿子有加了。
一天里的事不少,慕艳有些怀念祁曳在位的时候,虽然那时也有事但至少还是正事。慕艳缓缓走回寝殿,在遣人送水听沉去休息后只剩她一个人。她不喜欢留人伺候,别人心底里不情愿,她也不自在。
“臣恭请陛下安,襄太妃近来抱恙,陛下可要去瞧瞧?”颜敬给祁蕴行了个礼然后道。蔺家在太医院中根底深,他因站在先帝一派被排斥在外,所以常是清闲。襄太妃与曾经的端云公主有几分情谊,每逢身体不适便点名传召他看诊。先帝不常召太医,祁蕴不让任何人诊脉,所以诺大的宫里他的病人并不多。他对襄太妃便多上心了这么几分。身子上的毛病好好将养不成大问题,但心情沉郁能令人无病也生出病来。襄太妃虽有太妃之称但年纪并不是很大,他不知道一个过了双十年华没几年的女子怎会有那么多的悲情哀绪。请得陛下去作陪一阵是他唯一能为她做的了。
哪怕同在宫中但见面的机会不多,慕艳想起她曾经说的“殿下还宫使这宫中多了分人气”便道:“太妃既病了当去瞧瞧。可曾开了药给她?”
颜敬面露难色道:“恕臣唐突,太妃久存死念,非人力可治愈。”
慕艳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不相关的问题,“颜太医为何至今未婚配?”
颜敬有些尴尬道:“小门小户,难觅佳偶。”
慕艳经他那么一提倒记起来了,他父亲本是个游方郎中,碰巧治愈了富户家的小姐因模样俊俏又得对方的青睐所以最终和小姐结成了夫妻,但富户不同意这门婚事还和小姐断绝了关系。颜家无甚亲戚可依靠,颜父早逝,颜敬是颜母一手拉扯大的。曾经一个娇弱的小姐硬生生扛起了一个家的重任。颜敬凭才学入了太医院算是给家中添了固定的收入,但有些大家族的有意疏远也够让他吃些苦头了。云启整体还算可以但家中女儿优秀些的都希望她们高嫁或被选入宫,这种附强慕富的风气由来已久是极难一下子转变的。慕艳本想将颜敬和襄菀凑在一起,但她看得出颜敬对襄菀并没有那个意思。她也没有促成一对怨偶的癖好,颜敬对襄菀有些特殊却无意令她有些惋惜。
“陛下来了。”襄菀挣扎着从床榻上坐起来,脸上出现了一抹惊喜的笑。
“你应当好好照顾自己才是。”慕艳顿了顿才道,“若是许你离宫嫁与颜敬,你可会对人世多几分眷恋?”
襄菀仔细辨别她的神色,脸上的笑意渐消道:“我一垂死之人怎可无端毁人前程呢?由此可知世人大谬,端云公主分明再是良善不过了。死了于我才算真正解脱了。我知陛下不喜欢以权压人,怎能为了我如此呢?”
“可你……”慕艳还想说些什么却因她剧烈的咳嗽而停顿了。
“如今英瑞王回都,陛下该操劳的事只怕不少,陛下不该在我处耗力费时。陛下需记得,心中的善要分人交付,切不可对不值当的人留有善意。”襄菀以手中绣花帕子掩口轻咳了几声才接着道,“今年李花不似去年开得多,零星的几朵白花缀在光秃的枝上难看得很,好在陛下未看到。朝事我虽不懂但看得出来陛下对英瑞王的不同,若是陛下有心打压,只怕之前太后的信根本送不出宫去。现下英瑞王兵权在握,陛下也该当心些。旁人不信陛下思量英瑞王,我却是信的。”
襄菀没有活到她院子里的李子成熟的那天,或许在别人眼中她不过是一个媚君惑主的妖妃,但慕艳只觉得她也不过是一个可怜人。慕艳着人照她的遗愿火化了她的尸身然后她慕艳亲自将她的骨灰投入了流出宫外的活水中。有人退场也有新的人登场,人生的舞台从不缺唱戏的人。
“有人参皇叔而今有独揽朝政之嫌,皇叔心中可有何看法?”慕艳将奏折合上,笑着问到。
“臣问心无愧。”祁拯上前一步道。他挺直背同时向后看了一眼,只见朝臣纷纷低下头不肯与他对视。
因为文臣和武将分列而站,所以一干武将大都对着临近的文官面露怒容。慕艳往下看了一眼,手指轻轻在桌面敲击然后肃声道:“皇叔忠心昭昭,此事今后不提也罢。”她授意人上书此事并不是要借机处置祁拯,只是为了给后宫中最尊贵的太皇太后一个警告。祁曳在位时没让当时的太后插手朝事,慕艳自然也不想让她干预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