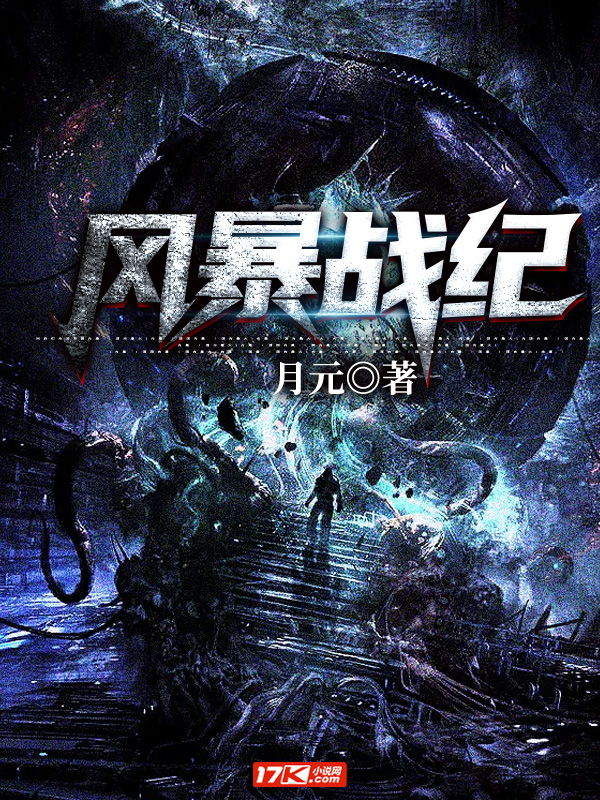就在阿真与蕃将怒目相瞪时,突然远方嘶吼声大骤,随即而来的就是大阵的嚎吼声和马骤声。
远处突然传起撕杀声,所有人皆愕地扭头向道路眺去,还没反应过来,忽然咆吼声大骤:“塔郭(周围)……啊……”
“杀!”大量的喊杀声掀天震起,人人都给震得耳中嗡嗡绕响。错愕的蕃将听到汉语杀声,额头滑下一排冷汗,见到追赶奸细的兵马狼狈败逃返回,立即调转马头,脖子突然粗了四五倍,扬喉咆哮:“度度度……(走、退)”挥鞭紧急逃命去了。
阿真和兔姑卡茫茫,不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愣目看了看怆慌逃走的吐蕃兵马,看了看如豺狼凶狠追来的大理兵马,现在是怎样?据他所知,雅砻江好像不是战场吧,怎么吐蕃和大理在这里打的这么热闹?
西江大将军麾下左先锋方天蚕,围截来追蕃兵,见到封锁的战地竟有夏周百姓,皱起眉头急拉马绳,怒目滚滚瞪着不知怎么会出现于此地的夏周人,阴阳怪气喝问:“你们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方天蚕一停,身边的数名副将急不可奈扫看夏周百姓,紧急道:“将军,别管这两人,还是趁胜挑了吐蕃寨窝吧。”
“挑不下的。”方天蚕心里明白,一个帅气翻跃落地,提鞭抬了抬微垂的将盔,对左右的将军说道:“老哈才刚败,昨天都不敢把头伸出来,寨里肯定守的极严,大将军可没有强攻的军令,太深入就违抗军令了,而且说不定中了老哈的计算。”
阿真站于萋草上看着这个姓方的将军,从铠甲的颜色与样式来看,这是名镇守一方大将军的先锋将军,年纪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张圆脸跟油烙饼有一拼,看上去既滑稚又可笑,明明就长着个福娃样,偏偏又冷板着个脸,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对属下说完,方天蚕转过眼眸打量跟前的男女,见着女的冷冷冰冰目光腥辣,似母狼般的凶狠,而男的……
“你们是谁?从哪里来?”见着阿真,方天蚕大惊,此少年看上去比自已还要小,可是一身浑然天成的尊贵浩气不容他人小觑。这还不是最让他惊讶的,让他惊讶到掉下巴的是,此少年无形之中有种让人心惊的压迫气息,仿佛天下唯他独尊一般,此气宇他活了二十五年也仅在公主身上感受过,不料在这里竟也有个气宇与公主一模一样之人,如何能不震惊?
好了,跟前站着的是自已的兵马,阿真卸下冷肃威严气息,裂开血盆大口观看突然受到惊吓的将军,呵呵笑道:“从夏周来的,刚刚差点被吐蕃兵逮去,现在遇见你们,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众将茫然,方天蚕既傻眼又狐疑,刚才还唯我独尊,怎么才一眨眼就地痞无赖了?死皱起眉头想不通阴森说道:“被吐蕃人带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夏周与我大理正打仗,落入敌国手中,你认为是庆兴?”
阿真含笑看着恐吓自已的将军,嘿嘿扭眸与兔姑相凝,摇了摇头道:“且不管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都没那个胆敢虐杀我们。”
“放屁!”还真的不曾遇到过这么猖狂的平民百姓,方天蚕麾下一名副将额头青筋暴跳,狠啐一口抡起拳头就要打。
阿真也不躲闪,笑咪咪对要欧打的将军凉凉威胁:“这一拳打下去,可就违了军令,你可以试试。”
“住手。”方天蚕急握住副将的手臂,目光冷冽直视阿真,眯起双眼道:“你是什么人?为何知晓我大理戒令?”
“语嫣公主治军之严天下谁人不知?”阿真呵笑竖起手指道:“也是因为语嫣公主对百姓爱如亲生子女,我才会说遇见大理军就好。因为你们是只会保护百姓,不会伤害百姓的英雄军队。”
这番话说的气愤的大理将军们个个欢腾雀跃,方天蚕也大觉受用,满意点了点头,接受他的说词,却不怎么相信他,眯起双眼说道:“纵然本将不会伤害你,但你们身份不明,行踪诡异,不得不防,那就委屈你们了。”话落,手掌一扬大喝:“把他们带回营寨,查明身份再作决处。”
“是!”一声应喝,数名兵士提绳,瞬间便把阿真和兔姑绑结实了。
雅砻江下游黑拉咭盆地驻扎着七万兵营,被绑的如只蚕蛹的阿真自入大理营寨,他眺眼四观这个井井有条的军寨,远方的山峰上设有三卡,前面又有阻隘,寨营设于两道天险后面的平坦之地,位置极佳,让人看了就舒服不已,没想到那个像福娃的将军看上去呆头呆脑,却挺有战略眼光。
方天蝉老早就在寨门迎接了,见到大哥回来了,兴奋不已迎上前拉住亲哥的马绳,询问:“怎么样,这一战得到什么?”
“就些只会吃的俘虏。”方天蚕啐了一口,翻落马匹手指后方垂头丧气的蕃兵,扬手大喝:“把那两个夏周人带来。”
听大哥哟吼夏周人,方天蝉脑袋浮出大排问号,疑惑目光朝入寨队伍后方眺看,果见两个穿着夏周服饰的男女,倒竖起眉头询问:“哥,你从哪里抓来的?”
“啪!”方天蚕当即赏了亲弟一大爆粟,板起福娃圆脸叱骂:“和你说战场没有父兄弟妹,叫我将军。”
阿真被押上来就见到姓方的将军教训一个长的跟他雷同的少年,此少年也是穿着将铠,不过此将铠颜色更浅,职位充其量就是个参将,呵呵上前说道:“能不能先解开绳索,绑着挺难受的。”
教训完亲弟,方天蚕冷冷打量了阿真与兔姑一番,怀里掏出从兔姑身上搜出的大堆毒瓶子,交给亲弟吩咐道:“这些瓶内装的不知是什么,拿去给军医验一验。”
王可姑目光寒冷,面无表情冷瞪大理将军,声也不吭,就这么凶狠狠瞪着。
方天蚕是沙场征将,半点都不惧怕兔姑杀人目光,转眸阿真说道:“你们身上揣着巨大项款,身份极其的可疑,本将可以先松开你们的绳索,但是本将得警告你们,好好呆于囚帐内,若随便出来走动,那杀了你们也就不算违犯戒令了。”
这只福娃还算可以,阿真点了点头,“就依将军。”
“松绑,带入囚帐严格把守。”方天蚕挥掌施令,转身入了寨内。
阿真与姑兔被兵士押到一间囚帐内,帐内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架烛台,入帐内,冷酷的兵士便松了他们的束缚,阿真扭了扭被绑出痕的手腕,听到兔姑重哼阴森道:“说什么来雅砻江安全,现在怎么离开?”
阿真不似兔姑这般的急骤,反而安心之极,找了处帐角落坐,睇看冷站于中央的兔姑,叹气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吐蕃和大理会在这里打仗。”
“不知道?”兔姑磨了磨恨牙,走到他跟前凶狠说道:“你身为宰相,手掌天下兵马,会不知道边境之事?”
“真的。”阿真举天发誓,到现在他依然搞不懂,怎么吐蕃和大理会在雅砻江打起来,开口道:“雅砻江、大渡河、折曲等地早几月前就被大理所占,为什么吐蕃兵马突然在雅砻江,这个真的就不知晓了。”
寒脸的姑兔死瞪他的双目,不见有假,柳眉拧成一团,似乎哪里不对,可却一时没想起来,阴森森确定:“真的?”
“千真万确。”阿真顿时垂头丧气的垮下脑袋,怎么也想不通吐蕃会突然在雅砻江,若说吐蕃趁悯儿攻打夏周出兵收复故土,那也不可能这么迅速就来到雅砻江,吐蕃他有这个能耐吗?若有这个耐能,怎么大理兵马会在吐蕃境内?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吐蕃那个活佛达赖会法术,施法让悯儿无条件奉还了这些战略要地?
“呃?”想不通的阿真戏想到悯儿把全境送给吐蕃,整个人一怔,想了数想,脑中几道灵光掠过,换位思考着若他坐于悯莉的位置,自已会如何做?
还真是啊?凝神细细思索了番,阿真张大嘴巴,想诸葛亮这么有能耐,要北伐之时,南王孟获不安份地拖后腿,他大爷都不得不先停下北伐大军,征服了南蛮,这才能集结力量去北伐。吐蕃就像孟获,不先安抚下,南征在最关健时刻倾巢来攻,那可就危险了。
兔姑不知他在想什么,目光疑惑看着这张苦思的脸庞,急急询问:“是不是有什么逃出去的办法?”
思索被扰乱,阿真抬眼摇头:“现在没有办法,不过大理军不会乱杀无辜,多等几日吧。”
兔姑自已也没办法,气结走到帐蓬另一个角落席地而坐,闭上双眼不再吭声。
坐在地上,阿真菀尔一笑,解开脖颈上的项链,项链虽是铁打的,不值半个钱,可吊坠何只值万金,心情快活转动扭结,组合那块至高无上的王印,心头那只快乐小小鸟已在天上自由自在飞翔了。
卡嚓一声轻响,阿真脸上的笑容扩大,看了看气呼呼闭着双眼的兔姑,阴恻恻裂开嘴巴,站起身走到帐口对守门的兵士唤道:“我要见你们将军。”
驻守于口的兵士看也不看阿真,冷漠回答:“将军没空。”
“我有急事。”
“有急事也没空。”
“你……”面对这个蛮兵,阿真气结,扬起笑脸换个说法道:“我想写封信给家里人,你为我取来笔墨如何?”
“没有笔……”蛮兵冷漠双眼突然见着一叠银票,目光刹时灼热起来,直直转不开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