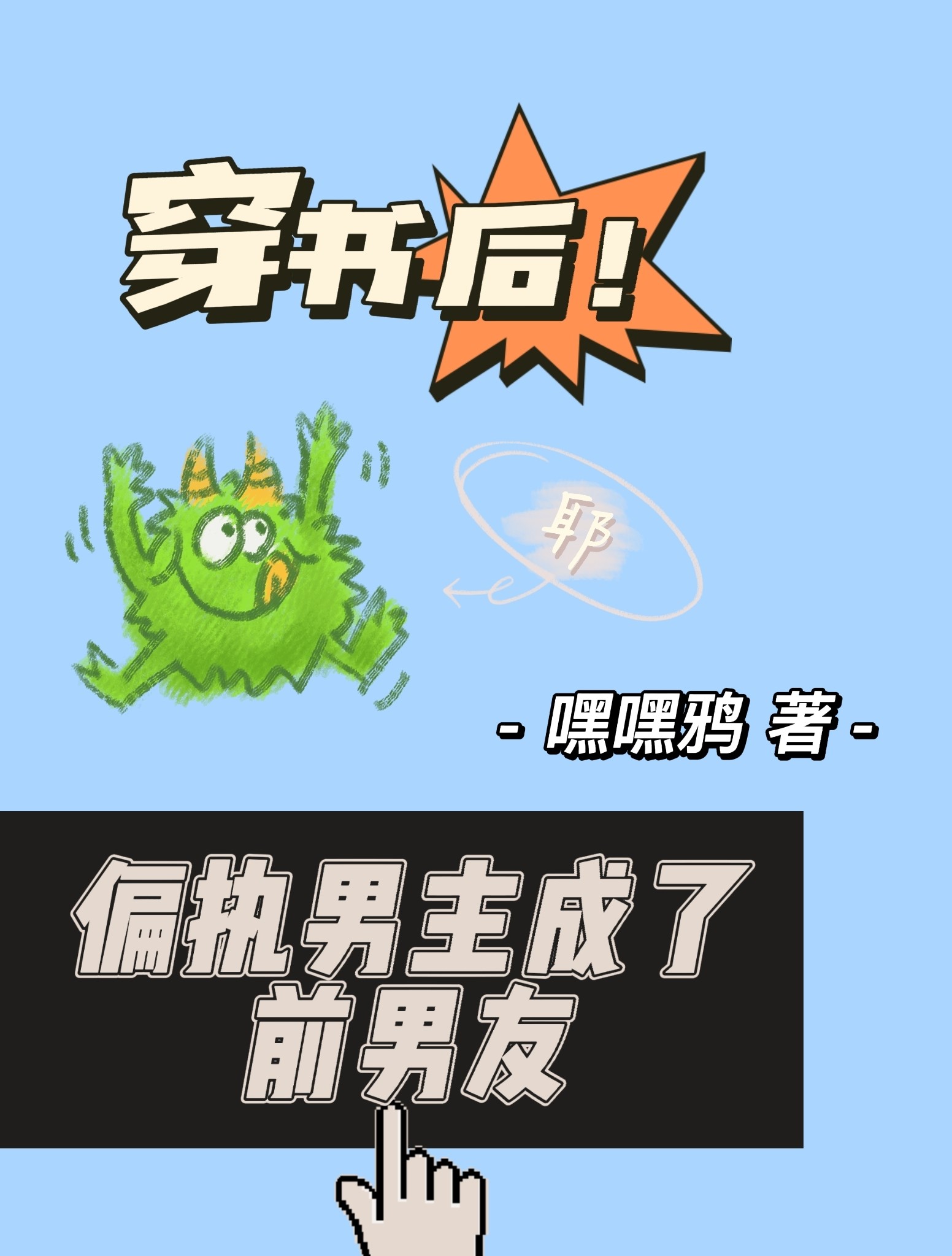夜宵凉凉,无星无月黑暗天宇在丑中终于挤出点点沥雨,从天上不停掉落的雨很快就在平头马房屋上汇聚成涓,顺着漏瓦滴答滴答,滴答的让人心烦意乱、心神难宁。
心浮气躁的阿真早就坐不住了,频频把脑袋探出房门,老不见蒙古大夫回来,眼见夜已深到底了,再想到蓝倪儿还等他,顿时更加着急了。
殷银见他如热锅蚂蚁般,心头暖暖,小脸儿羞羞,正要唤他时,突闻外面响起急骤步声,随后那个奇怪的大夫便跨了进来了。
阿真早就等急了,见蒙古大夫来了,蓦地就从椅上崩起,急急拉过他的手腕催问:“怎么样?怎么样?”
“郡王防心。”巴格微微一笑,扭头向登特都三人吩咐搁下东西,指着殷银对阿真说道:“筷筷让固娘把瘦浸泡到药水哩。”
阿真急迫之极,马上奔到床榻,轻柔扶起殷银走到茶桌上溢药味的脸盆前,先伸手试了试水温,在感觉并不烫时,哄道:“来把手给我,乖啦!”
在众人面前被他宠,殷银脸儿绯红一片,不敢出声伸起很痛的双手,咬唇搁于他手中,心里很是惧怕。
轻揉握住她的手腕,阿真小心地向蒙古大夫询问:“这药汤都有什么成份?”
“是生荠根,捣出地汁,掺水熬成。”巴格理所当然说道,催促道:“防脓又效。”
阿真瞥了一眼登特都,见他轻点头颅,顿时安心了,对殷银说道:“乖,泡一泡好防脓,不用害怕,就当洗手。”
“好,好!”殷银胸口大力起伏,喉咙不停吞着沫液。
阿真深深吸了一口气,铁灰脸上双嘴唇抿成一条线,手掌用力,死握住她双腕,就把她美白小手强按进温热药汤内。
“啊……”突然钻心巨疼让殷银惨叫出声,眼泪如江河决堤,死命挣扎。
巴格早就吩咐过登特都,只见登特都速度飞快,在殷小姐要挣脱时,双臂立马便强握住她双臂,死死让她把手定在药水里。
“啊啊啊……”崩天裂地的疼痛,痛的心似活让人给剜了,痛的世界都断裂了,殷银脸蛋布满冷汗,白唇不停颤抖,眼泪刷刷滚掉,扬声惨叫。
巴格双目死死盯着药水内那双手掌,见到手指在微微挣扎了,兴奋嘶吼:“动瘦指,筷扭动瘦指。”
“啊……”殷银使劲浑身力气动指,心脏痛的已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惨叫想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不是她的了。
巴格眼见药水的十指越动越大,大量血水渗杂,直至最后水中手掌紧握成一团,大喜唤道:“好了,好了,刻以了。”
呼!阿真额头的冷汗不比殷银少,听到这句可以了,急拿出浸泡的双手。
“银儿……”水中手掌刚拿出来,身边的人儿身子一柔,阿真惊呼搂抱住昏过去的殷银,心头一抽,拦腰抱她往床榻上安放,小声急唤:“大夫,快……”
巴格飞速欺身于床榻边,切脉探息忙碌一番,安心说道:“郡王仿心,固娘只是睡果去了。”
“好好好。”心安地移了移身躯,静看给殷银洒药粉抱扎十指的蒙古大夫一会儿,双眼瞟瞄于床上人儿白析如鬼的粉白青颜,一股抽心让他难受的紧。
寂静里,他暗暗叹气,好好个人儿竟然被折磨成如此模样,如果躺在这里的是婷儿,他不把蓝倪儿砍成数段才怪。
安静之时,客栈老板小心亦亦捧着个碗,与小斯惶恐不安地站在门口轻唤:“郡王,药来了。”
“进来。”从恍惚里回神,阿真赶紧招进怯惧老板,小心亦亦接过他手中的汤药,轻轻捺坐于床沿边,扭看蒙古大夫,再看床上的殷银,不知该怎么下手了。
巴格包扎完,安静站于旁边等候,瞧郡王不知该如何喂药,开声轻道:“郡王扶起固娘,才好喂。”
“哦哦。”没喂过别人药,电视上也都是这么上演的,忙把药碗递给蒙古,小心非常轻轻抱起殷银,让她仰躺于自已身上,准备就绪后,迟疑询问:“大夫,这药是什么?”
巴格从未见过如此小心谨慎的人,浸药询是什么掺配,引药又询是如何煎成。轻睇靠于郡王身上的姑娘,心想这个姑娘对郡王应该极为重要,弯躬禀道:“肉苁蓉煎熬而成,专治破伤风。”
阿真根本就不懂草药,自觉里就是想要问一问,轻点了点头,一手抱着昏迷的殷银,一手拾起汤匙,小勺小勺艰难喂养,想不明白自个儿干嘛要这么亲力亲为,也许是愧欠吧。毕竟她是因要救他才受伤,虽然殷大小姐是鸡婆了点,却也是为他受尽折磨,他当然会觉的愧疚了。
长夜漫漫,满头大汗喂完一碗汤药,阿真已是气喘兮兮了。搁下汤匙后,把依靠于身上的殷银抱躺回枕上,扭头要对蒙古大夫询问时,发现不知何时房中已没人了。
拉了拉被单,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徐凝殷大小姐无血绝颜,思索了片刻才迟缓抬起手掌,轻轻把她的一缕秀发抚挂到晶玉耳后,很轻很轻柔触了触她绝美白颜,叹声道:“一个女孩子家家,整日尽板着冷冷冰冰脸儿,小心嫁不出去了。”
厢房寂静,烛火幽幽,好好一段沉默过去,坐于床沿上的男人才窸窣站起身,回眸一瞥,黯然负手拉开厢房,夜雨下的更大了。
麻骨和福绒早来了,这趟临潢没找到指定的人,却救回骨折的莫琼,返回时,已有人告知郡王已把殷姑娘接到客栈了,急急赶来时,在门外见了登特都他们守着,询问三两句过后,也不敢往房内探看,大堆人就杵在门口等着。
福绒、冷无敌、罗隳把受伤的四师弟莫琼安于房中,三人急来时也不见姑爷出来,大段的焦滤过去,看见厢门打开了,一群人急围上前急问:“姑爷,大小姐伤势如何?”
“上了伤没有大碍了。”阿真安抚这群个铁血楼的把子,轻拍了拍总管老爷爷的肩,才转身对蒙古大夫按胸躬谢:“多谢大夫了。”
“不用,不用。”巴格吓了一大跳,赶紧回礼说道:“郡王,耶很深了,效人就限行回去,明里再来谈望。”
“麻骨,快送大夫。”阿真礼数周到,笑吟吟对这个蒙古大夫酬谢:“今日夜已深,明日我备厚礼,亲自登门相谢。”
“多谢郡王,效人告退。”巴格次再躬谢,转身便往走廊远方跨步了去。
今天事还真多,着实累人的很。阿真疲倦之极地转过身,看了看总管老爷爷一群人,微笑说道:“我已把客栈的西厢院包下了来,大家随便吃随便喝不碍事,明天我再来看大家。”
福绒等人早就知道他在金辽的身份,深明他是要回郡王府了,各自脸色都不同地点头,礼貌相谢:“多谢姑爷,您慢走。”
“嗯。”再看这一群老人,阿真负手转过身,领着巴特都三人,没有语言往浙沥沥大雨内飞跨了而去,出了客栈往马车内一钻,咕噜车辄转动逐雨,飞快往黑暗寂寥街道狂驰离去。
黑夜都快接近尾端,辗转反侧、翻来覆去,蓝倪儿也难于成眠,酝酿睡意暗骂林阿真还没回来时,听闻外面珠帘轻铃,翻坐起身见他终于回来了。
“怎么去那么久?”蓝倪儿皱眉道,挪动下床,“我还以为你为殷银不回来呢。”
“她都被你折磨的在鬼门关徘徊了,又不能伺候我,不回来要干什么?”一边解外服,一边漫不经心责怪,着亵衣走到灯台,剪下一段蕊端,打着浓重哈切说道:“你这女人,也太狠了,竟然用这种刑。”
被他责怪,蓝倪儿不怒反笑,解开黄亵露出里面的绿兜儿,娇嗔道:“今晚咱们便成真夫妻吧。”
“太累了,没那精力。”走到床榻边,长臂一伸,自然把她拥入怀中,一起倒回床上,共枕于枕头,浅亲她洁白霞额,疲倦说道:“天都快亮了,睡觉吧。”
可这头母狼不能碰,碰了他恐怕很难走出上京,很难走出自已的心房了。搂了搂怀里雪躯,无声闭上双眼,仿佛已累睡过去般,浅浅呼吸了起来。黑夜延伸,滴答急雨纷纷扰扰,着实恼人的很。
次日初晨,沥雨渐小,却仍纷纷飘着,万物被这场入冬的雨水打的更是破败凋零,可雨中雪梅却含起了旺盛苞蕾。湿漉漉的雨,纷纷飘飘,五花十色油伞摭不住从无孔不入的细雨,湿了旅人们的衣裳绒帽,帘进了各铺子、摊台,世界一片湿重,万物皆萧瑟。
一夜奔波过去,累极的阿真舒服地枕于绒枕上,身上的鹅绒被褥温暖,房中一架碳炉在寂静里不时的劈吧爆出细声火花。
“嗯。”在一声火花轻爆声后,阿真轻轻嗯了一声,徐缓地睁开混沌双眼,愣看榻上雕塑饰物,眨了眨双眼,不知道自已身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