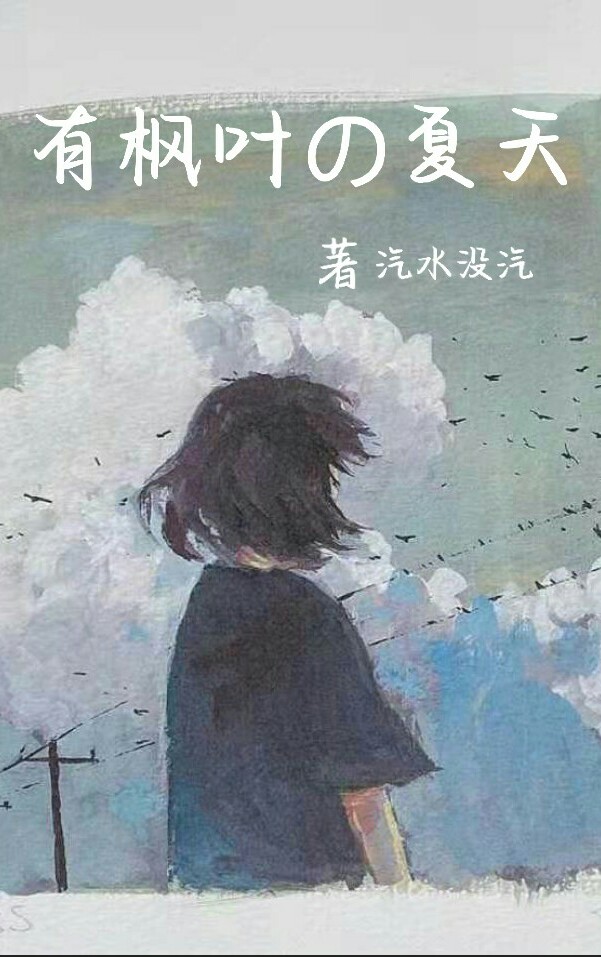祝亦安掀了掀眼皮,发现元初瑶正在看他,清眸中尽是认真听讲的乖巧。
与他对上眼,元初瑶就见他眉眼微弯,一派温和好说话的模样。
若不是见过他冷面无私的模样,她真会以为他是个不理世事的良善之辈。
“我在浓云酒肆见过廉郡王。”元初瑶将自己当时的作为也一并说了,说完还瞥了元景琛一眼。
这一眼意味深长,分明就是彰显她的坦荡,暗嘲他的隐瞒。
元景琛摸了摸鼻子,好笑的垂下视线:“日后有事也会告知与你。”心眼忒小。
元初瑶移开视线,不理会他的服软,支棱着手,托着下巴,开始秋后算账:“该说的差不多也说完了,你的伤势怎么来的,先说了罢。”
原来她是在这里等着,刚刚分明就是故意要他说出保证,才好让无法拒绝下一步的询问。
元景琛不自在的挪动一下,见她非常坚持,才道:“动手的人是廉郡王的手下。”
元初瑶眸色有一瞬的黑沉闪过,“他想接走林萧,你没同意,打起来他的手下还伤了你?”
“可有抓起来?”她不忘问对方的结果。
按理来说,廉郡王的手下伤人,身为主人,也是要负责任。
她终于明白元景琛之前提及廉郡王时为何会那么不爽快。
“抓不了,宣平候府要追究林萧的责任,廉郡王抢人没抢过,转身就进宫向圣上诉苦。”祝亦安替元景琛回答了这个问题,“周亲王已经病死,继承他爵位的长子,在一次水中救人惹来风寒,没能熬过去,作为周亲王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圣上对廉郡王较为宽容。”
周亲王死后,爵位传给长子,本来长子过世,爵位应该会留给儿子或者弟弟。
可圣上不想多一个亲王占去过多福利,一拖再拖,终于拖到廉郡王犯错,册封就改为廉郡王。
虽说有名号,可郡王与亲王天差地别。
如今多出一个私生女林萧,她无论做了什么,可以得到的宽容远超想象,尤其是这件事中并没有死人。
元初瑶突然想起,上一世她可从未见过林萧此人,若是江一玄的死与林萧相关,说明江一玄死后,有人查明真相,了结了林萧的性命,导致贵女圈子中,从未见过林萧此人。
看来改变的不止江一玄,还有林萧的性命。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在皇都中刺杀到底不是小事。”祝亦安看出她的思量,直接给出答案。
元初瑶沉默半晌,追问:“廉郡王呢?他伤了我兄长,可有什么责罚?”
明目张胆的要劫走犯人,还打伤朝中要职,若是没有惩罚,她就想法子坑他一回解气。
“惩罚是肯定有的,但父皇向来心软,对后辈的小打小闹更是包容。”祝亦安了解父皇的心态,与到了年纪就多疑爱猜忌的帝皇不同,他年轻时就爱猜忌,但年老反而慈和许多,对已故之人的后辈,多有包容。
导致混不吝的越发混不吝,藐视规矩,今日胆敢劫狱,明日指不定就干出颠覆王朝的事情。
可父皇的心思很简单,他对他常说的就是,他的朝代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就需要他们来头疼。
小打小闹?元初瑶可不觉得劫狱算是小事,她甚至有理由怀疑,当时廉郡王是故意让人打伤兄长,不过圣上对小辈较为包容这一点,倒是令人意外。
思来想去,她觉得,自己应该也算是个‘小辈’吧?
她没再抱怨为何惩罚那么轻,开始关心元景琛的伤势:“不能看,总可以和我说说你伤势如何吧!”
元景琛听着她凉飕飕的语气,头皮一紧,也不再隐瞒:“伤在小腹,不是刺伤,不过划出的伤口较长,未结痂之前,不方便行动。”
元初瑶一顿,啧一声:“如此说来,你不止是休假一天喽?”
元景琛将求救的目光瞥向祝亦安,希望他能说点什么,缓解一下氛围。
他休假一天的消息就是给祖母和妹妹听听,实际上他打算窝在房里不出门,免得她们察觉他过于空闲不对头,到时候一个个前来关心,不仅劳烦年迈的祖母,再就是,到底不是小时候,有点难为情。
祝亦安干咳一声,“见你没什么事,本王便先走了。”
人家的家事他才不掺和,元景琛分明是在炫耀,不过是小伤便有妹妹哭唧唧的关心,嘘寒问暖,好不温馨。
每次来将军府都会看见这兄妹俩温馨日常,祝亦安内心略感辛酸,你有我没有,到底意难平。
元景琛有伤不好送客,元初瑶自觉担起责任,跟在祝亦安身后,打算送他一送。
走出书房,元初瑶想着,他应该会停下,让她回去。
事实与想法有落差,他们从檐廊下走到外院的抄手游廊,也不见他说不用远送。
她稀里糊涂的送到中门,他停下脚步,偏过身看到她,颇为意外的问:“元小姐也要出门?”
元初瑶:“……”
她有一瞬的凝噎,不过到底经历不少大风大浪,稳住张口欲骂的心态,恭恭敬敬道:“兄长伤势未愈,我代他松松殿下。”
祝亦安目光缓缓落在元初瑶的面上,不过一瞥就收回,“无需同我客套,你兄长与我自小熟识,没那么多讲究。”
一离开书房,两人好似都换了个人。
女子恭敬有礼,落落大方。
男子一改温和,疏离中带着清寒的冷淡。
不过他说出来的话倒不那么讲究,贵为圣上之子,需拿捏人心,礼数可将他与部下区分开来,现在却同她说不必讲究繁文缛节,怎竟跟自家人说话一般。
似是看出她的疑惑,他眼尾微不可查的弯了弯,“无论是你兄长,还是你表哥,与我都算是自小认识的好友,在我眼里,你同我自家妹妹那般,何须过于讲究。”
听起来挺有道理,但总觉得有点儿不对。
元初瑶将自己归于学识浅显,对人情往来还是不够了解,可人家如此决定,她也不好置喙,便点头应下:“也好。”实则心中自有一番打算,无人在也就算了,有人的情况下,还是要知趣一些,该遵守的遵守。
有人喜欢独一份的特殊对待,她不行,上辈子祝亦荇一开始确实对她很是体贴,可后来证明,他看上的就是父亲手中的权势,用完就丢,殊不知眼前之人是否也有同样的目标。
一时之间,她心中对祝亦安的愧疚,稍稍减少一些。
皇权之下,好友又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