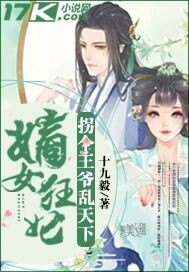“瑾儿,你是不是,打算走了?”
趁着空档,符半笙试探问岑乐瑾的想法。
只要她开口,符半笙有十足的把握一定能护她一生平安。
虽然,不能确保南歌无恙;于他心中,岑乐瑾才是最重要的人。
“不舍得?”
“不是。”
“瑾儿,他没什么大碍,别担心。”符半笙好言劝道,毕竟他们还没有孩子,现在放手不算太晚。
“哥哥,我们,欠他真的太多了。”不知为何,岑乐瑾听到娘亲在嫁给父亲之前还有一段过往的时候,竟有些内疚。
或者是因为这缘由,武烈才会灭了岑北渊一府把。
或者也是因为这缘由,岑北渊才被迫帮着武烈举报荣王叛国吧。
虽说具体经过是如何她并不知晓,岑乐瑾潜意识觉得事情始末不会和自己所i料想的有什么出入。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不会有错的。
岑乐瑾不断在心头暗示自己不该慌乱,亦不该犹豫不决。
“瑾儿……”塌上的男人在轻声唤岑乐瑾的名字,她只得暂时撇下。
“我去去就回。”
岑乐瑾却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握住,她抬眼一看,正是符半笙。
”不要去,忘了他,我养你。“符半笙一定要替她做了决断,她是个极易心软的性子,这点倒是从了岑北渊。
娘亲覃芊可是个很刚烈的女子,没法儿得到武烈独一无二的爱情,索性连孩子都不要也要和他断的干净。
只是这一点,不论是符半笙还是沁寕,均都无法做到。
符半笙和沁寕,反是更像武烈一些。
”你瞎说什么胡话呢?“
岑乐瑾尚不知,武烈已经默许符半笙一片江山,甚至许了他一块免死金牌。
岑乐瑾更不知,只要她一离开,南歌立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全意对抗武烈的精兵,早日洗刷父母的冤屈,夺回那个本属于他的帝王之位。
”你在质疑哥哥我的腰包?“符半笙鄙视地看道,虽然没有南歌那座金银山那样夸张,但养个女儿家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是,“岑乐瑾顿了顿,”他醒了,想见我。你我是兄妹的事情并无多人知晓,被这店里的看去讹传岂不是毁了我清誉,不好。你先松开。“
”瑾儿,这说辞找的倒是不错。“符半笙狡黠说道,手却握的更紧了。
”你松开~我就去见一面,什么都不会发生的。“
岑乐瑾试着和符半笙达成一致,就一眼嘛,又不会怀孕不是吗。
”万一呢?”符半笙这个时候对南歌的警觉性很高,与其说,他是更担心武烈的人会找来。
符半笙对这个血脉意义上的父亲并无好感,南歌敢不敢东他不知道,只是岑乐瑾武烈一定不肯轻易放过。
若是知道她就是岑北渊的唯一血脉,那还不得掀翻整个江湖也要斩草除根。
爱一个人的时候,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痕一个人的时候,他的一切都是恶心的。
身上淌着一半岑氏鲜血的女子,究竟该如何躲得过各种明枪暗箭。
符半笙不知道,南歌也不知道。
“他在凤鸣渊有兵,我不会有事的。”岑乐瑾还想着是不是符半笙担心江湖和朝廷同时追杀到濮阳城。
凤鸣渊?
符半笙居然意外窥破 了为什么武烈迟迟不敢对南歌处以狠手的原因。
但现在他明白了——原来高祖帝传说中的谕旨是真的,在天朝境内某处,有一队兵力,凭一枚玉佩调遣,哪怕是皇家的虎符和皇帝老儿现身都无济于事。而这群最精锐强悍的军队,便是由岑北渊的亲信和荣王的亲信遗留下的干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岑乐瑾或许也能调度他们。
“瑾儿,我们去凤鸣渊。”符半笙兴冲冲地想早日见着那传说中的军队。
是否真的兵强马壮?
是否真的一将抵得过一师?
是否真的见玉佩尤见高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什么意思?”直到这会儿,岑乐瑾才听出符半笙话外之音。
敢情,符半笙不是担心南歌的生死,亦不是看重自己的性命。只是一味地对凤鸣渊的人感兴趣。
“你和谁有的交易?”岑乐瑾不由得提高了戒备,不能再和他说下去了,言多必失的道理她打小就清楚。
少说一定没什么,多说一定有问题。
细细思量,岑乐瑾此刻有些感谢邱一色的教辅。
“没有。”符半笙否认,一面儿不忘环顾四周。
武烈这回派来的都是高手,符半笙不知肖尧是全都对付完了,还是被对付完了。
“你骗我。”岑乐瑾试图甩开符半笙的手,不想一个不留神竟被点了穴不能行动。
“瑾儿,对不住了。”符半笙不敢直视她的眼眸,带她离开的确是权宜之计,谁叫她偏偏挑了个惹不起的人。
“你敢——”
里屋的男子许久没等来岑乐瑾,咬着牙冲破了穴道跑出房门,恰巧看见符半笙扛着她准备开溜。
“南歌!”她失声叫道,汩汩的血迹似又加深了他的衣襟。
“哥哥,你放我下来,我就说一句话。”岑乐瑾身体不能动,但嘴巴还好能吼。
可下一秒,符半笙就掐断了说话的机会。
“卑鄙。”南歌咬牙切齿地样子,岑乐瑾看在眼里疼在心中。
南歌都受伤了,符半笙居然还想着打架——还是当着自己的面儿,不是活生生要她难受吗。
我为什么摊上这么个哥哥?
他的长相和性格完全是两个极端阿!
南歌眼神一直在岑乐瑾身上,从头到脚,唯恐符半笙一个不小心摔了磕着他捧在手心的人儿。
犯我妻者,非死即残。
当南歌说出这八个字的时候,岑乐瑾起初还有质疑;
当符半笙直愣愣跌在青石板上的时候,岑乐瑾的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负伤的王爷都这么厉害了,他要是不受伤,认真打架或是打仗,那不得闭着眼睛又是一场胜利。
看来,我没嫁错人。
岑乐瑾竟然有些自豪和骄傲,身为他唯一的正室,唯一带出门的女子,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