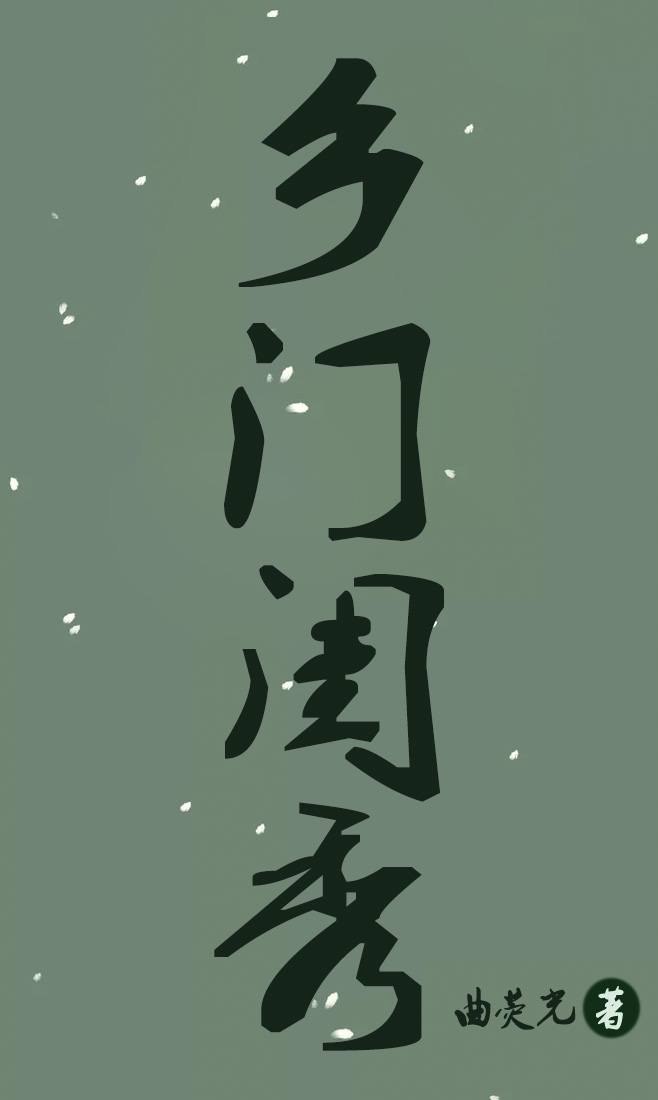渊儿的高热一直不退,时而剧烈咳嗽,本虚弱似无骨的孩子,每每咳嗽都会从床上弹起来,又重重地挺倒在床上。加之脸和四肢都有脓疱,血水样的脓液渗出,十分可怖。
姜太常说孩子能不能救活全看今晚,她便执意要留在其病榻旁,姜太常不允,她就苦苦哀求,说尽了这孩子如何命苦,若是上天非要带了去,身边到底该有个亲人陪着。
姜太常勉强让人拿了条棉布,裹在她的口鼻处,又再三命令可以坐在窗边,万不可坐在榻前。她满口答应,这才求来陪着渊儿的机会。
漫云拧了帕子搭在渊儿额头,又拿了新帕子为他擦拭溃烂后的皮肤,听到渊儿极虚弱的哀叫声,采苓转过眼去。
“连日来你唤得最多的便是你娘亲和姨娘。”采苓同渊儿婉婉道来,又仿佛是自言自语,“姑姑从没听过你提到爹爹。”
“你爹是怎样的人,你可知道?姑姑兄长三个,你爹是同我年岁最近也最亲。小时候他淘气,常常带着我翻墙出相府去京郊打兔子,从不嫌弃我跑得慢。有一次,我崴了脚,你爹就背着我一路慢慢走回去,边走边讲故事,走啊走,居然迷了路。夜黑风高,我很害怕,你爹找了间破庙,用稻草铺了床,说天亮之后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准能找到家。”
采苓陷入沉思,面上却是微微的笑。
“后来家丁们举着火把将我们找到。回去后,我被罚抄书,你爹被送往了洛阳拜师,从此我们三年一聚首,直到他长大成人。现在你爹不爱出家门,最喜欢的是躲在屋子里雕刻,连话也不同人多说。许多年过去了,我们都丢失了不畏艰险的勇气和朝着太阳走就能找到家的乐观,但是曾经的那个少年,是我生命里的明灯。姑姑爱他。”
“你爹要是在京城,看到我家渊儿生了病,他不会火急火燎像姑姑这样方寸大乱,但是他一定会坐在渊儿身边守到天明。”
“再说到你娘,她又何尝不是为了你好,以为将你留在外祖母身边以后的路会少了许多荆棘,毕竟外祖母和你姨娘都很疼爱你。你若是有事,你娘往后的日子再没了盼头,你姨娘、外祖母也会抱憾终生。”
……
一夜未合眼,天边渐渐露出鱼肚白,朝阳的霞光通过小轩窗的缝隙洒在采苓身上,她晕晕沉沉却被寒风吹得立马清醒,说了太多话,觉得喉头微痛。
“姑姑……”嘶哑又虚弱的喊声,却像是心头擂起的锣鼓震天,采苓激动得倏忽从椅子上蹦起来,连忙走近,“渊儿!姑姑在……”
丫鬟们也激动,连忙去请姜太常,孰料与太常一同入屋的是沈牧迟。
太常把脉时,采苓对沈牧迟颔首,是打心底里的感激。
渊儿算是保住了性命,余下的治疗便是维持水分、增加营养以及皮肤护理。
姜太常极力反对采苓留在此屋,又对沈牧迟道:“请殿下也速速离开。”
采苓不敢多言,又对渊儿说了几句安慰鼓励的话,谁知道渊儿断断续续道:“渊儿没事了,姑姑自己保重。”
那行热泪就瞬间凝在眼眶里,仿若眼前这个孩子正是多年前姜府里的老三,成日笑闹、爬墙、打兔子、住破庙的三哥。
……
过了十几日,渊儿已能下床跑跳,只是脸上和身上的脓疮正在结痂,瘙痒难受。采苓仔细请教姜太常,如何避免留疤,生得如此讨人喜欢的孩子,若是变了麻子可如何是好!
再过十日,即便是每日涂着药膏,也不准渊儿使劲抓挠,可还是留了些痕迹,小腿和手臂上较多,脸上只一二处,并不影响他的软糯可爱。采苓却极懊恼,总觉得自己未能做到最好。
“姑姑别伤心。我长大后又不光靠这副皮囊。”渊儿蹲在地毯上玩石子。
采苓忍住不笑,“想不到年纪轻轻,说的话还挺有道理。谁教的?”
“姨娘。”渊儿抬头道,“姨娘还说好男儿应该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良明月看男子的眼光到底比她好。从前她只认个风流倜傥、鹤立鸡群。不过,良明月不是也看上了沈牧迟吗?他哪里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了?他那是冰冷如雪好不好!
话到嘴边,却只是点头称是,“你姨娘说得很好。”
说话间,漫云端着茶进来。采苓笑着接了茶,正要喝,漫云忽得扬手将那茶碗打翻,热水将采苓的一双手烫得微红,连刚刚病愈的渊儿也冲上来,势要保护他姑姑。
采苓将他拦在一边,才看到跪在地上发抖的漫云满是疲态。多日以来,若不是她精心照顾渊儿,此时这孩子还不知是个什么状况。她姑侄二人还未曾对漫云说过一声感谢,心中不免愧疚。
“渊儿,漫云姐姐这许多日衣不解带照顾你,太累了。快给漫云姐姐道谢。”说着,就去搀扶漫云。
漫云一躲,避开了她的手。采苓以为是因为自己手湿,便使眼色让渊儿去。漫云磕头道,“奴婢失职,不该再留在姑娘身边。”
“你这说得什么话!”采苓急道,“连日以来太辛苦你了,快去歇着,过几日缓过劲来,咱们再细说。”
漫云连忙退下,跨过门槛时顿了一下,双手扶着门框,似摇摇欲坠。采苓只以为她是过于疲劳,就像是她守了渊儿一夜,回小榻时也是昏昏沉沉。刚要去扶,渊儿却道,“姑姑,我饿了。”
被渊儿这么一提点,她恍然醒悟。
院子里的这些人帮了他们姑侄二人许多,她却毫无表示,真心过意不去。可是思来想去,困在晗章院里,也不知该如何感谢。
看着渊儿大口喝着鸡汤,她忽然开了窍。
沈牧迟喜欢吃清蒸鲈鱼,要答谢他就亲自去厨房做一桌子菜吧。
姜太常说过吃饭只吃七分饱,看来对吃食没什么兴趣,将来送一支千年的人参去。
至于漫云,自是女子玲珑,送一箱绫罗珠宝笼络之。
后院内的小厨房,临时调来的婆子秋二嫂正是曾经围观过她煮糖醋鱼的,如今看她不心死,心中啧啧叹了两声,却再不敢围观,连忙将厨房整体让出。
她本想叫秋二嫂杀了鱼再走,可那婆子似逃难一般,转眼就消失无踪。
她挽起袖子去缸里捞鱼,没想到肥硕的鲈鱼溜滑,好不容易捞上来,又窜到地上,在青石板上打挺。她再去捞,鱼又窜,好不幸苦。
反复折腾几次,鱼落地数次,终晕了过去,她嘿嘿笑两声,就要开膛破肚,谁知道刀刚触到鱼鳞,鱼就醒过来,比之前翻滚得厉害数倍,她吓了一跳,惊叫一声。
好不容易将鱼按在砧板上,听到背后的脚步声,她忽道,“大婶儿!你总算回来了。”
“谁是大婶儿?”沈牧迟的气息荡在耳畔,她心扑通一跳,手不稳,那鱼就又窜到他们脚下,她连连跳起来。他却站得笔直,不为所动。
“若是要吃鱼,吩咐一声,何必自己动手。”他蹲身捡起鱼,手起刀落,那条鱼瞬间毙命,也免于挣扎。
“我想给你做顿饭。”采苓失落。
“做顿饭?”他薄唇微扬,转过眼来看她。
“为了感谢你。”采苓依旧沮丧,“没想到连最简单的杀鱼都不会。”
“谁说杀鱼简单。”沈牧迟柔声细语,“你可知晓本王爱吃何菜?”
“清蒸鲈鱼、碧玉豆腐、西湖藕片、三彩羹、四喜鸭子、桂花酥……”她一口气说了数个。
“嗯。不错。”他面上带笑,挽起袖子,开始清理鱼肚子里的内脏。
见他用刀在鱼身上划口子,她连忙阻止,“清蒸鲈鱼应是把鱼剖成两半,不用划口子,糖醋鱼才划口子。”
“懂得倒不少。”沈牧迟抓起那鱼凑到她跟前,“那你说说这条是什么鱼?”
“鲈鱼呀。”她要做清蒸鲈鱼,当然得用鲈鱼啊,真是多此一问。
“出去可别告诉别人你管着京城最大的酒楼。”他复将鱼扔在砧板上, 头也不抬,“这是鲤鱼。”
她有些不好意思,却立马笑道,“一时情急,抓错了鱼。”
“还愣着做什么?”沈牧迟忽然用头点了一下灶台。
采苓尴尬一笑,“对不住,我不会生火。”
“你!”沈牧迟恨不得拿手上的鱼砸她,口口声声说要做一桌子菜来答谢他,如今认鱼不会,杀鱼不会,炒菜自然不会,连生火也不会!
“殿下,看来此次是我有心无力,就此作罢吧。”采苓陪着笑脸,往后自然有能够报答他的时候。
熟知他竟自己拿着打火石和干草去灶台后蹲下,像模像样生起火来。采苓几乎是崇拜地看着他,“殿下锦衣玉食中长大,怎会生火做饭?”
“你以为谁都如你一般蠢!”他责道,见她有一丝沮丧,“三年前并州之战,敌军兵临城下我军穷途末路时,本王连树皮也吃过。”
他是想告诉她自己并非一帆风顺,日子也是有起有落,可是瞬间她的情绪却更加低落,“记得并州之战大捷后,殿下凯旋归来,车马已经入了城,陛下亲自出宫为殿下接风,谁曾想殿下坐在马上却被刺客的冷箭所伤。我眼睁睁看着殿下摔下马去,当时只当殿下妄自尊大,于战场上骁勇却差点丧命于歹人。如今才知,殿下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时候是真的没有力气可以防得了暗箭。”
他怔了片刻,往炉子里扔了一把柴火。
她接着问,“后来追拿到刺客没有?知他受何人指使吗?”
他起身,“刺客被擒后自尽,线索断了不可查。”并不想告诉她实情:他沈牧迟是姜相的眼中钉、肉中刺,刺客们背后的指使者从来就是姜相!
她叹了一口气。
沈牧迟淡淡一笑,握着锅铲,好像握着一把剑,威风凌凌地看着她,采苓转而露出笑容。沈牧迟往锅里倒油,“今日就做你爱吃的糖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