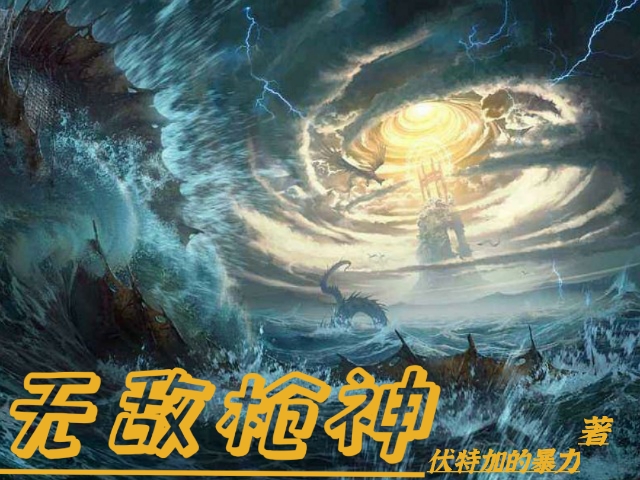布轮退尔(一八四九~一九〇六年),以提出“意志”说著名的法国戏剧理论家,早年未考入大学,当过兵,做过私人教师,担任过编辑,发表的评论文章汇集出版后被破格聘为师范大学教授,一八九三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布轮退尔在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影响下开始演讲法国戏剧史,一八九四年写成的《戏剧的规律》集中地阐述了他的以“意志”说为中心的戏剧理论。在二十世纪初布轮退尔还出版过《法国古典文学史》,更系统地阐述了生物进化论的文学史观。这位理论家晚年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把宣传“意志冲突”说和宣传教义兼了起来。
《戏剧的规律》是布轮退尔为《法国戏剧与音乐年鉴》写的一篇序文,本意就想把自己多年来探索的戏剧规律总结一下,因此,他在文前文后一再说明所谓“戏剧规律”这一命题的含义,以及它与以往许多戏剧法则的区别。他说,“所有这些被肯定了的法则,只能体现或者表达戏剧最肤浅的特征。这些法则非但并不神秘,而且一点也不深奥。无论我们遵守与否,有它或者没有它,戏剧仍然是戏剧。这些法则仅仅是一些手法,它们随时都可以让位于另外一些法则。这完全取决于主题、作者和大众。”所以他把这类法则称之为“一些必然可以变化的套子”。与法则的狭隘、顽固、僵硬不同,规律虽然也具有稳固的必然性,“但是在应用方面它却是广泛的、可以变通的,同时又十分单纯、十分普遍,在应用上还十分广阔,并且,它永远准备以任何意见、经验,或者历史来丰富它。无论是什么样的贡献,以肯定来解释它也可以,以否定来让它吸收也可以,而它却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规律”。布轮退尔回想到前几年在一个剧院作戏剧史演讲,戏剧现象涌现在眼前,有拥塞不堪之感,但是由博返约,他慢慢觉得脑子中的戏剧观念简单了,明确了,同时也更广阔了,这就是规律的获得。
这个规律乃是:戏剧是一个自觉的意志的行动。
自觉的意志行动会遇到阻力,因而必须攻击这些阻力,进行反抗、斗争和冲突。于是布轮退尔指出:“一般所谓的剧院,不过就是发挥人的意志,对命运、财产、环境等方面阻碍它的东西进行攻击的地方”;“戏剧是表现那些与限制和贬低我们的自然力量或神秘力量发生冲突的人的意志的;是我们中间的某一个被放到舞台上去生活,并且在那里进行斗争,以反抗命运,反抗社会法律,反抗他的某一个同类,反抗他自己——如果需要的话,反抗野心、盘算、偏见、愚蠢,反抗他周围的人的恶意”。
这样一来,所谓“意志”说,也就成了“冲突”说——“意志冲突”说。
布轮退尔分几个层次来说明自己的学说:
(一)戏剧与史诗、小说的区别就在于有无自觉的意志的行动。为此他剖视了两个作品: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和博马舍的戏剧《费加罗的婚姻》。这部戏剧正恰是以这部小说为范本的,所以对比起来焦点集中,较能说明问题。布轮退尔认为,差不多的人物,在戏剧中“他总是继续不断地要求他所要求的东西。他没有停止过策划达到这个要求的手段,并且在这些手段失败之后,他又没有停止过新的手段。这就是可以称为‘意志’的东西:竖立一个目标,叫每一件事都向着它,努力使每一件事都跟它一致。”到了小说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没有什么计划,因为他并没有特殊的或者确定的目的。他是服从环境的,而不是支配环境。他没有‘产生行动’,而是在‘接受行动’。”布轮退尔所谓的“接受行动”,是指史诗、小说只描绘一幅从身外作用到主人公身上的力量的组合图。史诗、小说中当然也有各种行动,但不是“自觉的意志的行动”,因而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行动”。“自觉的意志的行动”的标志,是要求“主人公确实是他们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也有一些小说具备这一标志,这说明这些小说具备了戏剧性,可以比较顺利地经过改编搬到舞台上去。但这种小说不能代表小说的总体特征,而一般的小说在布轮退尔看来是不能也不应搬到舞台上去的。
(二)戏剧类型的划分界限,在于自觉意志所遇到的障碍的性质。如果说,以意志的有无来区分戏剧和其他艺术样式,是表明规律在外部关系中的作用,那么,以意志的对象来划分戏剧种类则表明规律还起作用于内部关系。他的划分简单说来就是:自觉意志所遇到的障碍如果是不能克服的,即构成悲剧;自觉意志所遇到的障碍如果是有可能克服的,即构成正剧;障碍更小一点,与意志势均力敌,而且障碍也表现为意志,出现了两种意志的等力对峙,即构成喜剧;要是自觉意志在对立面中找不到也发自自觉意志的障碍,障碍只在偏见、滑稽、手段与目的的不相称等更为琐屑畸形的因素,那就构成闹剧。布轮退尔所说的障碍,是包括醇己的激情在内的,因此所谓克服,也就包括克服自己的激情力量在内。悲剧的外部障碍固然或命运,或上帝,或规律,无法克服,而内在热情也激动狂暴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而构成无法克服的障碍;正剧的外部障碍已从命运、上帝等先天之力下降为同类人的行为如偏见、社会习惯等,而内在热情也有了克服的可能。
(三)戏剧价值的高低电竟志的质量来衡量和决定。就剧种而论悲剧的价值之所以比较高,是因为其间包含的意志,大到足以克服对死的畏惧;其他品位也就依次类推。就具体作品而论,“一个剧本优于另一个剧本,决定于意志所发挥的力量的分量,看哪个大些,哪个小些,决定于哪个剧本的偶然性部分少些,必然性部分多些。”这是与布轮退尔对意志的整体看法分不开的。他认为,意志给人以力量,、支配人的行动,因而也支配着历史,世上没有比意志的扩张更伟大的事情了。既然他把意志看成是人的行动和历史的主宰,那么,以人为主体,以行动为血肉,以历史为反映对象的戏剧,自然也要相应地随着意志的升降而沉浮了。
(四)戏剧史的兴衰也决定于民族意志的张翕。布轮退尔断言,戏剧通史证明了一条规律:一个伟大民族的意志十分昂扬的当口,也往往是戏剧艺术发展的高峰所在。他举例说,希腊悲剧的繁荣和波斯战争同时,西班牙出现塞万提斯和维迦的时代正是它把意志力量扩张到欧洲和新世界的时期,古典主义戏剧繁荣之时正恰是法国完成了伟大的统一之后。他又回到小说《吉尔·布拉斯》和戏剧《费加罗的婚姻》这一个对比上,指出这两部作品虽属同一族系,却不属于同一时期,前者属于摄政时代的意志松弛时期,而后者两属于革命前夕由意志力操纵着的强有力的恢复时期。从这样的思想出发,布轮退尔重复了黑格尔在《美学》中讲过的一句不符合事实的话,而又比黑格尔说得更武断、更不留余地:“东方人没有戏剧,他们只有小说。这是因为他们是宿命论者,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说,他们是定数论者。”布轮退尔还进一步把这一点上升到规律:“对定数论的信仰更有利于小说的发展,但是对自由意志的信仰则更有利于戏剧艺术的发展。”不仅如此,他还列举了历史上以意志和行动闻名全球的政治家如拿破仑、腓特烈等,指出他们都是喜爱戏剧的。
总之,布轮退尔为了说明戏剧与意志的密切关系,几乎占领了全部论述途径。因此,他论述得十分浓烈,成了以“意志”概括戏剧本质特征的理论代表。显然他是受了黑格尔以至一些唯意志主义者的影响的,但黑格尔等人为意志张目是就整个美学、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整个社会而言的,未曾像布轮退尔这样专注集中地把戏剧与意志单独地绑扎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也显示了布轮退尔与唯意志论者的区别:唯意志论者把意志说成是上天落地的宇宙精灵,布轮退尔也有过类似的说法,最终却还把意志的专利权交给了戏剧(连小说也不能分享),这在唯意志主义者看来,无异是束缚住了意志这位无敌天使的手脚。
观点固然是鲜明极了,但弊端也就包含在这种“鲜明”里。是不是一支意志升降表就能囊括全部戏剧史了呢?当然不可能。布轮退尔对东方无戏剧的乏识之见姑且不论,就从他所举的那些欧洲戏剧例证看,也常有削足就履、牵强附会之虞。至于他不得不避开的“例外”就更是大量的了。一切凡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观点,既讲出了一些道理又不免片面武断的立论,总是会引来对立面的。那就让我们紧接着看看“意志”说的主要反对者亚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