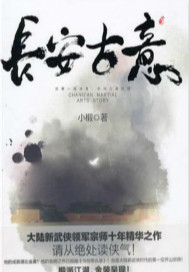中国戏剧与希腊戏剧、印度戏剧相比成熟得比较慢。由此,不少研究者想从希腊和印度的戏剧中寻找中国戏剧的渊源:
中国戏剧的理想完全是希腊的,它的面具、歌曲、音乐、科白、场次、动作,都是希腊的……中国戏剧的思想是外国的,只有情节和语言是中国的。
(戴·鲍尔:《中国种种》)
传奇的渊源,当反“古于(元)杂剧”……而传奇的体例与组织,却完全由印度输入的……就传奇或戏文的体裁或组织而细观之,其与印度戏曲逼肖之处,实足令我们惊异不置,不由得我们不相信他们是由印度输入的。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十章)
印度的戏曲及其演剧的技术之由他们(商贾们——引者注)输入中国,是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地方。
(同上)
其实是大可置疑的。判断两个人是否是亲缘嗣衍关系,不能依据他们外貌的接近或往还的踪迹,而应寻访各自的家谱世系。在文化领域中,非经“输入”的也可彼此相像,因为人类在有规律可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于类似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经验和需要,创造过无数不谋而合的“逼肖”奇迹;反之,确属“输入”的也可以有许多不像,因为新的环境总会给各种输入物带来变异。多年来,经过不少文化史家的努力,中国戏剧由萌发到成熟的家谱世系已大体理清,这便是否定“输入说”的最有力的证据。中国戏剧的始祖,不在地中海岸,不在印度河流域,而是在中国自己的大地上。
中国戏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外来影响。中国现代印度文学研究家许地山是倾向于“输入说”的,但他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很谨慎地采用了“点点滴滴”的提法,这倒是较易被人们接受的。无疑,“点点滴滴”只能溶入而不能改变中国戏剧自身的河道。
中国戏剧的起源可迳直追溯到先秦。如果说,原始歌舞只能看做一般文学艺术的共同始源之一,那么,在公元前几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可找到戏剧的正式起源。此后,缓缓地流,渐渐地变,终于正式形成于十二世纪,成熟并繁荣于十三世纪。换言之,中国戏剧正式起源于希腊戏剧的发展和繁荣时期,而当印度古典戏剧完全走向衰落的时候,它以成熟的姿态大张旗鼓地出现于人类的文化舞台,使东方的戏剧领域没有出现太长时间的空白和寂寞。此后,便繁弦紧鼓不绝于耳了。
中国戏剧形成和成熟得较慢,是有原因的。戏剧的最初始源可以发生于乡村,产生于民间,但是,闭塞的山陬海隅、远乡僻壤究竟无力哺育这么一门组成门类繁多的综合艺术,它需要城市经济土壤的滋养;它需要在城市里招揽广大观众,开辟演出场地,收罗多方人才,尽力扩大影响,否则不能立足生根并得到发展。但要做到这一些,它又不可能避开统治者深切的关注,因此统治者的爱憎弃取对戏剧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一门艺术从原始的或未定型的粗疏状态全面地飞跃成完整、稳定的艺术,又离不开一批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士的参与和加工。这些条件,在宋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对戏剧来说都不甚齐备。
宋代以前,城市经济虽然早已存在,但像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盛的城市工商业面貌,却是前朝所不可比拟的。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唐代长安都城的考古复原图,长安当时已是经济文化空前繁华的世界名城,这个周长三十五公里有余的大城市设有东西两个周遭六百步的很有一点气魄的商市,但与《清明上河图》中熙熙攘攘延绵不尽的宋代商市大街相比,却又明显地表现出唐代商品交换的规模小得多了。宋代空前繁忙的商品交易很自然地与游乐、庙会连在一起,一方面商市以文娱吸引和集中顾客,另一方面文娱也借商市而出售自身,于是就两相帮衬、齐头并进了。中国戏曲史家张庚曾这样阐述文娱演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与唐代的显著区别:
艺人到勾栏里来是为了“卖艺”,而观众到这里来是出钱买娱乐。这就和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大不相同了。那时的艺术是不论价的,是被皇帝、贵族、达官们所养起来供自己娱乐的;它的艺术内容、风格和趣味是由他们决定的。现在呢,它是由广大市民观众的爱好所决定的。这样子,属于市民的艺术就出现了。
(《戏曲的形成》)
确实如此。但当市民艺术广泛出现之后,广大市民观众仍然生活在封建枢纽的近旁,中国戏剧还不能在“皇土”、“官道”之外搭起一座舞台,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志趣仍然有力量控制勾栏里的鼓乐之声。长期以来,独尊儒术的权贵们也何尝不把玩和利用各种艺术,但却反对艺术领域里任何实质性的演进。厌恶新奇和鲜亮,倡导简昧和钝拙,艺术活动也不能超越这个基本的思想风格。这无异植树于瓮、缚鹏于笼,戏剧何以能大模大样、舒展顺畅地发育成长呢!原先在印度时曾与戏剧发生过密切过从关系的佛教,到了中国,也只能变成一片“苦空寂灭”,与戏剧没有什么缘分了;主张“清静无为”的道教当然更不待说。总之,戏剧固然在发展,在成熟,新的经济条件滋养它,热心的人民浇灌它,但它的枝桠伸到哪儿都碰到那张理学思想的巨大网络。没有想到,竟然是气势汹汹南下的蒙古统治者的铁蹄把这张网络暂时地踏破了。他们对伎乐的喜爱远胜于中原文明,对艺人艺事也不特别贱视。他们废止了科举,拦断了文人仕进的路途,那些知识分子在失望地长叹几声之后蹀躞街头,谋求出路,最后踱进了勾栏,本当撰写洋洋策论的笔,也就描情画态起来。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本来就“不屑仕进”的傲岸文人。于是,一片焦土培植一丛奇卉,在没有留存多少文明的大地上,戏剧繁荣的各方面条件倒已一一俱备。更何况,无论是那些刚刚走进勾栏的文人,还是那些长在勾栏的艺人,胸口早已积压了太多的郁闷,太多的愤懑,漫有最强烈、最有容量的艺术方式已无以倾吐,无从排解。种种必要性遇到了种种可能性,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终于出现在最黑暗的历史环境中。最低劣自乞野蛮和最高贵的文化,骇人听闻的血污和令人惊叹的珍宝,组合成了这个短暂的朝代——元代。
元杂剧是真正完全成熟的戏剧形式。元杂剧发展的繁荣程度,足可以与世界戏剧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戏剧黄金时代媲美。当时,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有八十余人,见于书面记载的杂剧作品达五百余种。南北各大城市,特别是开封、大都、杭州等都城集中了许多戏剧活动家,出现了许多戏剧活动场所,戏剧气氛十分浓厚。
水往低处流,戏往热闹处传。十四世纪初,由于偏安在南方的南宋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比北方快,杂剧也就逐渐南移。但是,此时的杂剧已不甚景气,科举制度的恢复夺走了许多戏剧创作人才,元统治者的插手又抽去了它不少生命的养分,再加上拔离原先生长的土壤而迁移异地,恰如树棵卉朵“水土不服”一般,竟更其萎顿起来。而南方原先就默默成长着的另一剧种南戏,却日见茁壮。
南戏早在十二世纪就在商业经济相当繁荣的浙江温州形成,并不比杂剧出现得晚,但由于流传地区的人民(“南人”)被金元统治者压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一时无法与浩浩南下的政治、军事、文化势力相匹敌。“莫向人前唱南曲,内中都是北方音”,正是时尚之风。元代南戏有些零星曲子遗留至今,也有十余传本,但都是没有说白动作的曲文、故事。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有人发现了三个南戏全本,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第一种较长,科白甚多,而第二、第三种则曲多白少,篇幅很小,只抵得上元杂剧的一本,总体来说,还比较粗疏幼稚。杂剧南移之后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杂剧和南戏这两个对手在竞争中慢慢发生了互相渗透,特别是原来作为弱者的南戏,更是努力从杂剧中吸取养分,滋补自己,并进而发展自己原有的特色,由此获得强健。这中间有一批南方文人起了很好的媒介作用,杂剧的南移给他们以不小的激励,他们一方面学习创作杂剧,一方面又写南戏戏文,并且常常不存门户之见,南腔北调,熔于一炉,南戏更日臻丰满成熟。恰巧当时元末南方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使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权威日益动摇,文化专制统治也不能不有所削弱,于是南戏终于以一种引人注目的面貌出现于元末剧坛。它吸取了杂剧的许多长处,又有不少比杂剧更为进步、更有容量的特点,使它具备了足以取代杂剧地位的内在条件。但容量大又易致拖沓,杂剧的本色和骨力就不容易在南戏中看到了。后来在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容量更大,唱腔在昆腔兴起之后更优美柔婉,文辞也相应而典丽,长期雄踞明、清剧坛。
元、明两代在演出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有记载说明代著名演员颜容由于在表演一个悲剧时发现观众无悲戚之容,便深深自责,认真地对着镜子体验、表演,直到自己孤楚感怆之情难已,再行登台,终于使得千百人哭皆失声。另一位著名演员彭天锡善于表演反面角色,即使扮演千古奸雄也会演得比人们想像中的形象更阴险狠刁。明代著名文学家张岱说他有“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陶庵梦忆》),这倒是很有点像日本世阿弥所说的演员丰厚的艺术储备了。但又不仅仅是艺术储备,这里明明还包藏着过人的学识、见闻、智慧和一个正直的艺术家郁闷万分的现实感受,而这一切,恰恰是寄人篱下的世阿弥所不愿意多有涉及的。正因为如此,张岱说彭天锡“串戏妙天下”,就不仅仅是褒扬他对剧目和演技的熟悉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