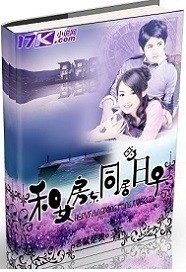多少年了,我一直洗涤心灵上的污垢,可每洗掉一点,就增加一点,总是洗不净。也就是说自己至死都高尚不起来。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伙”的?
有时,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感觉自己的灵魂都飘起来了,心里美滋滋的,有时,却幻想着把小姑娘拽进高梁地“扒去她薄薄的衣衫,凌辱她那雪白的象天使一样的肉体。”注:此句摘自《外国文艺》韩国小说<喜鹊叫>。完了,说声谢谢你给我的爱。
每当看到革命英雄人物壮烈的影视作品时,我总是热泪盈眶,可是那反靣人物尤其是日本鬼子的残暴,又让我浑身颤抖,真不敢保证日本鬼子再进咱们村,我能不能抗日到底?
我曾梦想自己是一个万能的超级外星生命;敢问茫茫宇宙,谁能主宰日月星辰?
我也曾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匹全身呛毛、枯瘦如柴的老狼,站在山颠上,仰望着云缝中的残月发出绝望的嚎叫。
这就是一个老男孩的自我解剖。
“咣、咣、咣…”
一家大酒店的门前,几十门斜竖着的小礼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不知哪对新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多大个逼事还搞炮轰。”随着阵阵的炮声,在大酒店对过的小酒馆里,正与我饮酒扯闲蛋的老班长,手中的杯子一哆嗦,掉在了桌面上,还好杯子没碎,杯里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残酒溅了出去。愣了几秒后,待炮声停了下来,老班长撇着嘴望了望窗外,用鼻子“哼”了一声,又接着说,“这若是有心脏病,红的白的就一块办了。”
我扶起老班长的杯子,又满上了一杯酒,“别转移目标啊,老班长,我刚才问你哪,东瓜西瓜南瓜都有,为何没有北瓜?”
老班长把目光转向我,端起酒杯饮了一小口,习惯性的晃晃脑袋,回答很干脆,“不知道。”
我给老班长夹了一块他最喜欢吃的鸡屁股,笑着对他说,“北瓜让傻子偷走了,有人问他,他晃着脑袋说不知道,人家再问他,他急眼了,跟人家喊,傻逼,你他妈犯病了,我说不知道,就不知—”
“停!”老班长打断了我的话,用筷子指着我的鼻尖,“你拿我当巨婴呢?用这么一个低级段子埋汰我,开玩了,是不?别看你是名牌大学蹦出来的,我他妈的也不照你差多少,本人也是七十年代第一批高考的大学漏子,就差零点五分。你是愤青我还是愤老呢。以后少在我面前玩这套业务。装逼犯。”?
我忙着辩解,“晃着脑袋说不知道的多着呢,难道大家都是傻瓜?再者说了,我可不是被人不齿的愤青,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屌丝。”
“拉倒吧,在我眼里,什么愤青屌丝,都是人渣,没出息那伙的。”老班长撇了撇嘴角,象往常那样习惯性的抬起胳膊,用袖口边抺了一下眼角上的眼屎。
人们若是注意到老班长这般模样,很难相信他曾是一个准大学生。也许是无情的岁月把他从一个文质彬彬的帅小伙折磨成一个干瘦干瘦的粗俗的小老头。有点力气的人,把他撅巴撅巴就能塞进灶坑里。
我没再言语,顺手端起了酒杯,呷了一小口,把自已喜欢吃的一片锅包肉放进了嘴里,“多吃菜少饮酒。”这是我的饮食之道。
“瞧你那意思,北瓜就是傻瓜,傻瓜就是北瓜了?”老班长放下杯子,用他那双小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这个嘛也算是一个答案。”
“这么说还有第二个答案?”老班长低下头,琢磨了一会,抬起头冷笑道,“你小子行啊,哼!挺会玩意识。我问你,我现在坐的位置是哪个方向?”
我不加思索的回答,“我对面啊。”
“好好看看。”
“咋看也是对面。”
老班长“啪”的拍了一下桌子,“你小子真他妈能装,我坐的是北面。咋的?脑袋还没起包,你就装迷糊找不着北了?”
我的脸有点发热,还好,饮点酒就脸红勃子粗的我,不用担心老班长会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对,是北面,可没有瓜啊。”
我两手一摊,笑嘻嘻地着着老班长。
“瓜,瓜。”老班长不再看着我,只是不住地挠着自己的后脑勺。这样过了一会,他放下手,那双眯缝着的小眼睛裂开了一条缝,瓦亮瓦亮的目光里似乎含有一丝寒气,“你小子把我脑袋当成了瓜,是不?”
看来,这小老头身子骨不怎么样,精神头来了却让人不寒而栗。凭我的直觉,就是有人把他捺在地上揍,他的嘴也特有尿,紧着逼扯,“有本事你打死我,靠你妈的。”
“脑袋是脑袋,瓜是瓜。”我有点底气不足,笑容也没了,只是小声反驳道,“精神病患者才会把脑袋当成瓜。”
老班长“嘿嘿”一笑,露出了他那颗还沾着菜渣的半拉门牙,“你小子心虚了,是不?我问你,脑袋和瓜加在一起是啥?”
“是啥?是俩混蛋?不对。”我用手摸摸自己的下巴,微微的摇了一下头,“咱脑袋瓜没有你那小脑袋灵光,你说是啥?
”
“哈哈。”老班长笑着把嘴角咧到了耳根下,这功夫,只要有人把他的嘴角和耳根子一上一下,轻轻一扯,准保让嘴角和耳根子来个肌肤之亲,“自己都逼逼出来了,还臭不觉呢,你个傻逼样。”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说啥了?”
老班长收敛了笑容,“脑袋瓜,你刚才说的。”
“是呀?”我点了一下头。
“脑袋瓜不也是瓜吗?三岁小孩都知道脑袋加瓜就是脑袋瓜,你他妈给我装糊涂,是不?你小子太会玩意识,你先用第一个答案埋汰了我一把,然后,你用第二个答案让傻瓜的我赶时髦,也玩了把穿越重生,坐在小酒馆里让你刷存在感,你把我的前世和今世都玩了个遍,这叫什么来着?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对不?”
我很无奈,“老班长,你这是哪个哪呀?太不靠谱了,纯扯蛋哪。只是一个低级庸俗的小段子,你就脑洞大开,七扯八咧。你啊,是不是象某些年轻人看了太多的穿越重生小说,满脑子都是梦幻?完了,把夜壶扣在自己脑袋上,还以为是皇冠或是逍遥小地主的瓜皮帽。”
“纠正一下,不是夜壶,应该说把—”老班长的小眼睛紧着眨巴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啊,你小子又给我设套了,那三个脏字我不说了。总听你穷白乎了,也该我考考你了,我可没设套。我问你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是哪个逼第一个先说的?”
我也象老班长那样习惯性的晃了下脑袋,回答也很干脆,“不知道。”
“平常,你总是卖弄小聪明,那小嘴紧着逼逼,这回咋瘪茄子了?”老班长又笑了,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仿佛他也玩一把存在感。
“这么说吧,这个人叫啥名我不知道,”我用肯定的语气接着说,“不过从你对这个人的态度来看,他不是个争议人物,也是个历史罪人。”
“靠,我问你是谁?没让你给人家定性,又装逼了是不?”老班长的小眼睛瞪得溜圆,语气也很严厉。
“已经回答了,是争议人物或历史罪人。”
“你,你。”老班长干嘎巴嘴,一时语塞。
这回该我得意洋洋了,“回答的不对吗?你问的是谁?不是姓啥?名啥?”
“算你小子比北瓜懂点事。”老班长的语气有所缓和,“我再问你,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句话是谁第一个先说的,他叫啥名?”
我自信的一笑,“哈哈!这个你可难不住我,他是圣人孔子。”
“那老而不死视为贼呢?”老班长又问,“也是孔圣人说的吗?”
这回轮到我语塞了,直勾勾地看着老班长。
“停电了吧,你倒逼逼呀?”
“哎哟,你就别整节目了,告诉我,这两句话谁说的,就得了,猪八戒看报纸—硬充文化人。”
老班长架起了二郎腿,两只脚紧着颤悠,开始玩造型升级,得意洋洋变成了趾高气昂,嗬!这个得瑟劲就甭提了,“很简单,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真是气死我了。
我呼呼地喘着粗气,狠狠地瞪了老班长一眼,“说我跟你玩意识,你干啥呢?”
“第四个问题,”老班长没有回答我的问话,用他那双眯缝着的小眼睛瞧了瞧我碗里的最后一块锅包肉,嘴角咧了两下,很快,那块锅包肉随着喉节的耸动,进入了他的消化系统,看来他喜欢吃的不仅仅是鸡屁股,“自已裤裆不利索就不要抖露别人的裤衩子,这句话是谁第一个先说的?”
我没给老班长好脸子,把头一扭,“这个网上也有?”
“绝对没有。”老班长放下二郎腿,板直身子,颇有点庄严的派头,仿佛他就是当代圣人,“全地球村除了我没一个人知道,因为这句话是鄙人第一个先说的。不信,你从网上查一下。跟你说,我这是有感而发,看不过某些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纯他妈的装逼犯,尤其是那个漂亮国,是世界头号装逼犯。打倒装逼犯。”
说到这里,老班长情绪甚是激动,脸色如同猪肝,但这与酒精没一毛关系。受老班长的气场感染,我也跟着他咬牙挥拳头,对他的那小小的不满立马抛到了九霄云外。不明白的人,还以为我俩酒喝多了,耍彪呢。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一星期前我和老班长痛揍小偷的情景;老班长也是这番模样,只是他那双小眼睛没有象今天这样露出一丝让人倍感恐怖的凶光。看来,这小老头年轻时绝不是一般“战士”。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轻轻拍了一下老班长的肩膀,“拉倒吧,‘激情燃烧的岁月’早就过去了。咱俩的酒也喝完了,走,上哪逛荡逛荡去?”。
请斧正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