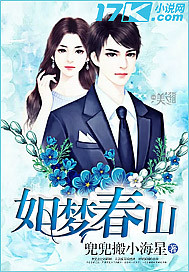终于在她六岁的时候,爸妈平静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她跟着爸爸。她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不要她,她不是说她是她最爱的人吗?为什么不把最爱的人带走呢?
妈妈半个月来一次。带她看电影、逛书店、吃好吃的、去游乐场。
妈妈的新家收拾的很干净。
床又大又软,她开心地在上面跳来跳去。
妈妈穿着丝质的白色睡衣,坐在梳妆镜前仔细地梳长长的黑发,红色的指甲在黑发中忽隐忽现,风情万种。
“妈妈,我也要涂红指甲。”
“好看吗?”妈妈把白嫩的手伸到她面前,“喜欢吗?”
“嗯。喜欢。”
妈妈打开化妆包,拿出一个细高的粉色小瓶,“给你的。”
她把玩着小瓶,眼睛放光。
“来,妈妈帮你涂。”
妈妈小心地把她的小手指一个个涂上亮晶晶的液体。一股刺鼻的气味在房间弥漫开来。
“好难闻!”她说。
“可涂上它,你会更漂亮。宝贝,很多漂亮的东西是有毒的。”
“妈妈,你也有毒吗?”
“瞎说。妈妈怎么会有毒。”妈妈用手指轻轻刮了一下她的鼻头说。
“因为你漂亮呀。”
妈妈笑起来,她的宝贝太可爱了。
她拿起梳妆台上一个精致的瓶子,打开,对着空中一按,“噗噗”地喷出几滴水雾,整个屋子立刻充满芳香,仿佛屋子里有个百花园。
“这是什么?”
“香水。”
“干什么用的?”
“喷在衣服上的。”
“为什么要喷衣服上?”
“因为可以变香?”
“为什么要变香?”
“因为喜欢?”
“为什么喜欢?”
妈妈答不上来,她们的谈话进去了死胡同。
十万个为什么的节奏,受不了呀!
那次妈妈把她送回来。爸爸和妈妈又吵了一架。
“你以后不要给孩子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孩子会学坏的。”爸爸生气地说。这个女人越来越不知如何疼孩子,每次来看孩子总带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还说是什么高档货,有几个钱了不起呀,浮夸!
“孩子喜欢,哄她开心喽。”
“你知不知道,每次从你那里回来。我都要花很长时间改掉你灌输的那些东西!”
“为什么改掉?我的东西有毒吗?何天成,你什么意思?”
“你说呢?”爸爸反问,“不要觉得有几个臭钱,就跑来现摆。”
“我有没有钱,和你又关系吗?我们已经离婚了,没有任何关系,OK?不要对我指手画脚,你没资格。”妈妈很生气。
这个男人可真够可以的,离婚后还一副老古董的样子,保守僵化,动不动指手画脚。
“我没资格?你有资格吗?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像你一样整天化的像只猴子。否则,取消你的探视权。”
妈妈气的手指乱抖,“我要起诉你,要回女儿的抚养权。”
“随你的便!”爸爸把门打开,“请吧,这里不欢迎你。”
她从窗户看见妈妈背着小坤包,黑发的长发在身后随着步子有规律起伏,妈妈真的很漂亮,可为什么爸爸还和她吵?
妈妈消失了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回来时她上二年级了。
那天下午放学后,她刚走到学校门口,听见有人喊自己名字,回头一看:不远处一辆红色汽车旁站着一位干练十足的时髦阿姨,一套剪裁合体的乳白色套装衬托的胸部愈加饱满高耸,腰身修长,脚穿一双白色小高跟,栗色大波浪侧披一旁。面上一幅黑超更增添了几分霸气。
香车美女引得路人频频回望。
漂亮阿姨红唇紧闭,浑身散发着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傲。
看见自己有些疑惑,漂亮阿姨摘下黑超,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秋日的阳光下,妆容精致,妖娆多姿。
“妈——妈,妈妈。”她迟疑地喊。
妈妈快步走过来,弯腰抱住她,把脸贴在她的小脸上,好一会才放开。
“上车吧!咱们去吃好吃的。”
“师傅,开车,去爱丽丝餐厅。”妈妈对司机说。
爱丽丝ALLCE是本市最有名的西餐厅。坐落在繁华地带,门口立着一个巨幅广告牌,上面是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身边有一只兔子和毛毛虫。长大后才知道那上面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人物。
餐厅内人不多,毕竟喜欢吃西餐的中国人不多。有时候吃西餐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新鲜。
那是她第一次接触西餐。银制小巧的刀叉让她觉得好玩,就像小时候过家家用的道具,很好玩。她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餐布铺在腿上,一边用叉按住牛肉,一边用刀来回划。盘子发出刺耳的“咯吱咯吱”声。好不容易划掉一块牛肉,放进嘴里,小丫头眉头一皱。
“呀!好难吃。”
妈妈娴熟地用刀割下一小块牛肉,优雅地放进嘴里,慢慢咀嚼。食指拇指中指捏住高脚杯细细的杯柱,轻啜一口杯中诱人的红色液体。
没有爸爸做的土豆炖牛肉浓香有嚼劲。尽管看着卖相不错。
桌子上一盒蛋糕,上面铺满白色的奶油,芭比公主带着一只小狗站在一片白雪里。几颗红色的樱桃呈弧形托着一顶闪闪发光的王冠。蓝色的月亮镶嵌一圈。
一盘水果沙拉,红的黄的绿的白的,五彩缤纷。
“我的小公主。生日快乐。”妈妈轻声哼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妈妈拍着手,满脸幸福地唱。她小手合十,对着跳跃的烛光,许下一个七岁女孩的愿意——让妈妈回家。
那天晚上爸爸接她回家。在公交车上,他拉着她,一路上嘴角紧抿,脸色苍白,一改往日的温和。
她却自顾自地说着牛奶,面包,沙拉,王冠和生日蛋糕,一切与妈妈有关的惊喜与美好。没有注意到爸爸的沉默。
门打开,再“啪”的一声关上。一扇门把世界分成两边。门外的热闹与门里的清冷形成强烈的对比。
“一个蛋糕就把你收买了!我天天为你洗衣做饭,接送你上下学怎么算?为什么一个蛋糕就让你一路喋喋不休?”爸爸尽管尽量控制着音量,但她分明感受到他的怒火。
她低下头,靠在墙角。
“告诉我,蛋糕好吃吗?甜吗?”爸爸摇晃她的胳膊。
她看见爸爸的眼睛瞪得很大,和电视里生气的老虎一样可怕。她点点头,马上又摇摇头。
“你说呀!到底是甜还是不甜?”不知为何声量立刻高起来。她被吓到了,眼泪在眼框里打转,惊恐地看着面前扭曲的面孔,泪终于缓缓地流下来,流过脸颊,流入嘴角,咸咸的,有点苦。不知道为什么,她竟然没有哭出声。
对视多久,她记不得了。也许10秒,也许10分钟,眼前这个男人才灵魂回归,变成她稳重慈爱的爸爸。他摸摸她的头,轻轻把她揽入怀里,一股温热的淋透她的衬衫。她知道面前的这个男人哭了。
和她一样。
从此,她再也不提妈妈的事了,甚至连妈妈这个名词也不在提起。她把那个充满爱的名字埋在心底最最幽深的角落,绝口不再提起。
因为她不想让爸爸伤心。
虽然她不懂他的忧伤。
其实,他也不懂她的忧伤。一个二年级孩子的忧伤。
时间真是一个矛盾体,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
小时候总觉得时间很慢,盼望长大。
自那件事之后,她和爸爸之间总像隔着什么,言语间充满客套,生疏。她不明白大人总是说珍惜眼前人,为什么他们说分开就分开?为什么分开后就不能再和好如初呢?
她想等自己长大了会找到答案的。
转眼之间,她考上大学,长大了。却发现,长大是件更麻烦的事。
暑假前爸爸曾在电话里含蓄地暗示过她,想成立一个家。她不是不懂事的孩子,觉得自己大了。这些年来,爸爸也很孤单,辛苦。若真能找个人陪伴度过后半生,也不失为一件美事。所以爽快地同意了。只有一个条件——对爸爸好。
可昨天爸爸告诉她要结婚的女人竟然是那个逼走妈妈的女人,那个护士。这么多年他们还藕断丝连。她怎能不伤心绝望。家因那个女人解体,妈妈因那个女人消失不见。她因那个女人被同学瞧不起。
现在因为自己长大了,他们可以心安理得的结婚了。曾经疼爱自己的爸爸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疼她哄她。以前只要爸爸去相亲或者说带阿姨回家,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谁叫也不开,绝食不吃饭。屡试不爽。其实她也不是真的绝食,提前藏了零食在房间。就这样拖这直到爸爸妥协,直到她长大。
而这次爸爸态度坚决,铁了心要做新郎官。无论她多么强烈的反对,爸爸不理她。她这招失灵了。
如果长大以失去为代价,她宁可不要。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那个女人?”她抬起泪眼看着卞爱。
天下女人那么多,他为什么偏偏选她?难道他不知道她最讨厌她吗?
卞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成人的世界太过沉重复杂,不是对与错,黑与白就可以解决的。年轻的她们找不到答案。
她们正一步步朝着那个世界靠近,不管愿不愿意。
卞爱茫然地看着远方,手无意识的握成拳头,好像要握住什么。脑海里冒出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