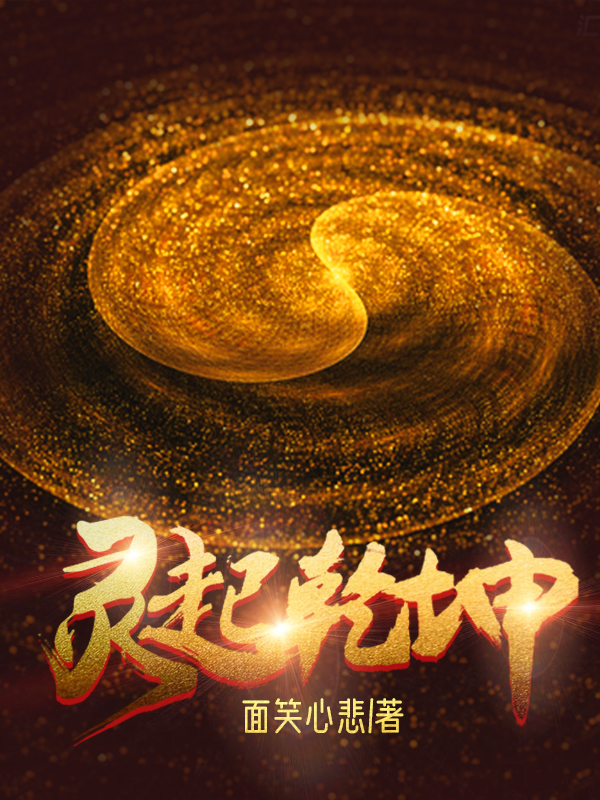此刻正是二人心理战争的开始,郑大吉额头隐隐蓄满了汗,他也不敢低头擦,心中揣测万分。
莫非他采买物资阳奉阴违的事情被发现了?
“郑大人,昨日城内发生了一桩奇事你可知晓?”上官饮凌一撩官袍,二郎腿翘起来,靠着椅背,伸手拿过了刚刚衙差放在侧边小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浮叶,喝了口,“本官可是听闻,从天而降的这些食粮,是出自你郑大人的府中。”
郑大吉神色一震,脚下几乎站不稳,却还是强压住心头不安:“大人,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若是下官府中有如此多的粮草,怎会不拿出来救济百姓呢!这传播谣言的人实属丧心病狂!来人啊,全程搜捕传播谣言之人!”
上官饮凌也不拦,任由郑大吉派人去找。
“起初本官也是不信的,只不过郑大人手下采买粮食几日未果,不得不让本官怀疑,郑大人是不是朝廷的父母官,究竟有没有把心思用在百姓身上。”上官饮凌说着,微微抬眼,看向身前的郑大吉,眸色凌厉,“本官前两日刚刚上书圣上,说郑大人赈灾得力,郑大人莫不成就要打我的脸?”
“不不不,下官怎么敢?”郑大吉心头一虚,慌不择路的顺着上官饮凌的话下坡,“采买之事的确是手下人办事不利,下官这就去催赶,他们一定能在明日带回粮食物资来,请大人再等候一日!”
“那本官就再等郑大人一日,若是明日不见粮食,郑大吉就该要想想,如何同圣上交代了。”上官饮凌说完便起身离开,陆离特意慢了两步,故意留下来提点郑大吉。
“我说郑大人,您此次当真是为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啊,百姓家中从天降粮的事若不是上官大人为您压下来,传到圣上耳中,即便与你没有关系,圣上却不会这样想。”陆离小声提点,说罢还颇同情的拍了拍郑大吉的肩膀,“大人,同在朝中为官,我们大人知道您的难处,可是赈灾乃是圣上严令,您也得让我们大人交的了差是不是?”
“是是是,是我疏忽了,还劳烦陆师爷一顶在大人面前替我多多美言,明日下官一定将粮食运回。”郑大吉连连点头,心中也替自己捏了把汗。
陆离这才离开,待到驿站门口,同上官饮凌和徐运汇合。
“如何?”上官饮凌脸上带了几分笑,目光转向陆离,虽然是询问,神色中却已有了九成把握。
“如大人所料,郑大吉果然慌乱,着了大人的道,明日应当便会运回粮食物资,赈灾有望了。”陆离回答。
“大人,你们莫不是演了一出戏来诓郑大吉?”徐运这才后知后觉刚刚的一切只是一场诓骗郑大吉采买的大戏,他还以为是大人为了洗清嫌疑才这样说的呢。
“徐运,有时间看看郎中。”上官饮凌看着徐运,宛若看着自家不争气的儿子一般,恨铁不成钢的轻叹口气,转身上楼回了厢房。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徐运摸摸后脑勺,没有领会。
“你家大人的意思是让你去看看脑子,把里面的水都放出来。”陆离一摇折扇,扇着风上楼了。
“嘿……”敢情一个两个都在骂他。
又过了一日,次日下午,太阳落山之前,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拉着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回到宝州城,在府衙旁建起了物资领用站,城中的百姓一片欢呼,排起了长队。
陆离等人在领用站分发粮食和一些草药之类,很多百姓领完,都要到府衙门前拜上一拜,对着知府大人说上几句感谢的话。
“知府大人如再生父母,知府大人清官廉政,为民请命,是大大的好官呐!”
陆离轻叹一声,可怜了这些百姓,竟然不知多年来信任的府衙县令贪了他们多少血汗,如今家中库房还存放着数百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他们在街头几近饿死之时,郑大吉正在自家庭院吃肉喝酒,好不快活。
上官饮凌到领用站的时候,队伍已经到了最尾,只有几个年迈的婆婆大伯在领粮食,天色已然大黑,领用站周边点了两盏火灯,照的附近一条街都过分明亮,上官饮凌站在陆离身旁,把米面分好,递给老伯。
“老伯您收好。”
“这郑大吉为官这么多年,可算做了一件人事啊……”老伯接过米面,低声喟叹,脸上的苦涩之情过分明显。
“老伯,可否与我详细说说,这郑大吉这些年都做了什么混账事?”眼看老伯转身要走,上官饮凌忙叫住他,老伯回头,看向他的目光中充满抵触。
“老伯放心,这是圣上派来赈灾的钦差大人,也是因为他,今日大家才有这么多的粮食吃,有话大可以对钦差大人说,大人一定会为你们做主的。”陆离见老伯并不信得过上官饮凌,忙帮着解释了几句。
“唉,造孽啊!”
二人坐在火灯下,听着老伯将郑大吉这么多年尸位素餐买官卖官的混账事说了个清楚。
除了这些,他们还得知了最重要的一点,郑大吉将宝州百姓的赋税增加到朝廷征收的两倍不止,宝州百姓近十年来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度日,却无一人敢上京明言,郑大吉甚至一直对百姓宣称,正是朝廷下令收取如此多的赋税,他也心疼百姓,却也无可奈何。
实在是可恶至极。
“老伯,你且宽心,今日我既来了宝州,就绝不会轻易回去,郑大吉的事,待到赈灾结束,我一定上书圣上,严惩不贷。”
“多谢钦差大人,多谢钦差大人……”
老伯连连感谢,送走老伯,二人依旧在火灯底下坐着。
“大人,您不觉得奇怪吗?郑大吉近十年贪赃枉法可谓是十分嚣张,近十年的贪赃,绝不可能只有几个库房这么多的金银,还有一大部分,他藏到了何处?”陆离凛眉,回忆起那夜他们潜入县令府,虽说金银玉器不少,却也不够买百姓这十年的赋税。
“恐怕,剩下的已不在他手中。”上官饮凌眉头微皱,双眼直视前方,眼中有着更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