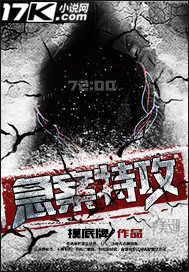很显然,这是别人给她写的,本来想以她的口气说话,但写着写着又变成了第三人称。
这件T恤就相当于一个狗牌。
小差帮她把衣服穿上了。
Asa说:“我们得把她送回家。”
四爷说:“可是,周Sir把我们告发了,我们回去太危险了”
Asa看都不看她:“谁跟我一起去?”
没人说话。
Asa看了看我,我说:“好吧”
小差说:“那你俩去送她,我们接着去找那个湖。你们尽快赶过来。”
Asa说:“没问题。”
接着,我和Asa就带着秀秀离开了,好在这个地方离西区并不远。
秀秀很听话,只在半路上停下过一次,怎么劝都不走,硬说她的车又出问题了,需要我们帮忙,我只好又跟她演了一遍戏,给了她10块钱,她这才喜滋滋地迈步了。
她家确实在西区的背后,红砖房上爬满了藤蔓,孤零零的,就像个不合群的鳏夫。
借着雾气的掩护,我们悄悄来到房子前,发现房门竟然是不锈钢的防盗门。
秀秀直接把门推开走进去了。在东北农村基本没有敲门的习惯,大家串门都是推门就进的。虽然404是个城市,但很多习俗更像农村。
我和Asa跟着走进去了。
这房子的装潢是典型的八九十年代风格,地上铺着地板革,客厅有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它对面是一排沙发一块水墨画屏风把客厅一分为二,不知道屏风那头是什么。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正坐在沙发上看书,她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立即站起来对秀秀说:“哎呦,你这是跑到哪儿去了?”
秀秀没理她,直接走过去把电视打开了,里面出现了黑白的雪花。
老妪这才对我们说:“谢谢你们了,快请坐。”
Asa说:“她是你们的女儿吧?”
老妪赶紧点头:“是的是的。”
Asa说:“那就对了。”
这时候,一位头发同样花白的老翁从屏风那头走出来——你可能觉得老翁和老妪的叫法有点别扭,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这么称呼他们。老翁蓄着长长的胡子,仙风道骨的样子,看上去年龄跟老妪差不多,应该有70岁了。他怎么都要我们坐下喝口热水,我们只好听从,顺便歇歇脚。
老妪把秀秀送进了屏风里面,然后关掉“吱啦啦”的电视,给我们沏了一壶茶。
Asa大概说了一下我们遇到秀秀的经过。
老翁说:“她都走失一整天了,我们都急死了。”
Asa说:“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老翁说:“请讲。”
Asa说:“这个女孩是不是你们买来的?”
我一愣,老妪赶紧摆手:“不是,绝对不是。”
Asa的手里还端着人家的茶,眼里却闪烁着侦探一样的不信任:“你们的年龄对不上。”
老翁点点头,说:“她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说起来话就长了。”
Asa一直盯着老翁:“你说。”
老翁说:“五六年前,我老伴在路上遇到了她,当时她正在哭,我老伴以为她是哪个职工的子女,就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的车坏了,我老伴跟她交流了一会儿,发现她好像精神有问题,就把她带回家了,从此她就成了我们的家人。”
Asa说:“这种情况应该报警啊。”
老翁说:“报了,但秀秀说不清楚信息,所以一直没找到她的家人。”停了停他又说:“我和于老师一直无后,也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他口中的“于老师”应该就是那位老妪。老两口看起来应该是知识分子,举手投足都文质彬彬的。
Asa点点头,表示相信了。接着他就坐不住了,放下茶杯对我说:“我们该走了。”
我却不想走。
我对老翁说:“还没请教您贵姓?”
老翁说:“我姓翁,你就叫我翁老师吧。”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他们老翁和老妪了吧。
我说:“您是老师?”
翁老师说:“我来404之前是老师,我老伴跟我一样,我们都在地质大学教书。”
当年的404都是高精尖人才啊。
我说:“那个女孩本来就叫秀秀吗?”
翁老师说:“是的,她清醒的时候说的。”
我说:“她还说过什么?”
翁老师说:“我只知道她是来旅游的,还有个女孩,但是那个女孩稀里糊涂地不见了。”
不见了?我看了看Asa,Asa也看了看我,难道又是一起消失事件?
翁老师问:“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呢。”
我说:“做好事不留名。”
翁老师笑着点了点头:“你们要是在404里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别的事做不了,吃口热乎饭还是可以的。于老师是四川人,她的手艺很棒的。”
我说:“谢谢,有机会一定品尝。”
Asa已经按捺不住,站起来了。
我和Asa跟老两口告别的时候,秀秀也出来了,她都到家了,也不提还钱的事了,看看,我说过是骗子吧?
我们正要走出去,翁老师突然说:“广播里说的就是你们吧?”
我一下就停下来了,他很慈祥地笑了笑,然后朝我们扬了扬手,意思是:孩子,走吧。
我又被感动到了。
多像谍战剧里,一个地下党受伤了,跑进了一个老百姓家,本来他隐藏了身份,只想讨口水喝,喝完之后,正要一瘸一拐地离开,那个老百姓却给他的口袋里塞了几个馍,小声说:孩子,吃饱了才好去打仗!
我和Asa再次扎进了浓雾中。
我们走在主路上,速度快了很多,一路都没遇到什么人,半个多钟头之后就追上了小差他们。
小差问:“送回去了?”
我“嗯”了一声。
人一累脑袋就停转,我看了看碧碧,突然说:“我有点忘了,你是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了?”
碧碧说:“送你们出去啊。”
我说:“噢,送我们出去”
碧碧说:“当然了,我也顺便找找我朋友的线索。”
我对小差说:“秀秀也是来旅游的,当时她还有个同伴儿,好像也失踪了,不知道秀秀经历了什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四爷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阴森啊。”
我说:“所以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我们来到了主路的拐角,看到了一辆废弃的公交车,两旁都是芦苇荡,根本没有什么湖。
我们走过去,看见车上写着路线:刑场到断头(4路环线)。果然,主路上分了一条岔路出去,只有几十米长,然后就被芦苇挡住了,尽头是几根水泥路桩。就是说,这里叫“断头”,这趟车的起点是刑场,终点是断头,而且还是环线。传说中,枉死的人会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一样,一直在殒命之地徘徊,无法投胎。这条线路多像个死刑犯的灵魂啊,一直在刑场、断头、刑场、断头之间往复
小差说:“这里的空气有点腥。”
我抽动了几下鼻子,说:“附近应该有湖。”
小差朝那条断头路指了指:“我们去那里看看。”
大家走过那几个路桩,扒开芦苇朝里深入,看到了一道低矮的水坝,它很窄,两个人都无法并排在上面行走,简直就像平衡木。上面有一些年头久远的脚印,那应该是割苇子的人留下的。
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只能走上去。
水坝上很泥泞,所有人的鞋子上都是泥巴,很像越战时美国大兵的靴子。
大家走得小心翼翼,就算这样,碧碧还是没保持好平衡,一脚滑下去了,他爬上来的时候,膝盖以下都湿了。他非说小马哥推了他,小马哥坚持说没有,两个人就拌起嘴来。
水腥气越来越重了。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水坝的尽头,前面变成了荒草甸子,除了几棵叫不出名字的矮树之外,遍地都是潮湿的荒草。
我们继续朝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巨大的水域。
如果是晴天,我们早就应该看到它了,但是雾太大了,我们等于撞到了它的鼻子上才发现它的存在。
湖水是绿色的,红色的雾气飘在上面,有点像某些劣质神话剧里的仙境。
看不到对岸。
这就是我们离开404的最后一道屏障了。
碧碧四下看了看,低声说:“这个湖有潮汐。”
什么话,只有大海才有潮汐。
Asa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碧碧指了指水陆的分界线:“你们看。”
果然,岸边有一条几米宽的退潮痕迹,上面遗留着一些螺蛳之类的小生物。
难道这是海?
我撩起一把水舔了舔,说:“淡水。”
小马哥一直在东张西望,他突然说:“那里有条小船。”
我们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不远处果然有一条小船,它拴在湖边的木桩上,一半在水里,一半在陆地上,竟然有一种水墨画的效果。
我们立刻跑了过去。
小船是木头的,没有舱,只有两排横亘的木板,那就是座位了。小船两侧拴着两支寒酸的桨,靠近水面的部分长着青苔,看来它停滞很久了。
我有点犯愁:“能坐下我们这么多人吗”
四爷说:“挤挤呗。”
我说:“你知道超载的后果吗?”
四爷说:“还超载,这里又没有交警。”
我说:“可是它会翻。”
小差说:“我们分批吧,先去三个人找对岸,找到之后再回来接人。我留下。”
Asa说:“我也留下。”
本来我也想留下,因为我很怕水,但一想到对岸就不是404了,我恨不能立刻登上船去。
小马哥已经解开了绳子,我和他一起把小船推进了水中,然后爬了上去。四爷也挽起裤腿儿走过来了,她没什么经验,一脚踩在船沿上,小船立即就倾斜了,小马哥赶紧扶住她,然后劈开双腿寻找平衡。船上灌进了不少水,但终于稳住了。
四爷在我旁边坐下来,伸手抓起了桨。
小马哥说:“老大,你坐船头吧。”
四爷把眼睛一瞪:“你当我不会划?”
小马哥说:“压秤很重要,你要不在船头坐着,这船就得仰过去。”
四爷这才去了船头。
我和小马哥一人抄起了一支桨。
我只在北海公园划过一次船,到了湖心怎么都回不去了,最后,我带的那个女孩把桨夺过去,“嗖嗖嗖”地划到了岸边,之后我跟她再没联系过。
虽然小马哥很有经验,但我不给力,头两分钟小船一直在水里打转。
四爷叫起来:“你们行不行啊?我都要晕船了。”
最后,我俩总算有了点默契,伴着划桨声,小船朝着雾气深处移动了。
过了会儿,我回头看了看岸边,已经看不见小差、Asa和碧碧了。四周雾气茫茫,湖水茫茫,我的心里不由慌起来。脚下没根,心里更没根。
没有参照物,小船就像没走一样。
划了大概十多分钟,四爷也有点不踏实了:“这湖到底多大啊?岸呢?”
我说:“湖越大,我们离开404的几率就越大。”
四爷说:“就我们这速度,还不如老年代步车呢。”
小船好像听到了我们的对话,速度突然变快了。
四爷说:“你们早就该这么用劲儿。”
小马哥喊起来:“不对,是它在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