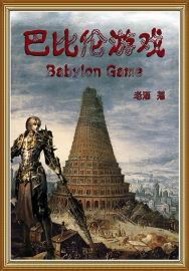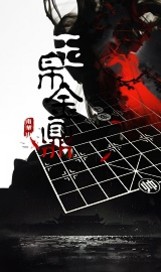碧碧说:“不是。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福建人。”
我说:“404职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碧碧摇了摇头:“我跟他很熟,他父母都在福建做生意,从没来过东北。”
小差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她在认真地聆听。对于她来说,任何猜测都可能是一种启发。
我忽然蹦出了一种猜测,公交车下的尸体会不会正是碧碧要找的那个驴友呢?
我说:“老K多大年纪?”
碧碧说:“跟我差不多。”
显然不是。
我们刚刚走进那个报纸发行站,碧碧就叫起来:“这就是你们的据点?太脏了。”
四爷说:“谁说这是我们的据点啊,我们只是路过,在这里暂停一下。”
接着,我们吃了点东西。碧碧带了几包青岛特产卤海蜇皮,我一口饼干,一口海蜇皮,竟然挺好吃。
小差说:“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出去吧。”
我说:“从哨卡肯定出不去。”
小差说:“没有别的路吗?”
我看了看碧碧,碧碧说:“好像没有。”
我说:“就算有,下这么大的雾,我们上哪儿找去?”
四爷朝外看了看:“能不能想办法除雾啊?”
我说:“那你得去跟老天爷要个授权。”
四爷说:“你少阴阳怪气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有人发明了一种‘扇风除雾霾’的方法,如果北京能聚集一千五百万人,用特制的扇子集体朝东南方向扇风,就可以把北京的雾霾扇到天津去。然后天津人民马上接力,他们只要组织起五百万人就可以了,也用那种扇子朝东扇风,就可以把雾霾扇到海上去了。”
碧碧实在没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这真不是个段子?”
四爷说:“绝对是正经新闻。”停了停又说:“我就是给你们开拓一下思路。”
想想,我们几个人站在404正中央,男的光着膀子,女孩穿着短裤,一声令下,大家一起拼命扇风。我旁边还有陈工、邢开、光头、板寸、黑框眼镜,以及西区的周Sir和大波浪等等,他们也同样光着膀子,穿着短裤,眼睛里冒着灼灼烈焰,那是无产阶级者的信仰之光,扇啊扇,扇啊扇
四爷忽然想到了什么:“哎,要是能把石棺里的机器重新开动起来,404就会升温,也可以把雾驱散掉。”
我说:“那你需要去联合国找安东尼奥商量一下。”
四爷捅了我一拳:“你丫就贫吧,我还不贡献我的智慧了。”
Asa说话了:“现实点吧,我们去西区找人问问路。”
碧碧问:“西区?”
我说:“那儿住了一群钉子户。”
碧碧说:“你们正在被通缉,去了西区还不被人一网打尽啊?”
我说:“那个周Sir跟我们成朋友了,他不会举报我们的。”
碧碧摇摇头,说:“还是小心为妙。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接近西区的时候,你们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一个人去打听。”
我说:“行。”
大家收拾东西的时候,Asa还在翻报纸,突然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雾并不是天气现象?”
碧碧对此很感兴趣:“你说说。”
Asa说:“或许是人造的你们见过红色的雾吗?”
四爷说:“你是说这雾是404特制的?”
Asa说:“看晚会的时候,经常有人造雾啊。”
我说:“弟弟,那是干冰,固态二氧化碳。我们这个雾要是干冰造的,我们早就没有空气呼吸了。”
Asa这才放下报纸,拎上行李箱,跟我们出来了。
我们没有走主路,专挑偏僻的街巷前行,最大可能地避开巡逻队。
比起我们刚进那个报纸发行站的时候,雾气显然更浓了,简直伸手不见五指。
这种天气,即使办公大楼的人出来巡逻也不容易看到我们,这让我有了一种安全感。
我们渐渐来到了一片野地上,此处杂草从生,足有半人高,还有一种类似玫瑰的花,花也高,就像山里的女人。这里终于没有大喇叭了。
Asa还推着那辆150元买来的自行车,大部分行李都绑在车架上。自行车的挡泥板总是被泥巴塞满,他走一段就得用树枝扒拉扒拉。
自行车好像要散架了,一路都在吱呀作响。没人觉得它吵,它的声音让我们不寂寞。
我一直盯着脚下,很奇怪,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影子。
在都市里,阳光都被高楼挡住了,很少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影子,但小时候,影子却是我们最长久的玩伴。
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我的心里对他有芥蒂,这种芥蒂让我跟我的影子越来越亲近。
男孩喜欢跟沙盘上的士兵对话,女孩往往跟芭比娃娃是闺蜜,而我自己的影子就是我的士兵和芭比娃娃。
影子总会回应我,甚至还跟我一起玩游戏。晚上,母亲熄了灯,帮我掖好被子,关上房门,我听着她的脚步声离开,总会偷偷打开床头灯,在昏黄的灯光下,影子如约地出现,我和他玩石头剪子布,当然总是平局。但有一次,我出了石头,它出了布,它赢了。
我发誓当时我没有睡着,换句话说,那不是梦。
大人们把这件事当成了笑话,一直讲到我长大。一来二去,我也有点怀疑自己的记忆了。记得小学的时候,学校为单亲家庭的孩子请来了心理医生,那个医生聊起天来很对我的口味,简直就是我的知心姐姐,我一股脑地说了好多话,甚至还想介绍她跟我的影子认识一下
后来长大了一些,我在家偶尔发现了那位心理医生写给家长的报告,上面说:孩子因为从小没见过父亲,导致父爱缺失,有轻微的自闭症倾向
想着想着我忽然有些警惕,这么大的雾,怎么会有影子?
我抬头朝上看去,半空中果然出现了一个发光物,我还听见了很轻微的“嗡嗡”声,我说:“等一下!”
大家陆续停下来,我朝上指了指:“你们看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发光物似乎知道自己被发现了,“嗖”一下就躲进浓雾中不见了。
所有人都朝上看了看,四爷说:“没有啊。”
我使劲搓了搓耳朵,声音也没了。
我问其他人:“你们都没看见?”
所有人都摇了摇头。
我说:“我可能看花眼了走吧。”
当时,我真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一架无人机!如果我早点警惕,也许会少走很多弯路。
我走到Asa身旁,低声说:“那帮黑风衣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是再不出去我会崩溃的。”
Asa任劳任怨地推着车,一言不发。我这才注意到他戴着耳机,那好像已经成了他的形象定位了,一摘下来,他的脑袋就好像少了什么器官似的。
我想到了耳机里那个神秘的广播声,于是碰了碰他,他这才看了看我,我说:“你又听到了?”
他习以为常地点点头:“我们从戈壁滩出来之后,我一直听见很多人走来走去,再就没有别的声音了。”
我说:“你一直在听?”
他说:“就当听收音机了。”
我说:“可惜什么忙都帮不上。”
他说:“不要急,我相信早晚会筛到有用信息的。”
我们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雾中突然出现了一栋房子,那是个废弃的道班房,很矮,踮起脚就能摸到屋顶,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我们走进去,纷纷坐下来歇息。
小差说:“前面就是西区了,碧碧你过去吧。第一座房子就是周sir家,你找他。”
碧碧瞥了瞥Asa的那辆自行车:“我能骑车去吗?”
Asa说:“那你得给我留点押金。”
碧碧笑了,他饶有兴致地看着Asa问:“我要留多少钱?”
Asa不假思索地说:“50吧。”
碧碧说:“你不讲规矩。”
估计Asa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他不讲规矩,他愣了愣:“我哪里不讲规矩了?”
碧碧说:“合同法规定,押金数量不能超过总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你这辆车多少钱?”
还没等Asa开口,我就说:“150。”
碧碧说:“150的百分之二十是30,你却问我要50,你不讲规矩。”
Asa朝他挥了挥手,说:“逗你呢,骑去吧。”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见到Asa开玩笑。
碧碧好像很开心得到了这辆自行车,他卸下我们的行李,喜滋滋地骑走了。
我对Asa说:“我不高兴了啊,上次我管你借车,你不但给我出了一份合同,还让我按了手印,今天规矩怎么变了?”
Asa说:“不一样,人家碧碧这是义务帮我们忙。”
碧碧离开之后,过了大概一个小时还不见他回来,难道他在大雾中迷路了?道班房附近好像是蟋蟀的大本营,它们一直在叫,此起彼伏。我觉得东北的蟋蟀叫起来似乎也有东北口音。
四爷有点着急了:“总待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儿?我去找找他。”
小马哥说:“老大,我陪你去。”
我说:“再等等。”
四爷说:“西区又没有武装,怕什么?”
我说:“要是你俩也不回来怎么办?葫芦娃救爷爷,挨个失踪,我们还不如自己解散了。”
小马哥突然压低声音说:“他好像回来了。”
我朝房子外面看去,都是雾,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听到了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很多人正在穿过草地,朝着道班房围拢过来,没有一个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