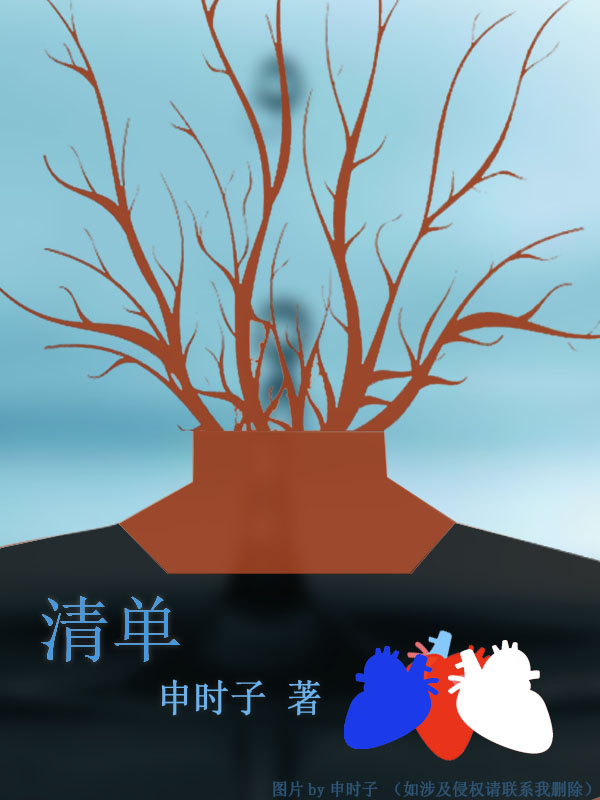此时大家都在东屋,而我刚刚来到厨房里,可以把厨房理解成一个过道。西屋这声“救命”把我吓了一跳,马上想到老少间里肯定藏着人,就是他在呼救。
我紧紧盯着西屋那扇半开的门,一双脚本能地朝东屋移去。
小差从东屋跑出来,喊了声:“C加加?”
我这才醒过腔来,那是C加加的声音——这个人很少说话,导致我竟没有听出来。
小差已经跑进了西屋。我也跟了过去。
C加加就像中邪了一样,正对着半空挥舞着双臂,好像在驱赶什么,一只手上还紧紧握着他的手机。
看来,他嫌吵,一个人跑到西屋玩手机来了。
小差问:“你怎么了?”
C加加说:“这屋里有东西!”
小差说:“什么东西?”
C加加说:“它们在咬我!”
我立刻看了看老少间,那扇门依然锁得严严实实,只有下面露着一条缝儿,黑糊糊的,似乎正在朝外输送着寒气。
小差快步走到了C加加跟前:“哪有东西啊?”
C加加还在挥舞着手臂:“滚开!你们给我滚开!”
小差回头求助地看了看我,我走过去,狠狠捶了他一拳:“清醒一下!”
C加加朝后趔趄了一下,都要哭了:“它们在半空飞来飞去,有好多”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蛮劲儿,拦腰抱起他,大步朝东屋走去。
小差立刻跟上来。
我来到东屋,把C加加放在了炕上。Asa摘下耳机问:“他怎么了?”
四爷和小马哥也不玩牌了,纷纷围过来。
C加加靠在墙上,伸手胳膊反复地看来看去,嘟囔道:“它们在吸我的血。”
那双胳膊很细弱,上面没有任何咬痕,更没有一丝血迹。接着,他又撸起裤管查看起来,那两条腿很苍白,同样没有任何异常。
小差担忧地摸了摸C加加的脑门。
小马哥说:“这哥们玩游戏走火入魔了。”
小差对C加加说:“你躺下休息一会儿。”
C加加说:“我不困!”
小差说:“你都出现幻觉了,还说不困?”
C加加说:“我没有出现幻觉!”
小差说:“你说你被什么东西咬了,为什么我们没看见?”
C加加说:“那些吸血鬼藏在空气里!”
小差马上抓住了这个关键词:“吸血鬼?”
C加加不再说话,又举起双臂检查起来。
这个人本来表达就有问题,中了邪就更说不清楚了。
我慢慢走出东屋,来到了西屋。
空荡荡的火炕,奇形怪状的高低柜,旁边堆着我们大大小小的行李。天棚和墙壁的连接处挂着一张蜘蛛网,上面粘着一只很小的死苍蝇,不见蜘蛛的身影。
我再次走到老少间的门前,低头看了看那把锁,它是当年的著名品牌——将军不下马。我伸手碰了碰它,“哗啦”一声。
我对着玻璃上的报纸说话了:“有人吗?”
里面无声。
我说:“你好。”
里面还是无声。
我鬼使神差地又说了句:“如果你有什么冤屈就敲三下。”
等了等,里面依然无声。
突然,有什么东西碰了我的脖颈一下,我猛地转过身来,什么都没有。我伸手摸了摸,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脖颈有点麻,有点痒,接着我就听见了一阵十分微小的“嗡嗡”声,似乎有蚊虫飞了过去。
我不敢久留,快步回到了东屋。
不知道小差怎么哄的,C加加已经在炕上躺下来,很不耐烦地闭着眼睛。
我说:“东屋好像真有东西”
小差立刻看了看我:“这就是东屋。”
我说:“噢,错了,我是说西屋。”
小马哥说:“大哥,你也魔怔了?”
我瞪了他一眼,接着对小差说:“我感觉到了。”
小差说:“你具体点儿。”
我说:“刚才我进去转了一圈,好像有人碰了我的脖颈一下。”
小差说:“怎么会!”
我说:“我怀疑那个老少间有问题。你们想想,老少间都是住人的,周sir为什么要把它锁上?”
小马哥说:“你是说里面藏着个小三儿?”
我接着说:“我问过周Sir,他说那里面供着什么东西,我觉得他在骗人。”
小马哥说:“踹开它看看不就知道了。”
Asa说:“我们是来做客的,现在主人不在,你把门给踹开算怎么回事儿?”
小马哥说:“破案啊。”
小差说:“不合适。”
小马哥这才不得瑟了。
小差看了看我的眼睛,低声说:“要不你也休息一会儿吧。”
我说:“你觉得我也出现幻觉了?”
小差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我们都太累了。”
我摸了摸脖颈,说:“如果很多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了幻觉,那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
四爷突然说:“你们看C加加的胳膊怎么了?”
C加加“腾”一下就坐了起来,我们转头看去,他的左胳膊肿起了一个大包,渗出了几滴透明的液体。
C加加马上哭咧咧地喊起来:“看看看看!你们还不信!完了完了”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大波浪进来了。
小差赶紧问:“嫂子,你快来看看,C加加的胳膊怎么了?”
大波浪抓起那条胳膊看了看:“被蚊子咬的吧?”
小差说:“不是。”
大波浪说:“就是。”
然后她快步走出去,从厨房拿来了一瓶醋,打开盖子,“咕咚咕咚”浇在了C加加的伤口上,C加加夸张地叫起来。
大波浪说:“碰到那玩意算是倒霉,去年我就被咬过,只是没这么严重。”
小差说:“可是他没出去啊。”
大波浪说:“那就是你们没关门。”
小差说:“东北现在还在回暖,怎么会有蚊子?”
大波浪说:“它们一年四季都有,只是很少能遇到。”
小差说:“冬天也有?”
大波浪说:“有啊,不过那时候都穿着棉袄棉裤,它们咬不着。”
我惊讶了。由于我天生招蚊子,所以查过很多关于蚊子的资料,据我所知,气温降到10℃以下,蚊子就会大量死亡,极少的蚊子会藏在室内隐蔽的地方,尽量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类似冬眠。
小差又看了看C加加的胳膊:“我不明白,被蚊子咬了怎么会流出液体?”
大波浪说:“都这样。”接着她又说:“这些东西跟没有似的,防不胜防。”
小差马上问:“‘跟没有似的’是什么意思?”
大波浪说:“它们是透明的啊。”
我愣住了:“404的蚊子是透明的?”
大波浪也很诧异:“你们那里的蚊子不是透明的?”
我说:“不是啊。”
大波浪嘀咕了一句:“我还以为哪儿的蚊子都一样呢。”
大波浪的这个说法让我感觉到了某种恐怖,就像皇帝的新衣——你说它存在就存在,你说它不存在就不存在。那么,所谓透明的蚊子到底存不存在呢?
我依然怀疑,这两口子在老少间里圈养了某种鬼祟的脏东西,趁着西屋没人它就溜出来了,正好C加加跑进去玩手机,于是它把C加加袭击了,后来又把我袭击了。大波浪编造出“透明”的蚊子,只是为了遮掩那种脏东西。
那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呢?
我突然问大波浪:“你什么时候来404的?”
她说:“我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
Asa说:“难道这里的蚊子也变异了?”
四爷说:“那不叫变异,应该叫进化吧?”
小差显得有些紧张,她看了看C加加,轻声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C加加摇了摇头。
小马哥说:“你到底有啥感觉,说出来啊,总摇脑袋是啥意思?”
C加加并不理他,还是看着小差摇脑袋。
小差问大波浪:“你确定他不用送医院?”
大波浪说:“浇上醋应该就没事儿了。”
我接着问大波浪:“那你怎么知道它们在哪儿?”
大波浪说:“冲着阳光能看到它们的小心脏。”然后她又变得气愤起来:“我们早就跟办公大楼提过,让他们给西区换一批纱窗,这都半年了,就是没人管!”
我忽然感觉脖颈有些酸痛,伸手摸了摸,赫然一惊——我也摸到了一个大包,还湿漉漉的。我赶紧对小差说:“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脖颈怎么了?”
小差探过脑袋看了看,大声说:“你也被咬了?”
大波浪也过来看了看,立刻按住我的脖子,又给我来了个酸溜溜的“淋浴”。
四爷问我:“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我被黄蜂蜇过,应该有抗体了,没事儿。”
就在这时候,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大家朝门口看去,周sir回来了!他的表情很激动,连声说:“问到了问到了。”
四爷马上问:“在哪儿?”
周sir说:“就在石棺附近。”
我们几个人互相看了看,小差说:“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了,收拾行李,我们走。”接着她对周Sir说:“你帮了我们大忙,谢谢谢谢。”
周Sir说:“嗨,举手之劳而已。”
C加加看着小差,脑袋摇成了拨浪鼓。
小差对他说:“别怕,路上我照顾你。”
Asa也拽了拽我,小声说:“你不是说石棺那里是禁区吗?”
我说:“如果过了象鼻人给的期限,整个404都是我们的禁区。”
说完我就去拿行李了,刚刚跨进西屋门槛,双腿一软,直接就瘫在了地上
实际上我只眩晕了大概两三秒钟,后脑撞击地面的疼痛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醒。
我用手拄着地想爬起来,脚下却使不上劲儿。
我要详细描述一下这种感觉——我动了动脚趾,发现身上的每个末梢都没有问题,但就是站不起来,就像重心移到头顶的不倒翁,头重脚轻。眼前就像出了问题的电脑,不断黑屏重启。其实晕倒的感觉跟喝醉了差不多,我感觉浑身绵软无力,意识模糊,想吐却吐不出来。
不知道是谁把我扶起来了,跌跌撞撞地放在了西屋的炕上。
躺下之后,我失去了一段意识,醒来的时候,我隐约看到有人在地上走动,还听见了小差的声音,她正在跟四爷谈论我,我在发烧,其他人好像出去找药了。
发烧?
毒素导致的?
我感觉老天在捉弄我,我刚刚接近了“错”,它就把我阻止了。
我的嘴角动了一下,意识又消失了。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大家都不在了,我很渴,很想喝水,我扶着墙艰难地坐起来,情不自禁地看向了老少间,又看到了那个黑体字标题——《第二次简化字方案(草案)》,又闻到了那股香灰和中药的味道。
突然,老少间里传出了一个很开心的声音:“现在这屋里就剩下咱们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