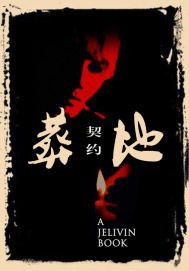老沪问:“你们西区有没有一个叫阿发的?”
周sir说:“你说发子?”
南方人喜欢在名字前加个“阿”,东北人喜欢在名字后加个“子”(发音:za),看来靠谱。
老沪说:“我只知道他叫阿发。”
周sir说:“那你说他多大,长啥样?”
老沪说:“我都不知道。”
我说:“我们跟他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我太急切了,每分每秒都有一种被人催稿的感觉,甲方还是两拨人,一拨是黑风衣三人组,一拨是象鼻人
周sir说:“好哇,你们跟我走。”
小差低声说:“我们能信任他吗?”
本来她不想让周sir听见,但离得太近了,周sir还是听见了,他毫不避讳地说:“你别担心,咱东北人敞亮,从来不记仇。”
老沪说:“走吧,我们只有找到阿发才会有线索。”
就这样,我们风忙火急地收拾了东西,稀里糊涂地跟着这个碰瓷儿的中年滚刀肉走了。
在路上,我问小差陈工是个什么样的人,小差说,他很文弱,不像个领导,更像个技术员,总体看来挺通情达理的,他承认我们所持通行证的合法性,表示不会驱逐我们,但他也提醒小差,旅游期间不能违反404的规定,等通行证到期了,必须马上离开。
大家听了,都松了一口气。
接着我问周sir:“你们为什么不搬走?”
周sir再次露出了无赖的表情:“我们在这里奉献了大好青春,突然来个命令让我们滚犊子,我们就滚犊子了?再说了,我们都不知道咋应对外面的社会。”
通过这个周sir,我们知道404大撤离的时候,对于职工和家属的善后工作是分批进行的。
由于外面的岗位有限,404高层决定先给部分职工安置工作,没有编制的职工先自谋生路,等待分配。
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国企第一次开始转型和改革,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了,除了公务员几乎没有铁饭碗了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首当其冲,下岗潮一波接一波。外面的形势如此严峻,404还能承诺给这些职工编制,真是良心企业了。
相对来说,以周sir为首的一群人就有点恩将仇报了。一听说暂时没有编制,注意——只是暂时,这些人马上不乐意了,死活不肯走,就算断水断电都没用。其他人都离开之后,偌大的404都成了这些人的家,在这里住几天,在那里住几天,也算逍遥自在。
Asa问:“那政府最后给你们安排编制了没有?”
周sir说:“安排了,可那都是三年以后的事了,我们出去之后肯定跟不上时代了。”
Asa接着问:“你出去过吗?没出去过怎么知道自己适应不了?”
周sir说:“咋没出去过呢,有个老梁,撤离前是404打更的,他出去没几个月就回来了,大家听说他是从404出去的,都躲着他,怕他身上有辐射现在他就住在西区。”
据周sir说,404每届领导班子都会来做他们的工作,可他们油盐不进,软硬不吃,没办法,上级只能把西区留给他们当做善后住宅,每个月定期派人送来粮食和蔬菜,还特意给他们扯了电线。到了现在,领导班子都换了三届了,这些西区住户依然屹立不倒
Asa说:“你们可给政府添了不少堵。”
周sir说:“你咋不说我们给国家添了多少砖加了多少瓦呢?”
我问他:“你们西区的环境怎么样?”
周sir得意起来:“我们有电有水,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你们干脆住我家吧,我家老大了。”
没想到这个周sir还挺仗义。
小差也不客气:“好哇,省得我们整天跟一群野人似的风餐露宿了,谢谢。”然后她看了看周sir的腰:“你的腰”
周sir 竟然有些不好意思:“都一家人了,还说那干啥。”
接着他就嘿嘿嘿地笑起来,竟然笑出了东北人的纯朴。
我接着问:“你们平时能出去吗?”
周sir说:“出去?去哪儿?”
我说:“外面啊。”
周sir说:“当然了,有个邻居几个月前就出去过,又回来了。外面没啥好的,我们出去之后啥也不懂,还不如留在这儿,不用上班,还有人管吃管喝。”
小马哥说:“哥们,404又没人,你想碰瓷儿得出去才有生意啊。”
周sir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有些无耻:“隔三差五就有人来旅游啊,一般都是团队,摄协拍照的,美协画画的,摄制组取景的我们这些人没有工资,所以就顺便讹讹他们增加点收入。”
我继续问:“你见没见过一个搞直播的?”
周sir说:“啥叫直播?”
我说:“就是拍视频的。”
周sir说:“来404的人谁不拍照谁不录像啊。”
当我没问。
Asa朝天上看了看,问:“周sir,西区应该在西边,我们怎么朝东走呢?”
周sir说:“西区在东边啊。”
我想了想才明白,旅馆的位置大概在左城区的最西侧,所以“西区”在东边,这就像站在南极点,朝哪儿走都是北。
周sir说:“你们不用管,跟我走就行了。”
走着走着,周sir和小马哥走到了前头,估计交流起碰瓷儿的经验了。
Asa的表情有些担忧,他小声对我说:“现在是我们人多,一会儿就是他们人多了”
我说:“他好像很诚恳,应该没问题。”
四爷把小差拽到了一边,根本不在乎C加加能不能听见,直通通地就问了:“小差,你这男朋友是从哪儿淘的?咸鱼上吗?”
小差说:“怎么了?”
四爷说:“刚才你都被人欺负了,他一个屁都不放。”
小差说:“他不会吵架。”
四爷说:“他可以不会吵架,但他应该会打架啊。”
小差说:“那就更不是他的强项了。”
四爷说:“换了我早就开骂了。”
小差笑了笑:“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等到了他的专业领域,你才会发现他的魅力。”
四爷说:“我的天,他还魅力?”说到这儿她又点了点头:“我算知道了,这就叫王八瞅绿豆——对上眼了。”
这段对话C加加都听见了,但他好像根本不在乎,甚至抻了个懒腰。
周sir在前面大声说:“你们想吃点啥?我让我媳妇给你们做。小马哥说了,他想吃小鸡炖蘑菇。”
老沪说:“你老婆不给我们吃闭门羹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拐进了一条芦苇荡中间的小路,路的尽头是一片果林,花瓣掉了一地,这是404里难得的彩色。
大家都走到了一起。
C加加凑近小差说了句什么,小差问周sir:“你们那里有信号吗?”
周sir说:“我们有信号枪。”
我有点诧异:“信号枪?”
周sir说:“这里没有公安局,谁保护我们?我们得自治,得联防,万一来了歹徒,我们一放信号枪,就算有人不在西区,也会立刻赶回来帮忙。”
小差说:“我是问你,你们那里能上网吗?”
周sir说:“那上不了,我们的座机只能打到办公大楼。”
我们穿过果林,周sir朝前指了指:“前面就到了。”
前面果然出现了几排平房,大概有几十栋,像个村庄,我看到了很多人影在晃动,一些人家的院子里还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颇有些生活的样子。
周sir说:“你们慢慢走,我先回去跟我媳妇说一声。记着,把头那个房子就是我家。”
说完,他就骑上了自行车先走了。
大概10分钟之后,我们慢悠悠地走进了这片住宅区,我敏感地发现,刚才那些晃动的人影都不见了,他们好像很怕生人,纷纷躲进了屋里。
周sir家有个小园子,围着葵花杆夹成的障子。我姥姥家就有一个这样的小园子,里面种着西红柿,还有甜杆儿,四周长着野生的黑悠悠,我离开东北之后再没见过那种小果子,我觉得它应该是东北的特产。不过现在季节还早,周Sir家的小园子只有黑土。
他家旁边立着一根又粗又矮的电线杆,上面装着变压器,电闸箱都黑了,乱七八糟的电线拉进了每家每户。
一个烫着大波浪卷的女人走出来,把我们迎进了屋子。她长得土俊土俊的,屁股特别大,她热情地说:“我是周sir的媳妇,你们管我叫嫂子就行了。”
这是典型的东北人家户型,从正门进去是个厨房,有一个大灶台,左右各有一个房间,俗称东西屋。
我们走进了西屋。有火炕,有老式的高低柜,有靠边站(东北的一种饭桌)。所有电器上都有一朵“大花”——电视上罩着牡丹防尘罩,冰箱上罩着月季防尘罩,电风扇上罩着玫瑰防尘罩。墙上挂着镜子和相框,相框里贴着密匝匝的照片,进屋之后,所有人都凑上去看了看,这是个本能的习惯,可能来自人类最古老的窥视欲。那些照片上都是陌生人,有脸色古板的老头,有穿着花棉袄的小姑娘,有结婚照,有旅游照
这个房间还有个套间,在东北叫“老少间”,不过门上挂着一个老式的锁头。一般说来,老少间是给老人或者孩子住的,里面也有炕,但我觉得周Sir两口子应该把它改成了储物间,不然不会锁上。
Asa发现了插线板,马上问:“周Sir,我们可以在你们充充电吗?”
周Sir说:“充电又不花钱,你们充呗。外道!”
Asa说:“谢谢谢谢。”
接着,我们马上把所有电子设备都掏出来,纷纷插在了充电板上,就像一群饿疯了的蚊子叮在了一条肉乎乎的胳膊上。
小马哥跳上火炕,熟练地盘着腿坐下来:“累死我了。”
四爷也脱了鞋,好奇地爬上去,坐到了小马哥旁边。
老沪说:“周sir,麻烦你看看那个发子在不在?”
周sir马上对大波浪说:“你去把许发子喊过来。”
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这个名字越来越不像了,老沪找的是“阿发”,最初周sir说西区有个发子,现在又变成了许发子
大波浪出去之后很快就回来了,她说:“他不在。”
老沪立刻问:“去哪儿了?”
大波浪说:“送去办公大楼抢救了,说是要不行了。”
老沪有些疑惑:“他怎么了?”
大波浪说:“年纪大了,全身都是病。”
老沪又问:“他多大年纪?”
大波浪看了看周sir:“有90了吧?”
周sir问老沪:“不是你要找的人?”
老沪失望地摇了摇头:“肯定不是。这里还有叫发子的吗?”
周sir看了看大波浪,然后说:“还有个王发财。”
越来越不靠谱了。
我看了看时间,象鼻人给我们的倒计时还剩下21个小时。
周sir说:“不着急,回头慢慢找。你们先坐着,我去做饭了。”
接着他就跟大波浪出去了。
大家开始小声聊天。
小差说:“反正这里都是本地人,我们吃完饭再出去打听打听吧。”
老沪把声音压低了:“来到这个西区之后,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周Sir两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