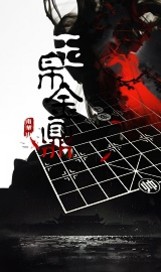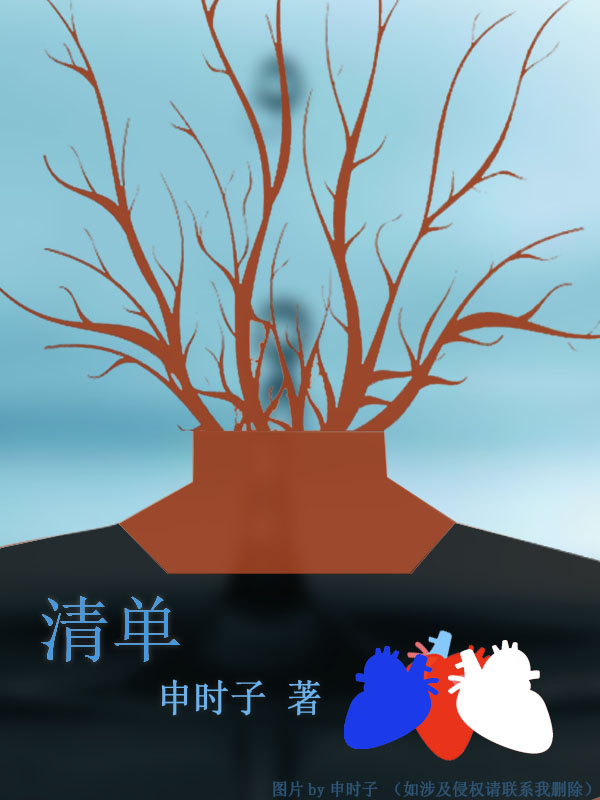Asa愣了一下:“对啊,我怎么不买个带进来”
我说:“办公大楼肯定有这种东西。”
Asa说:“就算他们有,你敢去借吗?”
我说:“那就偷呗。”
Asa说:“你可别拖我下水啊,本来我们就是违法闯入,要是再加上个偷盗的罪名,那就别想出去了。”
我说:“这里曾经是个高精尖的单位,明天我们先出去找找,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能找到一个。”
Asa说:“金属探测仪分三种,电磁、X射线和微波,我们找到类似的仪器就可以。”
我说:“老天保佑吧。”
随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说话,很快Asa就睡着了。
我一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忽然想起一件事,在当时似乎很乌龙,但是现在看起来却更像某种谶语——
那是去年的冬末春初,我还没有深陷债务危机。我去上班,发现公司的停车位都停满了,只好把车停在了马路对面的施工工地旁边,为了不耽误交通,我还特意靠近了围墙。
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初春的北京风很大,我裹了裹大衣,从写字楼走到工地,借着塔吊的灯,我看见我的车身上被喷了三个数字——404。
那里离798艺术区很近,很多吊儿郎当的青年,扎着脏辫儿,踏着滑板,没准就是他们干的。
我发现,我那辆车左侧的墙上喷着123,右侧的墙上喷着321。看来,他们想喷的是123404321,在数学上这叫回文数,我只知道跟编程有关系,但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关系,由于我的车挡住了墙,他们就把中间三个数涂到了我的车上。这帮青年的领地意识比公狗都强。
喷我可以,我认怂;喷车不行,得赔钱。
举头三尺有监控,找个嫌疑人比找个女朋友还简单。我抬头看了看,果然,一个工地的摄像头正好对着我。
没想到我进入工地保安室之后遇到了阻碍,一脸冷漠的保安大爷对我说,没有公安机关介入,他不会给任何人查看摄像资料。
没办法,我只好开车去了交警队。
警官要去了我的行驶证和驾驶证,一边听我讲述情况,一边在电脑上敲打着。
他突然打断了我:“你说你把车停在哪儿了?”
我说:“我公司对面有个工地,就在咱交警队旁边”
他说:“我记着那条路上没有停车位啊?”
我一下就卡住了。
就这样,我不但没找到那个喷我车的人,还收到了一张罚单现在想想,那应该是老天给我喷的,我不可能跟老天要赔偿。
但是
但是我进入404之后,在所有企事业单位的门匾上都没有看到过这组数字,它就像刻在了这座荒弃之城的血液里,基因里,灵魂里并不外露。
后来我终于睡着了,还做了个梦,内容记不太清了,大概是我梳着大背头,手上拿着一根雪茄,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街上,四爷扛着一麻袋的“错”,紧紧跟在我身后,她好像变成了我的美女跟班。我见到了黑风衣三人组,让四爷把“错”统统倒在地上,然后用雪茄在那个张本利的头上弹了弹烟灰,牛气冲天地说:随便挑吧!
突然,我被什么声音给吵醒了,竖起耳朵听了听,四周一片死寂,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自从进入404之后,或者说我被那些亡命徒威胁之后,变得神魂颠倒的,于是又睡了过去。
张本利笑起来。
梦接上了。
我有些诧异,他不跪下叫爹就算了,还笑?
过了会儿,我感觉不对劲了,回头看了看,地上只是一堆碎砖头
我正不知道如何收场呢,谢天谢地,我又被那个声音给吵醒了,这次我听清了,好像有一列火车从地下经过,整栋房子都摇晃起来。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我记得一个乌克兰专家在他的著作《Chernobyl: Historyof a Tragedy》中这样描述过核事故的现场——那些在操作室的人突然听到地下传来了一个恐怖的声音,他们以为地震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导致的地震!
想到这儿,我忽然开始担心起这座空城的安全指数了。
那座不起眼的哨卡,那座像待拆建筑一样的办公大楼,那座长满青苔的石棺404荒了这么多年,要是真的出了什么泄漏事故,它们靠谱吗?
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发生在1986年,当时,我们这些人都还没有出生,我只对2011年日本福岛那场核电站事故有些印象,当时我在白城读书,最深的印象就是每个人都在说:摄入碘,防辐射。一夜之间,全城超市的盐都被抢光了,很多人都没看清那些盐到底是加碘盐还是无碘盐。我妈跟单位同事借了一辆皮卡,也抢了很多盐回家,就像饥荒年代抢大米一样。她有个男同事更惜命,直接买张机票跑到海南去了。
虽然福岛的核尘埃最终并没有飘到东北来,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眼下,我置身于辐射读数忽大忽小的404,那种恐惧又出现了。
屋子里黑黢黢的,我打开手机照了照,Asa的睡袋是空的。
我正要下床去,他已经回来了,对我轻轻“嘘”了一声。
我低声问他:“你去哪儿了?”
Asa说:“有问题。”
我用手机在他脸上晃了晃:“到底怎么了?”
他说:“你先把手电筒关了。”
我把手机扣在了床上,他这才说:“刚才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然后就想上厕所,结果看见一个人偷偷溜出去了。”
我说:“谁?”
Asa说:“小马哥。”
我说:“他看见你了吗?”
Asa摇了摇头,接着说:“快半个钟头了,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想了想说:“这些人肯定都是来找‘错’的。”
Asa说:“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四爷是怎么知道的?”
他就不说话了,过了会儿他问我:“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装作不知道,睡觉。”
Asa很听话地钻进了睡袋。我看了下时间,凌晨三点半。
我闭上眼睛,捕捉着外面的动静。就在我快睡着的时候,终于听见了轻微的脚步声,之后是房门合上的声音——小马哥回来了。
天亮了。
我起床之后,看见各个房间的门都敞开着,Asa正在圆厅里吃东西,老沪则站在走廊的窗前眺望远方,小差在房间里练瑜伽,C加加坐在角落里玩着手机。四爷和小马哥不见了。
至此,我已经在404度过了两天两夜。今天是谷雨前三天,如果你翻开日历,会看见这样四个字——诸事不宜。
我问Asa:“那两位呢?”
Asa说:“四爷说她要出去走走,小马哥陪她去了。”
我忽然有点担心四爷。
Asa四处看了看,把声音压低了:“刚才我试探了一下小马哥,他说他昨天夜里哪里都没去。”
我说:“看看,他肯定有鬼。”
小差走了出来,她一边擦汗一边笑着问我:“那个四爷是你女朋友吗?”
我含含糊糊地说:“差不多吧。”
Asa惊愕地看了看我。
我也觉得自己有点无耻。
小差说:“那丫头挺好的。一会儿你俩怎么安排?”
我说:“我们打算出去拍点照片。”
小差说:“不一起走吗?”
我说:“大家的兴趣点不一样,还是各玩各的吧。”
小差说:“也好。”
我和Asa离开旅社的时候,太阳刚刚从废弃的楼顶露出脑袋。
旅社四周的建筑物乏善可陈,我把目光投向了远方,视野很开阔,办公大楼和石棺远远对望,看上去差不多一样大,我甚至还看到了位于它们之间的那棵古“树祖宗”
我们在外面转悠了很长时间,希望遇到某个研究单位或者某个特殊车间,找到他们丢弃的金属探测仪,然而,一路上我们只看到了商店、饭馆、台球室之类,基本没看到什么跟原子能有关的工业痕迹,虽然也有几个废弃的厂子,但那只是一些毛纺厂,罐头厂,家具厂
走着走着,我们看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医院。
它坐落在街边,院墙都是铁栏杆,只有一栋主楼,我估计当年把门诊和住院部都放在一起了。楼顶的红十字已经褪色了,但还是很醒目。
Asa说:“我们进去看看。”
我说:“这里又没有金属探测仪。”
Asa说:“这里有MRI。”
我说:“MRI是什么东西?”
Asa说:“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核磁共振。”
我说:“那跟金属探测仪有什么关系?”
Asa说:“你知道做MRI的时候身上不能有任何金属吧?”
我想起了一部电影,类似《死神来了》,有个人挂着金属的心脏起搏器去做MRI,结果他的心脏和核磁共振仪器一起炸了。
Asa又说:“我陪我爷爷去做MRI的时候,他就接受了金属检测,比机场安检都严格。”
我点点头:“有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