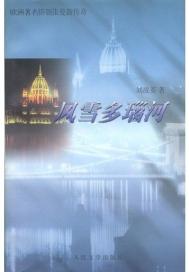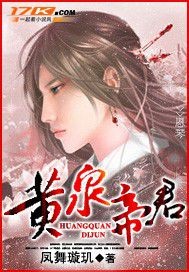尘埃落定之后,我探头朝里看了看,这条隧道跟我置身的通道有两米多的落差,我需要跳下去。隧道中间长着一棵很粗的树,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毫无疑问,它就是地面上的那棵“树祖宗”了,我看到的植物正是它穿墙而过的一个枝杈。
我朝上看去,“树祖宗”被隧道顶部的水泥禁锢着。从这个地下空间到地面之上至少有几十米土层,它竟然长出去了。我又朝下看了看,它的根部也被水泥地面禁锢着——这应该只是它的一截树干,就像隧道中的一根柱子,顶天立地。
我想起了一句话:这个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下都埋藏着恢弘的秘密。
它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地心?
这究竟是一棵什么树,生命力竟然如此强大?
槐树?我马上想到“槐”里藏着一个鬼。
我看过一部片子:一位裸女躺在原始丛林中,来探险的男性没人能抵住她的诱惑,纷纷和她发生关系,然后瞬间苍老,死掉。原来,这个裸女是一棵古树的化身,她就靠这种方式汲取养分,使自己枝繁叶茂
一幅画面迅速在我脑海中形成了:在隧道中,这棵“树祖宗”时而是树,时而是人。变成人的时候,她偶尔挂在隧道顶部,偶尔藏在地缝中,观察着每一个进入地下的人,他们在赶路,他们在休息,他们在涉水,他们在攀岩接着,这些人接连失踪,每少一个人,这棵“树祖宗”就长高几寸
我关掉手电筒,从窟窿跳下去,开始观察这条隧道。
它很宽阔,有三四层楼那么高,远远超过了国家对一二级隧道高度的要求。隧道中间每隔一段就有一根粗壮的承重柱,把隧道一分为二,变成了双向车道,每条车道可以并排行驶两辆大卡车。
隧道顶部镶嵌着两排灯组,亮着耀眼的白光。除此之外,隧道墙壁上安装着风扇,正在隆隆运转。
接着我走到了那棵“树祖宗”跟前,仔细观察起它来。
植物必须通过光合作用才能生长,在如此阴暗的地下,它为什么生长得这么茂盛?没有阳光照射,这些枝杈也不分阳面和阴面,长势对称。我回忆了一下,它的地面上的那部分好像也没有阳面和阴面。
我冒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整个地下空间都是围绕这棵树建造的,目的就是挖掘、探索这棵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神奇之树,而我所见到的一切设施,都是为这个巨大工程服务的
远处传来了车声,我赶紧躲在了一根承重柱的背后。我要看看这是一辆什么车,以及什么人在驾驶。
大概几分钟之后这辆车才开过来,它是一辆天蓝色的大卡车,什么都没装,它并没有注意到隧道上出现了一个窟窿,也丝毫不关注那棵“树祖宗”,呼啸着就开过去了,我根本没看到驾驶员的脸。
地下的“树祖宗”——或者说“树祖宗”的地下部分也伸出了很多枝杈,长满了叶子,只是上面蒙着尘土,看上去没那么绿了。我如法炮制,再次用它的叶子涂抹了全身,又揪了很多叶子塞进了包里,然后大步朝着隧道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我闻到了一股冷清的硫磺味,好像刚刚放过鞭炮似的。这个味道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地下会不会有炸药之类的东西呢?如果有,那也许会成为我的武器,起码是威胁敌人的筹码。尽管我至此都不知道敌人是谁。
隧道两旁的墙壁上有一些斑驳的标语——
“兴核强国,服务社会”。
“两弹一星精神”。
“打破霸权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
恢复触觉之后,我就像卸掉了绑在腿上的沙袋,简直是健步如飞。走出大概一公里的样子,我看到隧道旁有个凹进去的空间,挂着荧光电话标志,那是紧急停车带。我停下来,探头朝里看去,果然看到了一辆白色皮卡,车牌上写着:林 2B21。车后斗的围栏锁被打开了,三块围栏软塌塌地垂向了地面,车上坐着两个留守人员,他们都穿着灰色制服,外面套着反光马甲,上面写着:东北林区。此时他们正在打盹儿。
我一时不知道该向他们求助还是该躲开他们,正犹豫着,突然有人从我背后说话了:“谁?”
我猛一回头,原来是那个在办公大楼跟光头打乒乓球的板寸,他正在系裤子,应该是刚刚解手回来。
车上那两个人也被惊醒了,他们迅速站起来,其中一个居然举起了一杆猎枪,另一个则抄起了一根甩棍。拿猎枪的那个人好像扭伤了,他用铁皮自制了一个夹板夹住了胳膊,又用脏兮兮的尼龙绳挂在了脖子上。
我赶紧说:“我我我。”
板寸说:“你别动。”
我就乖乖地举起了两只手。
板寸走过来看了看我的脸,嘀咕了一句:“是你啊吓我一哆嗦。你咋跑这儿来了?”
他的口气一下就让我轻松了,我把手放下来,说:“别提了。”
另外那两个人见我跟板寸认识,又坐了下去。
接着,我把我来到地下之后的事儿讲了一遍。当我说到光头中枪的时候,他狠狠地咬了咬牙,看得出来他很愤怒。
我讲完之后,他说:“我看见你们一个女同伴被扎卡的人抓去了。”
我一惊,马上问:“四爷还是小差?”
板寸说:“我又不知道她们叫啥。”
我说:“好看的那个还是不好看的那个?”
板寸说:“不好看的那个。”
我松了一口气,但马上想到,也许只有我才觉得四爷比小差好看,在一般人眼中,一定会觉得小差更好看。另外,小差跟老沪在一起,她要是被抓了,老沪肯定也被抓了,我离开之后,只有四爷落单了
我又问:“高的那个还是矮的那个?”
板寸想了想才说:“高的那个。”
果然是四爷
我的心里一阵抽搐,突然问板寸:“陈工在哪儿?”
他说:“在未开发区,你要干啥?”
我说:“被抓走的那是我女朋友,我得去求救啊。未开发区在哪儿?”
他说:“那还真不好说,离这儿至少四五里。”
我马上在地上画了个“Y”字,然后抬着脸对板寸说:“你看,左边是我们的地盘,右边是扎卡的地盘,上面就是未开发区,对吧?你就告诉我,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我就知道怎么走了。”
他一下就不乐意了:“哪里是扎卡的地盘?都是国家的地盘。”
我赶紧说:“是是是,我是说,他们经常在那里出没。”
板寸指了指“Y”字下面的那一竖:“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抬头朝隧道深处看了看,再朝前走就是“Y”字的中心点了。
板寸又指了指上面那个三角区偏左侧的位置:“陈工在这里。”
我说:“既然那里没开发,陈工去那里干什么?”
板寸说:“今天,陈工把留守人员都带到了地下,我们先在左侧三角区待命,天黑之后,大部分象鼻人都去了地面,我们全部去了右侧三角区,企图捣毁他们的老巢,却被扎卡的人打退了,虽然他们只留了几个看家的,但都是亡命之徒,而且人手一支枪,而我们这些人只是厂里的职工,根本不会打仗,没办法,陈工就让我们先撤到未开发区暂时休整了。”
说到这儿,板寸气得咬牙切齿:“等抓到这帮瘪犊子,我把他们都敲(阉割,特指猪)了。”
我看了看那辆皮卡,问板寸:“你们的车是从哪儿开进来的?”
他愣了愣才说:“这就是地下的车啊。”
我说:“我不明白。”
他说:“在地下空间封闭之前这些车就开进来了,从此就成了地下专用车辆。”
我说:“噢,我懂了,只要把油料运下来就行了。”
他说:“不用,地下有加油站。”
我觉得自己太笨了,地上加油站的储油罐也是埋在地下的,拽出一根管子就可以加油了啊。
我说:“你们怎么突然想起抓这些象鼻人了?”
板寸说:“象鼻人?”
我说:“就是扎卡那伙人。”
板寸说:“噢,这是陈工决定的。”
我说:“我就是问,陈工为什么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偏偏这个时候要抓他们?”
板寸说:“这伙人太猖獗了,忍不了了呗。前两天他们去办公大楼偷粮食,竟然杀了我们一个打更的,简直无法无天了。”
我又问他:“我看见隧道那头有个通道,里面忽冷忽热的,那是什么地方啊?”
板寸变得严肃起来:“这是机密。”接着他马上盯住了我:“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板寸惊讶了:“那里早就封闭了啊,只有防火办的人定期去巡查,你是咋进去的?”
我说:“我从一个池子游过去的。”
板寸说:“你要是见了陈工可千万别说你去了那里,否则你会有大麻烦。”
我赶紧点了点头:“谢谢,那我去找他了啊。”
这时候远远传来了车声,我转头看去,一辆“品”字头的蓝色卡车开过来。
板寸说:“你走过去太远了,正好老四过来了,你搭他的车。”
接着,板寸就伸手拦住了这辆卡车,大声说:“老四,你把这小伙子带上,他要去找陈工。”
老四是个中年男人,胖乎乎的,他对我说:“上来吧。”
我告别板寸,爬上了卡车,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卡车开动之后,我问老四:“这车上拉的什么啊?”
他神秘兮兮地说:“汽油和火药。”
我又问:“干什么用的?”
老四说:“把扎卡那伙人炸上天。”
我说:“你们怎么不叫武警进来呢?”
老四有些不屑:“那是用高射炮打蚊子,没必要。”
我不这么看。象鼻人已经不仅仅是涉黑团伙了,他们简直是一支武装。我就纳闷了,陈工为什么坚持要自己解决呢?我怀疑他了解“错”的存在,他不想被国家发现,所以才不想上报请求支援。
皮卡沿着隧道开出了两三公里,两旁的墙壁上出现了烟熏的痕迹,我甚至看到了一些弹洞,道路也变得坑坑洼洼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山脉中,毒枭们为了贩毒建造了一条私人隧道,两国警方经常和毒枭在隧道内发生交火,估计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坐在颠颠晃晃的车上,开始思考眼前的难题——陈工会为了我改变计划,立马派人去搭救四爷吗?很可能不会。如果他不帮忙,我该怎么办?
终于,我们来到了一个类似转盘的地方,这应该就是“Y”字的中心了。隧道分岔了,右侧的隧道没有灯,很窄,也就一辆车那么宽,看着就像一条死胡同。左侧的隧道稍宽一些,亮着幽暗的灯,墙面和地面上有很多水渍。
老四朝左边开去。
我注意到,这个转盘的中间堆了很多瓶瓶罐罐,像个小山,好像被烧过,黑黢黢的。
我问:“那些瓶瓶罐罐是干什么的?”
老四说:“扎卡把自己当成林则徐了。他贩毒,但坚决不让手下人吸毒,这里就是他销烟的地方。”
想不到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还有自己的底线。
我突然说:“你就在这儿把我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