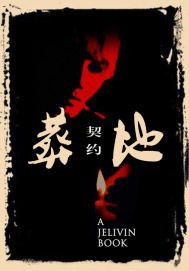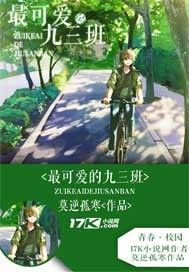我停下来,使劲摇了摇脑袋,那些人倏地不见了。
幻觉又出现了。
难道,这个画面在指引我?
我快步跑过去,来到了那个户外楼梯下,抬头看了看,楼梯很窄,它一波三折地伸向了楼顶。我有些犹豫,刚才那画面是几十年前的,而这个铁艺楼梯一直在户外被风吹雨淋,能承住我的重量吗?
我必须上去。
接着我就朝上爬了,刚开始它还很稳固,但是随着我越爬越高,它开始晃悠起来,发出了“咯吱咯吱”的恐怖声音,我就像逃一样“噌噌噌”地爬到了楼顶,一下瘫坐在地上,腿肚子就抽筋了。
我匆匆揉巴了几下,然后四下看了看,并没有看到任何人。楼顶铺着黑糊糊的油毡纸,中间矗立着那座彻夜不熄的探照灯,它的样子很像个炮台,此刻它并没有打开。最边缘有个混凝土建成的水塔,上面布满了苔藓。
我站起来走过去,围着它转了一圈,没有任何入口。
那些人上来干什么?维护这个探照灯?
这里是404最高的建筑了,四周没有遮挡,风很大,朝远处望去,一片暮色苍茫,越过高高矮矮的房屋,能看一片片的芦苇、草甸和湿地。
我再次盯住了那个水塔。不远处扔着一架梯子,我把它搬过来斜靠在水塔上,然后就爬了上去,
没想到,水塔顶部竟然是个入口,我看到了台阶!
这个入口并没有藏在地面上的某个隐蔽角落里,而是藏在了楼顶,牛。
我马上想起了我爸日记里的那句话——核城之所以被称为核城,那是因为它藏着更深的“核”。办公大楼是404的心脏,现在我在心脏里发现了一条秘密通道,它通往心脏的心脏,看来,这下面很可能藏着404最大的秘密。
我正准备进入,突然在离我最近的台阶上看到了一只扣子,我把它捡起来,情不自禁地在衣服上比了比,不大不小,一模一样。
现在,我必须要详细地介绍一下我的扣子了——它们是浅红色的,或者叫绛紫色,或者叫蔷薇色,圆形,但一侧就像被薄薄地切了一刀,正中心有三个扣眼
有一个问题永远都不会有答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扣子?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无数的网店中选择了其中一家,购买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某个服装厂生产的,他们的扣子来自批发市场的某个摊位,那个摊位又是从某个纽扣厂进的货,那个纽扣厂生产的纽扣又有无数种
怎么可能这么巧,我刚刚在西区掉落了一颗扣子,然后就在办公大楼顶部的台阶上捡到了一颗同样的扣子我忽然害怕起来,就像甩掉那条洋辣子一样,一扬手就把这颗扣子扔掉了,它顺着台阶滚下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接着,我从背包里掏出手电筒打开,正要顺着台阶爬下去,突然下面传出了杂沓的脚步声,他们正在跑上来。
我赶紧朝后退了几步。
首先,我看到了那个“董庆贵”,我愣住了。这次他没有穿军装,只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一条牛仔裤,一双很不般配的老北京黑色圆口布鞋。老实说,不如他穿那身美式军装好看,差远了。
他看到我之后,也愣住了。
他身后的人陆续钻出来,我看到了那个“李志高”,或者叫他“李志远”,看到了那个“宋德南”,或者叫他“宋德北”,看到了那个姓肖的观众,看到了那个“机枪手”,看到了那个“爆破手”,看到了那个“排长”,或者叫他“通讯兵”,他旁边站着一个人,两个人长的简直一模一样
所有这些人都穿着便装。
看到我之后,他们的表情都怔怔的,只有一个人朝其他人身后躲了躲,他是那个姓肖的观众。
我们都戳在楼顶的平台上,似乎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404的风浩浩荡荡。
我看了看那个“董庆贵”,终于张口了:“这么快就不替老蒋卖命了?”
“董庆贵”皱了皱眉:“什么老蒋?”
我说:“别废话了,你把那个女孩弄到哪儿去了?”
“董庆贵”说:“什么女孩?”
我说:“你不要装糊涂了,几天前你扮演国民党第五师第三旅第四团第一营连副,把跟我一起的那个女孩抓走了。”
“董庆贵”说:“我是‘解放军’一营三连二排三班战士,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指了指其他人,说:“他们我记不住就算了,当时你跟我说了那么多话,我会不记得你?”
“董庆贵”眯起眼睛审视了我一下,突然说:“你就是在红都剧院偷听我们军情的那个人?”
我说:“你快拉倒吧。”
“董庆贵”回头朝那对双胞胎说:“排长,这个可疑分子又出现了,怎么处置?请指示。”也不知道他在对谁说。
双胞胎当中的一个朝前走过来,他看了看,很威严地说:“你如果再跟踪我们,那我们真就认为你是国民党的特务了。”
我说:“好奇怪啊,你们把演戏的服装都脱了,怎么还从戏里走不出来呢?”
“排长”说:“没错儿,我们已经光荣退伍了,但依然还是预备役,就算过了预备役,我们也是民兵。只要有人威胁到我国领土安全,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你拿下。”
我不该再跟这些“演员”纠缠下去的,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只能从他们口中问出四爷的去向。
我突然对这个“排长”说:“如果这不是在演戏,那你已经牺牲了啊,你的英魂还在地下剧院里跟我说过话。”接着我又指了指另一个双胞胎:“还有你,你也阵亡了,我还用三轮车免费把你从那个饲料加工厂拉回了红都剧院。你们怎么都死而复活了啊?”
“董庆贵”说话了:“我们‘排长’那是假死,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枪弹。”
我看了看另一个双胞胎:“你也是假死?”
那个双胞胎有些不解:“我是一营三连二排三班战士郝昌江,我在红都剧院的战斗中亲手消灭了三名敌人,都没有挂彩,怎么会牺牲呢?”
噢,对,他并没有承认他是“国民党”。但我至少知道了,他是“郝昌江”,而扮演“排长”的这位是“郝昌河”。
我说:“我时间很紧迫,不玩了,我知道你们在演戏,不会把那个女孩怎么样,但你们必须告诉我,她去哪儿了?”
有个人凑到“董庆贵”耳边低低说了句什么,“董庆贵”想了想才问我:“敌人把她抓走之后,从哪个方向逃窜的?”
我说:“就是你抓走的,你问我?”
“董庆贵”说:“你要是这么固执己见,那我们就没法帮你了。”
我指了指跟他耳语的那个人:“你当‘连副’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你耳边嘀嘀咕咕,还装。”
“董庆贵”看了看那位“排长”,低声说:“他应该不是特务,他脑子有问题。”
“排长”看着我,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我突然盯住了那个姓肖的观众,他就像小孩一样,已经把自己的整张脸都挡住了。我说:“那位观众,你好吗?”
他并没有露出脸来。
我对“排长”说:“他真是你们的热心观众,大周末的早上就去看你们的舞台剧,还被放鸽子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他退票,3毛钱呢。”
“排长”说:“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他是我们排的文书,出了名的笔杆子。”
我接着对那个姓肖的观众说:“你不是要带我去见赵海边一家吗?怎么半途跳车跑了?连自行车都不要了。我跟你说话实说吧,赵海边是我爷爷,我很奇怪,他早就去世了,你怎么认识他?”
实际上不需要他回答,我“呼啦”一下全懂了——
我爷爷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爷爷家的住址当时都是我给人家提供的。他只是顺杆爬而已,不但说他认识,还说他跟我爷爷家只隔了一栋楼。
姓肖的观众终于闪了出来,不知道他怎么给自己打的气,他的表情竟然很淡定,他走到我跟前,轻声说:“你在跟我说话吗?”
我说:“是啊,你怎么也当上‘演员’了?”
他马上更正我:“我是一营三连二排一班战士徐福。”
我想起来了,他在获奖证书的名单上是第一位。
我说:“好吧,你怎么又入伍了?”
他说:“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啊,我1967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服役12年了。”
我情不自禁地四下看了看,404的废墟尽在眼底。我必须用现实场景让自己清醒清醒,不然又被他们催眠了。
我不得不拿出杀手锏了:“我看到你们的获奖证书了。”
这个“徐福”愣了愣,我说:“恭喜你们,你们的表演在未来获得了集体金鸡报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