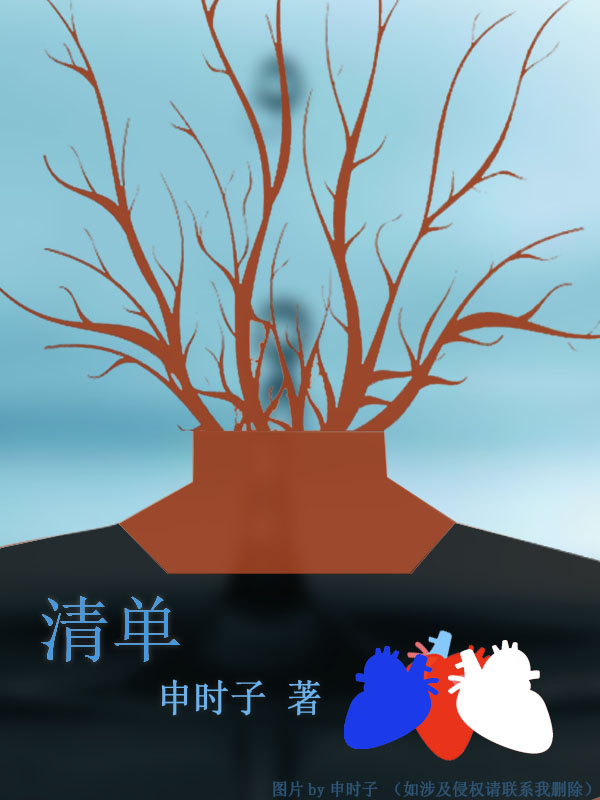我从飞机上醒了。
“舱门关闭,各客舱乘务员请就位。”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椅背,窗外的通化三源浦机场渐渐变小
我总觉得我忘了什么事儿,却怎么都想不起来,算了,想点别的吧。
通化机场为什么要叫三源浦呢?进而想到了哈尔滨的太平机场和乌鲁木齐的地窝堡机场,它们基本是全国最难听的两个机场名了。飞机的意境应该跟蓝天、白云、羽毛、翅膀相关,而此二者一个太平,一个地窝,生生把飞机拽了下来。
东北有三个“二哥”——黑B齐齐哈尔市,吉B吉林市,辽B大连市,它们的机场名分别叫:NDG齐齐哈尔三家子国际机场,JIL吉林省二台子国际机场,DLC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都这名了,还国际啥啊国际,就是仨村头嗑瓜子的。
相比之下,辽宁省一些机场还算中规中矩:沈阳的桃仙机场,营口的兰旗机场,丹东的浪头机场都还能听。
再往南,机场名普遍好听,济南的遥墙,青岛的流亭可能是因为离蓬莱比较近,连机场的名字都有一股仙气。
昆明、广州、福州、海口、杭州、武汉,他们的机场分别叫长水、白云、长乐、美兰、萧山、天河,这些名字很像仙侠小说的男女主角。
“滴——”一声,安全带指示灯熄灭,飞机进入平飞状态。空姐推着饮料车开始为乘客服务了,我打开手机,连上Wifi,安全感倍增。
到底忘了什么事呢?我好像应该联系一个什么人,但我拿出手机,又不知道该联系谁。百无聊赖,我打开了一款交友软件,老实说,这软件就是用来约P的,但我很久都没用过了,已经落后了三个版本。
更新之后,我发现一位好友就离我0.1km——很显然,她就在这架飞机上!她在软件上的名字叫小绝。
我翻看了一下之前跟她的聊天记录,她是个空乘,一个月之前匹配上的,当时我们交谈甚欢,互留了联系方式,甚至准备要见面了。
空姐嘛,盘儿亮条儿顺是肯定的,一个职业就可以大概勾画出她的长相和气质。相比普通人,她们多多少少会open一些。饮食男女,大家都想快刀斩乱麻,片叶不沾身。一个是个无业游民,搞创作的,另一个是靓丽空姐,搞服务的,一拍即合。
我点了点她的照片,放大了几倍,仔细端详起了她的五官,她长的并没有多惊艳,只是皮肤特别白。
我解开了安全带,站起来四下观望。我身边坐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他睡着了,脑袋歪向了一旁,经济舱的座位太窄巴了,我的动作似乎打扰了他的美梦,他不安地咂了咂嘴。
果然,我扫描到了那位跟我匹配上的空姐,她正在把饮品递给一位乘客。
我马上按下了呼叫服务的按钮。
她转身来到了我跟前,微笑着说:“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打开交友软件,点开了她的资料,低声说:“这是你吧?”
她探头看了看,说:“是的。”
我又点开了自己的头像:“这是我。”
她的表情并没有太大的波澜,依然保持着那种职业的微笑,说:“真是太巧了。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空姐就是这点不好,永远都是同一种表情,我怀疑就算飞机即将失事了她们也会面带微笑带着乘客写遗书。
我说:“等你忙完我们聊聊呗?”
她说:“没问题,您叫”
我指了指手机屏幕:“小赵。”
她说:“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说:“一瓶矿泉水,谢谢。”
她把矿泉水递给了我:“赵先生,祝您旅途愉快。”
我旁边的中年男人彻底醒了,等小绝离开之后,他压低声音问我:“兄弟,咋勾上的?”
我说:“你上网搜搜,套路多得是。”
中年男人兴致勃勃地打开了手机,过了会儿,他很激动地问我:“网上说能摸空姐三次屁股,真的假的?”
我指了指前面一个穿黑衣服的彪形大汉:“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学名叫安全员,在飞机上他就是公安局长。”
这款机型的安全出口设置在飞机中间,那里的空间很大,跟商务舱差不多,我这种身高坐在那里完全可以把腿伸平。但那些座位一般是不卖的,只留给航空公司的会员。
给大家讲个略显猥琐的小套路——值机选座的时候,尽量选在“会员座”的附近。“会员座”需要年富力强的男乘客,如果出现紧急状况可以协助空姐帮助乘客撤离,一旦“会员座”上有老弱病残,空姐就会把附近的男乘客换到“会员座”上。
小绝就是用这个办法让我坐到了“会员座”上。
她的座位和乘客的座位朝向相反,我们正好面对面。
我们聊了很多。她认为写作者不是在家宅着就是在旅行的路上,从来都没有具体的单位。而我认为空姐工时少,薪水高,还能看遍世界的名山大川。
显然我们都错了。
她一天要飞五趟航班,稍不留神就走遍中国了,这是她今天的第二趟。她们一般飞四天休两天,或者飞三天休一天,几乎不能请假,也不能选择航线,一切都要服从公司和系统的安排。
外人看来,空姐在爱情观上肯定比其他人更开放。我把这个观点对小绝说了,她苦笑着说:“工作环境限制,我们想开放也开放不了啊,不然我还需要交友软件吗?”
她连苦笑都是职业化的。
也是,一方面她们的社交圈子太小了,除了机长就是飞行员,而乘客都是匆匆过客,而且多数人都觉得她们高人一等,不好拿下,连尝试都觉得浪费精力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本难念的经。
又是空姐,又是交友软件,你们肯定很期待之后的情节,对飞机上的事儿没什么兴趣那我快进了啊。
飞机有点延误,一点多才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小绝还要继续飞,大概晚上七点左右能回到北京。我跟她约好了,到时候我接她下班。我的住处离机场太远,我打算在机场附近找个宾馆,开个钟点房歇着。
T3航站楼的穹顶是玻璃幕墙制作的,非常通透,能看见飞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我深深吸了口气,北京,我终于回来了!
走出机场,很快我就找到了一家快捷酒店,开房,付款,刷卡,进房间,刚刚躺下就听到了敲门声,外面传来一个女声:“您好,有人吗?”
应该是保洁人员。
我回了一句:“有人。”
我以为她会走掉,没想到她居然刷卡把房门打开了。接着,她把房门固定住,推着工作车走进来,看到我吓了一跳:“喔,有人啊”
我说:“我刚才说了有人,你没听见?”
这位保洁人员抓着制服下摆,显得很紧张:“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奇怪,前台告诉我这间房没人啊。”
我说:“我刚开的钟点房。”
她赶紧把工作车推出去了:“打扰了,您接着休息吧。”
很幸运,由于天气原因,小绝的最后两班航线被取消。我麻利地退了房,来到航站楼接她下班。
灯初上,夜未央,飞机呼啸,车来车往。机场高速灯火通明,就像永远不会干涸的河流。
小绝从员工通道里款款走出来了。她穿上高跟鞋大概有1.70米,身姿挺拔,在机场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我拉过她的行李箱,快步朝外走去。
她说:“你步子大,慢点儿。”
我回头笑了笑,说:“我有点紧张。”
化解尴尬的办法就是说出尴尬,当然这是老办法了。
她笑了:“紧张什么?放松。”
我发现,我跟小绝在一起,竟然变成了被动的一方。
她的公寓就在机场附近。我们首先来到了一家日料店,在角落找了个餐桌坐下来,服务生立刻帮小绝拉开了座位:“小姐,您今天吃点什么?”
这个服务生大概刚成年,留了个西瓜头,眼睛又大又圆。
我们点了两份套餐,要了一瓶清酒,边喝边聊。清酒烫了四次,很快就见底了。小绝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很开心,甚至脱掉了高跟鞋,她说每次穿上它们就觉得自己被职业束缚住了。
我也晕乎乎的,盯着她的鞋,视线有点模糊:“我快被你束缚住了。”
我们又要了一瓶清酒,场地也转战到了榻榻米上,我们盘腿而坐,很像东北的炕。
想到“炕”这个词,我的思维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我到底怎么了?
小绝彻底放飞自我了,一口接一口地喝酒,那姿态有些熟悉,似乎跟我记忆深处的某个女孩很像,她是谁了?
喝着喝着,我们就着芥末章鱼竟然划起拳来
离开的时候,我和小绝抢着付钱,收银员却好像看不见我似的,直接接过小绝的手机结了账。此人的情商也够低的,怎么能让女孩结账呢?
入夜后起了风,外面冷飕飕的。
那个留着西瓜头的服务生追了出来:“小姐,您的打火机落下了。”
噢,那是我的打火机,zippo,很男士。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个服务生为什么只跟小绝对话?难道我不存在?
冷风灌进了外套,我脊梁骨一麻。
我和小绝相拥着回到她的住处,把鞋一蹬,两个人就滚到了床上。
她家的电视没关,正播放着一场搏击比赛。双方穿着短裤,汗水四溅,那是肉和肉的搏击。
第一回合,红方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不断进攻,蓝方连连躲避,一次次被防护绳拦住,身上出现了一处处深红色的印记。
第二回合,蓝方开始迎合红方的进攻,渐渐进入了节奏。这是势均力敌的几分钟。
第三回合,红方使出投技把蓝方摔倒,并且压在了蓝方身上,四条腿紧紧夹在一起。
第四回合,蓝方竟然翻到了红方身上,攻势比红方更猛。
第五回合,双方死死抱在一起,倒数十秒,比赛结束,双方精疲力竭
第二天,我和小绝一直腻在床上,叫外卖,饭也是在床上吃的。
下午的时候,小绝出去买菜了,晚上她要亲自下厨。
她出门之后,我爬起来四下转了转。
这房子最多40平方米,可以叫一室零厅,或者叫零室一厅。阳台旁边有个木门,半人高,它被锁上了。我从窗子看出去,天气昏暗,风声阵阵,刮起了沙尘暴,因此没有了黄昏的过渡,小区的路灯已经亮起来。
小绝的笔记本电脑虚扣着,我掀开它,看到了一部暂停的电影,就顺手打开了,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很意识流,忽而一群人坐在幽暗的货车内摇摇晃晃,忽而一群人提着大小行李奔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忽而一群人在红色大雾中气喘吁吁地奔逃,忽而一群“解放军”跟一群“国民党”在打仗
这些画面怎么这么熟悉?难道是我做过的一个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