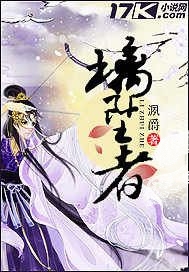能进宫,哪怕就是做个打扫尘除的杂役,那也是无数人的梦想,何况他六岁便被册封为太子,在别人眼中他是龙中金龙、凤中玉凤。可实际上,他的每一根头发、每一块皮肤都在诉说着他的不满。他不满的是,不能像其他的蓬头稚子一样奔跑撒欢摸鱼抓虾,不能像其他的英俊少年一样信马由缰驰骋田猎,不能像高祖先天子那样纵横天下谈笑寰宇。他更不愿面对的是,苦等数十载,孙子都到了他当年立太子的年纪,可他依然是太子,这就罢了,偏偏最近父皇好像刻意冷落他,置百姓疾苦不顾,置自己的建议不顾,也置母后不顾,却对弗陵弟弟,这个不知世事艰辛的小娃娃恩宠备至。其实他并不是贪恋权位,无尽的等待早已磨平了他内心所有的期望,也磨平了所有的焦灼,他放不下的只有逐渐凋敝的江山和衰老孤寂的母后——她可是曾经名动天下的卫子夫。
“罢了吧……”太子一拂衣袖,转身背过去:“师傅,您是大儒,那‘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是什么意思?”
“殿下……”石德明白太子的心意,声音不觉哽咽了。
“给我讲讲吧。”太子的声音甚为低沉。
“孔夫子的意思是说,侍奉父母之时,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劝说他们,即使他们不愿意听从,还是要对他们恭恭敬敬,不违抗他们,替他们操劳而不怨恨……”石德的声音同样低沉。
倏忽又是一夜。
皇上移驾甘泉宫,赵婕妤和几个嫔妃陪侍,依然没有叫皇后卫子夫随行。太子于是更加惦念母后,一大早,便由人伺候着来到椒房殿。偌大未央宫由于皇上移驾和百官随行而显得无比冷清,偶尔的鸟鸣竟激起回声,椒房殿正门前也无甚车马,只有那殿前的双阙展示着殿主人的皇后身份。
卫皇后出殿门迎接太子,就像一个普通的老母亲期待儿女一样。卫皇后已年过六旬,从集三千宠爱的绝色佳人到尽享荣华的中年女人,再到现在门庭冷若冰霜的普通老妪,斗过了金屋阿娇,却终究输给了岁月,更是在皇上曾经的蜜语甜言前败的彻底。
“据儿,听说你的车马被江充扣了?”卫皇后好似不经意一问。
“是,母后。”太子并没打算让卫皇后知晓此事,她已经历太多风风雨雨,且上了年纪,不应该再用此等小事让她劳神。
“哦,那几个被廷尉定了要弃市的人,你要把他们放了?”卫皇后又问道。
太子非常惊诧,不知卫皇后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答道:“回母后,那几人不过拉了一车原木进城,而且已经查明他们是烧炭为生的小民,并无证据说明他们运木头是为了做木偶卖于宫人,廷尉所判……”
“你们都退下吧,留我们娘俩说说话。”卫皇后突然打断太子的话,又道:“嫽儿留下”。嫽儿是卫皇后长御,容貌端正,落落大方,跟了卫皇后十余载,事她如事母,忠厚异常。除了她,所有宫娥、黄门都俯首退去。
“你说的我都知道,多少年了,我从不过问国事,但你的事我肯定要问的。你还不明白吗,汉家的事,没有对错,皇上说的就是对的。皇上叫你监国,并不是叫你否决他批过的事。巫蛊的事是皇上最在意的事,从阿娇到公孙贺,哪有什么对错,皇上说对了就对了,错了就对了,谁也不要逆龙鳞。我老了,整年也见不着皇上一面,见着了也不过是去做摆设的,也说不上话,我也不指望什么了,就指望着你能顺顺利利继位就行了。”
卫皇后一口气说了太多话,有点喘,长御忙在她背上轻推。
“传医官!”太子对着长御说道。
“不用了,我没病。”卫皇后轻声说道。“忍字怎么写”,卫皇后又突然问道。
太子自然知道卫皇后的意思,仍顺着答道:“回母后,上面一个刃下面一个心。”
“要时刻记得心悬利刃,不要让刀掉下来,再硬的心也躲不过明刀暗箭,否则,我们娘俩就算想当个普通百姓也难遂心愿。只要刀不掉下来,这天地江山有你改的时候!还有,以后没有特别的事,不要到我这里来了,也不要问安了,表面上越冷淡越好,有什么事,我会让她告诉你,她学过三拳两脚,不必担心。”卫皇后朝嫽儿转了下头。嫽儿忙退后跪了下来。
自从公孙贺全族被诛,本就较少笑容的卫皇后更是愈发寡言少笑,今天说出这些话,更是让太子大感惶恐,含着泪也跪了下来道:“母后……”
“都起来吧。”不待太子说什么,卫皇后表情又放松了。“都当爷爷了,怎么还像小孩子。”卫皇后无奈一笑道:“我已经看透了,我卫家已经没有人,天子用公孙贺的事把我卫家都除干净了,后宫那些有子嗣的都蠢蠢欲动,内宫的大臣们也都是见风使舵的主,你呀,一定要把尾巴再夹紧点,紧到让天子忘了你,只要太子封号在,都会水到渠成的。”
“儿臣谨记教诲!”太子俯首道。他这才明白,原来母后看的比他还通透。
“不说这些了。”卫皇后摆了下手继续道:“我这有个好宝贝,是以前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献给天子的,说是最能驱魔辟邪,当时你父皇正感风寒,没想到当天就大安了,他觉得很灵验,就给了我。还说什么西方有摩尼教,专保好人平安,最能降妖除魔,有个西方方士不知何年何月从何得到这个,给了张骞,我看做工精致,就带给我的小重孙当个长命符吧,等他满月了抱给我看看。能做几个孩子的奶奶,也是一个女人的人伦大福了。”
话音未落,嫽儿就从一个木柜中取出一个琥珀笥,双手托着举过头顶,跪在太子面前。
太子不喜方士,特别是西域巫师,但这个摩尼教他也有所耳闻,据说一心向善便能飞升,还能荫及子孙。教人向善,即使不能飞升又何过之有?所以他并不反感摩尼教,反道有些倾心。
太子用巾帕拭了泪,双手捧了,谢过,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面宝镜,大如八铢钱,正面似铜非铜,似玉非玉,澄明润泽,恰如明月。背面青如宫瓦,花纹与宫中所有铜镜都不同,乃是八瓣莲花,正中若隐若现一人结跏趺坐,衣露一肩,双手合掌,双目似闭,甚是安闲。
“去吧,我的儿,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否则,大祸将至矣!“卫皇后的声音有些颤抖,转过身去,不再看太子。
太子望着卫皇后瘦弱又略有佝偻的背影,大有风吹黄叶、雨打秋草之感,他知道,是到了儿子为母亲遮风挡雨的时候了,他深深一拜,道了一声“儿臣谨记!”便袖了宝镜退了出去。
回到博望苑时,阳光正暖,透过西域引来的葡萄架,斑斑点点撒在地上,葡萄架上,或青或紫密密麻麻挂着半熟的葡萄,两个孙子并十几个仆妇在挑葡萄。葡萄架傍着一个数十丈见方的小池,清澈澄明,或红或青的各色游鱼缓缓而行,几只鸳鸯浮在水上瞌睡。葡萄架旁有一凉亭,史良娣并儿媳王翁须一老一少在亭中逗弄小孙子。
天心难测,狂风突然卷着乌云滚滚而来,应是骤雨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