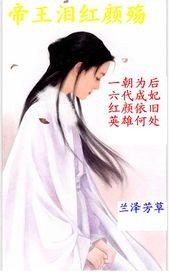原来,穿过掖庭后院还有一个不小的厨房,摆了许多简单的条案,有四个双口大灶台。厨房里间居然还有一个单独的餐室,各色家具涂着清漆,就连筷子都雕着图案,整齐的摆在筷架上。餐室灯火通明,颇为辉煌。
张贺道:“爷爷可不是贪官。这是预防着宫里来人用的,平常吃饭都是署吏送到房间里去,今日给你们破个例,以后咱们也不在这里吃,不踏实。”
病已抬头问:“宫里来人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吃饭呢?”
张贺笑了:“那怎么行,那样的话爷爷的官帽子早就没啦,一家子人也就等着饿死了。”
厨娘看到人来了,赶紧把焖在锅里的饭菜上到桌上。一面笑着上菜,一面说着“油焖鸭”“犬肉”“咸胡瓜”“河蚌羹”“麦饭”,菜量都不少,菜色也很正,最后还有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又有一个小吏名唤赵无用的,温了酒给张贺、史高倒上了。广汉百般推辞,也坐上席斟了酒。
病已是真饿了,却又认生。广汉看出他的心思,频频给他夹菜,病已养着大黄,不忍吃犬肉,便谢过广汉,自己夹些其他的菜吃。
史高心想:“这二十几年真是白活了,还是当官好。以前虽然有点小钱,但时时担忧官府和贼人骚扰,处处受读书人和世家子弟讥讽,说来说去自己不过是贱民,哪有官家气派!”
平日里史真君治家甚严,家中又没有多少余钱,史高平时也没怎么喝过酒,几口下去就有醉意了,几人便热络起来。史高和病已这才知道张贺和广汉都是受过腐刑之人。广汉最初是昌邑郎官,由于人老实,办事踏实,深得上司信任,却又常被同僚嫉妒,三番五次被设计陷害,官越做越小,沦为掖庭下属的暴室啬夫,也就是掌管后宫染衣坊的人,虽说手下不多不少也有二三十个民夫,那也不是个正经的“官”了,只不过比奴仆好了一点。
几人正聊间,门口忽然闪过一个人来,好像是喊他们吃饭的少年。病已忙站起来道:“你吃饭了吗,过来一起吃饭吧。”
厨娘闻言,慌忙跑过来跪地道:“张令,民女管理无方,有贵客在此,却还扫了您的兴,还望张令包涵。”
“这是哪里话,这是在后厨,不兴那一套,快快起来,叫缜儿一起来。”张贺招手道。
厨娘只得唤缜儿过来。缜儿又拜过,才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病已忙站起来给他半个座位,缜儿说什么也不坐,只找了个脚凳在最边上挺着背低着头坐下了。病已这才看清,缜儿形容瘦小,脸颊发红,双手粗糙,腰间系了一个布条,粗麻衣明显偏大,上面还沾了不少柴灰,而且衣服上打了几块颜色深浅不一的补丁。病已没想到堂堂长安城中,竟有和杜县乡野一样的小孩,顿生怜悯之心,暗想明天找身冬衣送给他。可再仔细看,缜儿头发和脸都洗的干干净净,补丁也是针脚细密,又兀自感叹毕竟是有母亲好!
可后来才知道,厨娘并不是缜儿母亲,他母亲早年嫁给刘姓当差的,生下缜儿,谁知刘差役在巫蛊之事中丧命,他母亲便带着他到处做短工,结果被人欺凌,变得有些疯癫,缜儿就带着母亲到街上乞讨,张贺看她娘俩着实可怜,便叫来到后厨做帮工,腾了住的地方,母子俩吃住都在后院,缜儿母亲虽有些头脑不清,却能干些粗苯活。厨娘看着缜儿可怜,便收为义子,也不怎么使唤缜儿母亲。缜儿也百般懂事,跟在义母后面帮着担水劈柴烧火、洗地擦桌上菜,有饭吃都先给母亲吃,有衣穿都先给母亲穿。
病已听说这些,心中大为感动,世间竟有这样的好男儿,想想自己的生活还算好了,又想到疼爱自己的外曾祖母,不觉偷偷流下泪来。
张贺觉得话题沉重,便打岔道:“缜儿,听说你常常在烧火的时候读《诗》,很好,很好!学的怎么样?”
缜儿害羞道:“好多字都不认识,看不懂。”
张贺道:“没人传道授业,确实不好理解。我认识一个家学师傅,是东海人,叫澓中翁,对《诗》很是精通,在长安城开馆收徒,离我这掖庭署不远,等过几天,你跟着病已一起去上学,早出晚归的,两个人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
这时,厨娘赶忙过来又跪下道:“张令,缜儿现在吃得饱穿的暖,哪还敢奢望读书,再说,我儿这样的人家,读书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张贺忙叫厨娘起来道:“此言差矣,有多少英雄豪杰、风流才子都崛起与阡陌,高祖不也不是世家豪族么。缜儿这孩子,至善至美,必须要读书,当今天子圣明,大将军也爱才惜才,从上到下都乐于举荐人才,说不定‘明经’‘孝廉‘正等着他呢。”
厨娘笑道:“那可不敢奢望,能跟着您做做饭就行了,不过,要是真能那样,他亲娘可算是能享福了。只是……”
张贺猜到厨娘的心思,便道:“老先生是我的旧友,其实我前几日就跟他说过了,两人只收一个人的份子,钱你就不必担心了。”
厨娘带着缜儿千恩万谢,病已也对眼前这位张爷爷深感钦佩,这么好的官,怎么会受腐刑这种奇耻大辱呢?
饭食结束,杂役赵无用送史高去休息,张贺赵广汉带病已到了广汉的房间,张贺见果然收拾的清清爽爽,病已的床铺也干干净净,便也放心的去休息了。广汉伺候病已洗了脚,还给大黄狗弄了一个草窝,也就各自睡了。病已忍不住想外曾祖母,又觉得这今天的事情像做梦一样,自己成了所谓的皇族,却又不得不跟亲人别离,这皇家的规矩还真是奇怪,翻来覆去的半天才睡着。
第二天一早,病已便被外面的说话声吵醒了,睁眼一看,广汉早已出去,看来他这个暴室啬夫还真闲不住,便独自穿好衣服,开门一看,院中停了一辆有盖的马车,一个年轻公子跷着二郎斜倚在架辕上,嘴里刁着一根干草。公子细眉宽眼、肤如夏麦,颇为英俊。马车旁边与他说话的正是张贺,病已赶紧叫了“张爷爷早。”
张贺见病已起来了,忙道:“病已,这就是彭祖,比你大三四岁,我这几日事多,就叫他带你和史公子到处玩玩,你就叫他彭祖哥吧。”
还不待病已开口,彭祖就道:“哎呦,张令,他叫我哥,叫您爷爷,那我不也得叫您爷爷。”
张贺佯怒道:“小兔崽子,净贫嘴,这是皇曾孙,比你小几岁,就叫你哥了,我今天把话说在前头,你就是把命搭进去,也得保护好他!”
彭祖翻身跳下来,认真地行礼道:“小的遵命,您老人家就放心吧!”
张贺道:“等会史家大公子史高也要来,你带他们去东、西两市转转,几个大宫也都可以转转看看,长安城哪里好玩好看,这些你比我懂。”
彭祖魅笑道:“长安什么最好看?姑娘最好看。带他们见识见识?”
“你!小兔崽子,别跑!”张贺风一样脱下自己的木底鞋,劈头盖脸就朝彭祖扇过来,彭祖也早就风一样绕到马车另一边了。两人正难分难解间,史高也到了,张贺只得停下来,又互相介绍一番。
几人刚要出发,突然,一个挎着食篮的白衣女孩儿娉婷袅娜的走过来,丱发粉带,眼流秋波、顾盼生辉,面似满月、温润如玉,嘴角微微上翘,一个酒窝清浅,几缕不听话的青丝飘在眼前,不知哪来的仙子!虽衣着朴素,没有妆容,更无环佩,却愈发惹人怜爱。病已的心突突跳起来,看一眼觉得可爱,再看一眼觉得甚是熟悉,又看一眼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像走在秋日的溪边,像坐在盛夏繁茂的树阴中。想多看一眼又怕其他人笑话,只得扭过头去,却看见彭祖一本正经的在捏掉身上沾的麦杆。
女孩儿本没注意到院中有这么多人,猛的看见,不觉吃了一惊,“啊”的一声竟自己绊倒了,像一只粉蝶一样扑落在地上,餐盒中的熟鸡子一个个滚了出来。
病已的心也“咯噔”一下,仿佛是自己摔倒了。不过,还不待他反应,彭祖又像风一样几步跑过去,将女孩儿轻轻扶了起来,揶揄道:“快起来,何必行这么大的礼,还没过年呢。”
"一边儿去。”女孩声如脆玉,边说话边弯腰去捡鸡子。
张贺关切的问了问,料女孩儿没摔到什么,便道:“你今日来的很巧,皇曾孙恢复了宗室署籍,天子下召掖庭抚养,昨天才来,今天叫彭祖陪皇曾孙和史家大公子四处走走,你既来了,就把东西放你父亲床上,和他们一起出去散散心吧!”
女孩天天在家受母亲管制,巴不得出来,听见张贺如是说,也不问皇曾孙是谁,点头如啄米的答应了。
张贺公务繁忙,容不得他再安排下去,便把一切交代给彭祖,准备先走了。彭祖喊住他道:“父亲,您倒是安排的爽快,这么多人一辆车可坐不下了。再说了,难不成我还真带他们满大街干转悠,不吃点喝点买点?”说着,将手指伸出来搓了搓。
张贺放心这小子,别看他平日里没个正经,做事却不含糊。笑道:“早预备下了,给了赵无用,要用就从他那里拿,别替我省着,另外,叫他给你们驾车,还省下个车夫。”
彭祖听了道:“您真是高人,给我派了管账的,还派了个监军。”
张贺没功夫跟彭祖闲扯,兀自先走了,留下彭祖当家,不知他将做何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