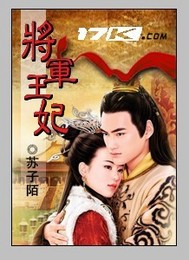鸡鸣三遍,郭穰和羽林卫的马蹄声远了。丙吉安排田尊将赵、胡二人和病已乔装成民妇带回家中,并告诉田尊,若囚徒保不住,就叫二人带病已远走高飞,不要再回长安,若保得住再听吩咐。
这边,郭穰顾不得梳洗吃饭,下了马直奔建章宫,脸上冻的发青也顾不得了。天子年老,又整日思虑国事,每日醒的极早,看见郭穰灰头土脸的跪下了,冷冷道:“差事办完了?”
郭穰早把说辞又理了一遍,答道:“陛下,廷尉监丙吉无理,竟然敢公然抗旨,说大汉依律治国,还没审定的案子不能滥杀。”
“哦,丙吉倒是个硬骨头。”天子好像居然没有生气的意思,边缓缓展开一卷竹简边问道:“你是来请兵的还是来说情的?”
“陛下,小的既不请兵也不说情,有要事陈奏,可否让左右侍从先回避?”天子也知郭穰办事还算稳妥,便恩准了。
“陛下,丙吉说太子有个孙子,皇孙刘进之子,当年沦落郡邸狱,阴差阳错得以保全性命,就在郡邸狱,且他以性命担保,所以小的没敢贸然行事。”郭穰缓缓道。
为防天子伤心,触了霉头,臣子们一般不提太子刘据之事,内宫之人更是对比讳莫如深。自从天子把提立储之事的臣子骂出去后,天子更是已好久没有听到过“太子”这个词,好像忘记一样。今日猛一听到,心里一惊,再听到太子居然还有后人,不自觉的从喉咙发出一声怪声,往事一幕幕又涌上心头,头也又痛起来,一使劲,竟把手中竹简扯散了,噼里啪啦掉了一地。
郭穰吓坏了,忙把头“嘭”的一声磕在地上道:“小人罪该万死!”
天子没搭话,仰面长叹道:“天意,天意啊!也许,欠的要在子孙上面应验了!”良久,天子低下头来,低声道:“叫人传丙吉过来。”
郭穰听了,心中暗喜,事情好像走上了他们预铺的道路,朗声道:“遵旨!”
丙吉就在郡邸狱候着,马都备下了。不一会便到了天子面前,见了君臣之礼。天子急切问道:“你说据儿还有个孙子,就在郡邸狱?”
“是。”丙吉并不急着算盘豁出。
“孩子是怎么来的?”天子果然有点急切。
“臣以为,可能是陛下福德深厚,子孙隆盛,又恰逢巫蛊之事,所以并未来得及录入宗正府。但皇孙进确实有了这个孩子,乃是和王翁须夫人所生,当年,王翁须带孩子落入郡邸狱,太**亲近之人悉数殁了,唯独这孩子没有名字,反而落下了。臣蒙受天恩,从鲁国来到京城充任廷尉监,发现了这个孩子,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看着着实可怜,就在狱中找了乳母养了起来,一晃五年了,若不是陛下昨日下旨,可能,臣也还不敢禀报,如有罪责,臣甘愿一死!”
“爱卿深明大义,宽厚仁爱,何罪之有。孩子可否有什么随身之物?”天子追问道。
“有。”丙吉早就准备好了,有两样物件他层层包裹,一直放在家中最隐秘之处,今日总算又见得阳光了,丙吉也难掩内心的激动,手竟然有点抖。翻开布包,正是五年前收起来的肚兜和宝镜。
郭穰把东西拿到天子手中后,天子眯着眼睛看了又看,道:“这个肚兜却是宫中之物,却也不稀奇。这个铜镜,朕虽老了,但认的仔细,就是当年张骞带给朕的,只有一面,朕给了皇后,不是卫家子弟,断不可能再有的。”天子说罢,眯上了眼仰面靠在龙椅上,像睡着了一般,眼角却不经意间流出浊泪。
“臣与太子有过几面之缘,如今皇曾孙已经完全长开,小小年纪便英姿飒爽,与太子容貌极像,陛下要不要……要不要看一看皇曾孙?”丙吉知道,眼下最当紧的是病已的出路。
“还有有没有名字?”天子并没有回答丙吉的话。
“回陛下,当日臣为了给皇曾孙穰灾祈福,僭越规制,给孩子起了小名,叫‘病已’,望陛下亲赐正名!”
“‘病已’好啊,多好听的名字,‘霍然病已’,爱卿有心了。郭穰何在?”天子道。
“小的在。”郭穰忙答道。
“近日黑鸦阵阵,盘旋于诏狱上空,其声凄厉,这是上天在警示朕,有无罪不得申诉之人,朕可能真的时日无多,传旨大赦天下,京中二十三监囚徒悉数放归回家。”天子努力正色道。
“是。”郭穰暗喜。
丙吉大喜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宽厚仁爱,定能龙体康健,永享福禄。”
“朕累了,你们都下去吧。”天子又眯上了眼睛。
丙吉忙道:“微臣还有一事,望单独呈奏陛下。”
“好,爱卿留下,其他人都下去吧。”天子闭着眼道。一干人等皆窸窸窣窣退下。
丙吉俯首道:“陛下,微臣不敢妄自揣摩圣意,但微臣既食君禄,就要尽君之事,微臣以为,可能有人借机加害皇曾孙……”
“朕想到了。”不等丙吉说完,天子便开口了:“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这许多年来,但凡放书之士有那么一点灵验,朕的诚心也该感动上苍了吧!朕自会查清此事的来龙去脉。此外,朕久居深宫,对这宫中之事了如指掌,所以,刚刚朕刚冒出将病已立为国储的想法就又打消了,朕不想他还没等到皇位就被人害了,还是让他自由自在的成长吧,一条小蛇比一条小龙更容易活下去!”
丙吉听了,痛心不已,倘若病已真的立储,那也是对太子的巨大弥偿,也会把病已的命运从地上拉到天上,但天子如此安排,自己也不好再说什么,今日面圣,已经换来天子大赦天下,一干人等皆得免死,比预想的最好的结果还要好了。只得回道“陛下圣明!”
“爱卿保全有功,朕自会安排,下去吧。”天子说完,斜靠在龙椅上。
“陛下,那病已该如何……如何安排?”丙吉仍不罢休。天子却动也不动,似乎没有听见。郭穰在一旁连忙使眼色摆手,病已只能作罢,缓缓退了出去。
丙吉走后,郭穰以为天子睡着了,便着人拿来金丝云锦被,正欲给天子盖上,天子突然张口道:“不必了,去,叫钩弋来,朕想和她说说话。你亲自去。”
顷刻,郭穰通秉钩弋夫人觐见。天子道:“夫人可曾问你什么,神情若何?”
郭穰如实答道:“回陛下,夫人问小的,皇上有什么事,神情若何。”
天子“哦”了一声道:“宣她进来,你们都退下吧,一个都不留。”
“喏。”一众人等悄悄退出。
钩弋有些心虚,却最擅做戏,又是给天子松肩膀又是揉腿,但她发现内侍一个都不在,骤然慌了起来。
良久,天子才开口:“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钩弋夫人忙道:“这是陛下巡幸河东时的诗,陛下竟还记得如此清楚,这首诗臣妾也最喜欢。”
“哦?朕只是想起往事,何等风流快哉,如今只能‘奈老何’了。不过,在老之前,朕还有一事问你。”
钩弋夫人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是福是祸。忙跪道:“臣妾愿与陛下生死相随!”
天子努力的扬扬手道:“坐朕身边来。”钩弋夫人便蹭了过来。“李茅已经被朕处死了,没有人会说你坏话了。”天子突然道。
钩弋夫人瞬间心惊肉跳,凭她对天子的了解,天子必是查到了事情的真相,又立刻跪下,却被天子抓住了手。没待钩弋夫人说什么,天子又道:“你知道刘髆是怎么死的吗?”
钩弋夫人早已魂不附体,拼尽气力道:“昌邑王暴毙而死。”
天子睁大了眼睛:“不,是朕逼死了他,朕又逼死了自己的亲儿子!哎,要是朕不逼死太子,刘髆也不会想着争位,朕也不会逼死他!一个皇位害死了我两个最英武的儿子,他们都是我汉家栋梁啊!”说着,天子眼角竟流出浊泪。
钩弋夫人浑身如筛糠,不知该如何接话。
“钩弋,你不要怕,朕不怪你,天下人都是道,朕最疼的就是你,朕为什么要逼死刘髆,因为朕要立陵儿为太子,这下你放心了吧。”
“啊!”钩弋夫人不自觉的发出一声惊呼,本欲高兴,又觉得天子神色不对,只得低下头去。
“郭穰何在。”天子轻轻一呼。候在门外侧耳倾听的郭穰旋风般进来跪下了。
“钩弋夫人恃宠而骄,靡费无度,身居后宫大位,不能专心抚养皇子,左顾右盼,似有不忠之心,赐白绫自缢。”天子所言极慢,神情凄惶,并不看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脑中一嗡,再也坚持不住,摊在地上苦苦哀求。
天子轻轻一摆手:“去吧,去吧,今日你不得再活。”
钩弋夫人无法相信昨日的温柔遣倦一下化为梦幻泡影,无法相信昔日的百般努力一下随风而逝,真是百般计算最后不过是在车上股掌中转圈,觉得掉入寒冰冻一般,寒的透心彻骨。
郭穰虽惊讶,却也不觉得意外,只站在钩弋夫人身边等她起来。天子又摆了一下手,郭穰会议,叫来两个小黄门,将钩弋夫人使劲扶了起来。钩弋夫人只得转过身去,面色苍白地一步一步往门外挪去,外面日头正好,暖阳射在冰冷的铜门上,煞是刺眼,钩弋夫人避过光,顺势扭头看了下天子,却只看到比那铜门还冷峻的侧颜。
天子虽未看她,却似乎察觉到钩弋夫人的举动,又道:“放心去吧,朕说到做到。郭穰,这就把画工所作的‘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送给大将军霍光”。钩弋夫人何其聪明,扭头朝着天子发出邪魅一笑,然后迈开步子,跨过及膝门槛,消失在一片苍茫日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