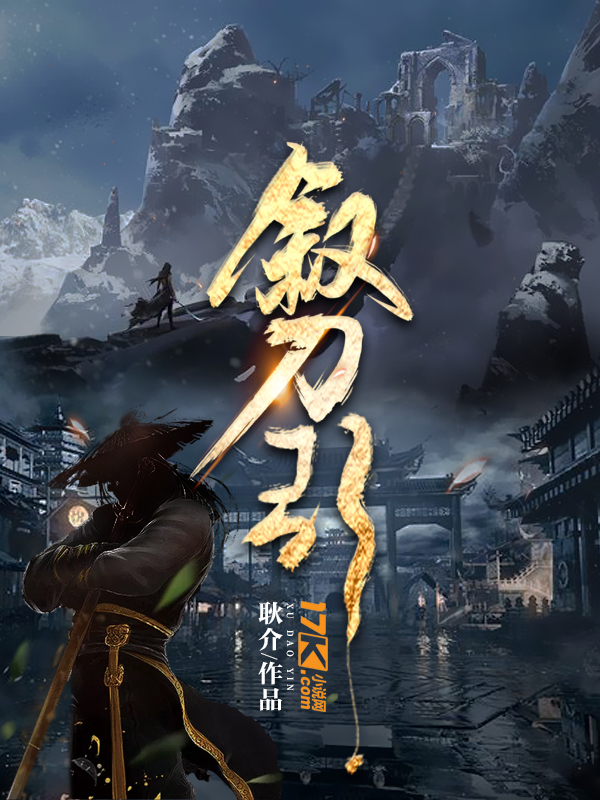西门霸听得全身寒毛都竖立起来,说:“不……不敢。”
乌邦慢慢地喝茶,静静地看着这边。
他看见那脸色通红的人冷笑道:“就凭你,也配称疾风刀?”
他的手一抖,掌中突然多了柄鲜红细长的西洋软剑,迎面又一抖这绳子般的软剑。
他用这柄剑指着西门霸,一字字说:“留下你从波斯带回来的那包东西,就饶你一命。”
这时,程炳坤突然长身而起,陪着笑说:“两位只怕是弄错了,我们这趟是在波斯交的货,现在车已空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两位……”
他的话还未说完,那脸色通红的人掌中红色的剑已刺穿了他的咽喉,剑柄轻轻一抽,赵老二的脖子就喷出了鲜血。
接着,鲜血如雨点般飞来,洒在西门霸的脸上。
每个人的眼睛都看直了,两条腿却在不停地抖着。
乌邦静静地看着,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西门霸能活到现在还没有死,毕竟是有两手的,他突然从怀中掏出了个黄布包袱,丢在桌上,说:“两位的消息果然灵通,我们这次的确从波斯带了包东西回来,但两位就想这样带走,只怕还办不到。”
乌邦盯着桌子上那黄布包袱,心中想:那包袱中是什么东西,他们二人为什么要来抢?
红脸阴恻恻一笑,说:“你想怎样?”
西门霸说:“两位好歹总得留两手真功夫下来,叫在下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退后七步,突然“呛啷”一声拔出了刀,乌邦知道他是要和对方拼命了。
谁知他却一反手,将旁边桌子上的一碟菜挑了起来,碟子里装的是红烧狮子头,狮子头也立刻飞了起来。
只听刀风呼呼,刀光如匹练地一闪,十多个狮子头竟都被他斩为两半,纷纷落在地上。
看到这里,乌邦嘴角又泛起一丝冷笑。
西门霸面露得意之色,说:“只要两位能照样玩一手,我立刻就将这包东西奉上,否则就请两位走吧。”
他这手刀法实在不弱,话也说得很漂亮,但乌邦却在暗暗好笑,他这样一做,别人也就只能斩狮子头或者别的菜,不能斩他的脑袋了,他无论是胜是负,至少已先将自己的性命保住了。
红脸哈哈一笑,说:“哈哈,这只能算是厨子的手艺,也能算武功么?”
说到这里,他长长吸了囗气,刚落到地上的狮子头,竟又飘飘地飞了起来,然后,只见鲜红的光芒一闪,满天的虾球忽然全都不见了,原来已全都被他穿在了剑上,就算不懂武功的人,也知道刀劈狮子头虽然不容易,但若想将狮子头用剑穿起来,那手劲,那眼力,和速度,不知要困难多少倍。
西门霸面如土色,因为他见到这手剑法,已突然想起两个人来,他脚下又悄悄退了几步,才嘎声说:“两位莫非就是……就是蓝睛双犬?”
听到“蓝睛双犬”这四个字,另一个已被吓得面无人色的镖师,一下就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就连少年身后那位虬髯大汉,也不禁皱了皱眉,因为他也知道近年喀什一带的黑道朋友,若论心之黑,手之辣,实在很少有人能在这蓝睛双犬之上。
可是他听到的还是不多,因为真正知道蓝睛双犬做过什么事的人,十人中倒有九人的咽喉都被他们刺穿了。
乌邦并不知道这两个人,但看见那个钻进桌子下面的镖师时,就知道这二人一定有点厉害。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二人会露出怎样不凡的功夫来。
只听那红犬嘿嘿一笑,说:“嘿嘿,你总算认出了我们,总算眼睛还没有瞎。”
西门霸咬了咬牙,说:“既然是两位看上了这包东西,在下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两位就请……就请拿去吧。”
白犬突然说:“你若肯在地上爬一圈,我们立刻放你走,否则我们非但要留下你的包袱,还要留下你的命。“
这句话正是西门霸他们刚才自吹自擂时说过的,此刻从这白犬口中说出来,每个字都变得象是一把刀。
西门霸面上一阵红,一阵白,怔了会儿,突然爬在地上,居然真的围着桌子爬了一圈。
乌邦身后的少年这时候忍不住叹了口气,喃喃的说:“原来他的脾气已变了,难怪他能活到现在。”
他说话的声音极小,但红白双犬的眼睛已一齐向他瞪了过来。
乌邦一见,立即低头,慢慢地喝茶。
背后的少年却似乎没有看见,端着酒杯慢慢地喝着。
白犬阴恻恻一笑,说:“原来此地竟还有高人,我兄弟倒差点看走眼了。”
红犬狞笑着说:“这包袱是人家情愿送给我们的,只要有人的剑法比我兄弟更快,我兄弟也情愿将这包袱双手奉上。”
白犬的手一抖,掌中也多了柄白色细长的西洋软剑,剑光却如白虹般眩人眼目,他迎风亮剑,傲然说:“只要有比我兄弟更快的剑,我兄弟非但将这包袱送给他,连脑袋也送给他!”
他们的眼睛毒蛇般盯在乌邦身后这个少年的脸上,这个少年却在专心的喝着酒,仿佛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但门外却忽然有人大声问:“你们的脑袋能值多少大洋?”
听到了这句话,乌邦身后的少年似乎觉得很惊讶,但也很欢喜,他抬起头,那佩戴残剑的青年终于走进了这屋子。
乌邦立即知道,这个青年来杀的人,就是这蓝睛双犬。他又抬了一点头,悄悄的看了过来。
他头发里布满了沙尘,将他的头发染黄,有些掉落在衣服上,将他的衣服也染成了黄色,但他的身子还是挺得笔直的,直得就像支笔。
他的脸看来仍是那么孤独,那么倔强。
他的眼里永远带着种不可屈服的野性,像是随时都在准备战斗,冷漠得让人不敢去接近他。
但最令人注意的,还是他腰带上插着的那柄残剑。
看见这柄剑,白犬目光中的惊怒已变为讪笑,他哈哈的笑着问:“哈哈,方才那句话是你说的么?”
青年答:“是。”
白犬问:“你想买我的脑袋?”
青年答:“我只想知道它能值多少大洋,因为我要将它卖给你们自己。”
白犬怔了怔,问:“卖给我们?”
青年说:“是的,因为我是来拿这包袱的,所以要你们的脑袋。”
白犬说:“这么说,你是来杀我们的?”
青年答:“是。”